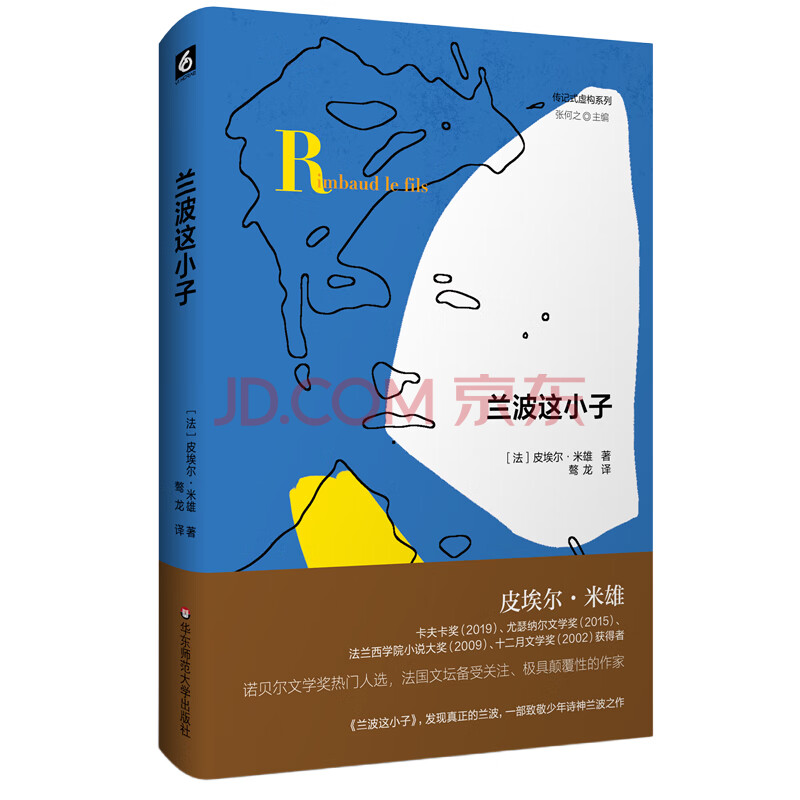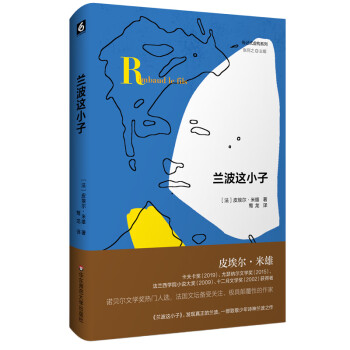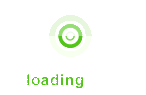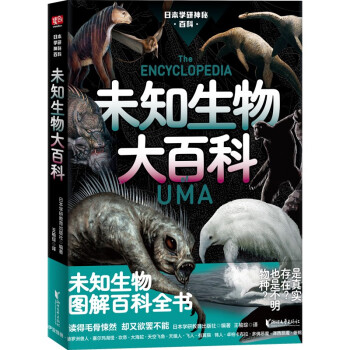内容简介
兰波(1854—1891)是19世纪法国著名诗人,早期象征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超现实主义诗歌的鼻祖。少年时代兰波便开始写诗并展现出惊人的才华,但他同时也放荡不羁,充满反叛精神,后来早早退出诗坛,英年早逝,成为诗坛稍纵即逝的神话。
“写兰波的书只有唯一一本,所有内容写出来都一个样。”《兰波这小子》以其独特的方式打破了这一传统。它既是断章,仅仅截取兰波生命中几个不起眼的时刻;也是残篇,以兰波写完《地狱一季》为全书结尾。同一个故事夹杂着两种声音。一个声音讲述不一样的兰波:受困于家庭牢笼,年少成名却难在巴黎找到立足之地,为爱奔走却在他乡斩断情缘,最终放弃文学远赴非洲。另一个声音穿引其间,是米雄自己的:他对兰波的阅读,对虚构的思考,对文学的坚持……
目录
相传维塔莉·兰波,本姓居伊夫1
在所有获奖人中间10
也不在邦维尔家18
再无踪影的诗人29
再谈《圣经》41
再回东站61
再说诗人热尔曼·努沃75
附录 兰波之后,赤子之前91
试读
相传维塔莉·兰波,本姓居伊夫,这农村姑娘和坏女人饱受折磨,烂了心眼,是她生下了阿蒂尔·兰波。大家不知道是她先骂了天、后遭了殃,还是她埋怨非得受罪的命,硬是在厄运里苦苦地熬;破口大骂和苦命如十指相连,大家不知道咒骂和命苦在她心里是不是一回事,能不能相互代替,是不是彼此的由头,可她把生活,把儿子,把她生命里的活人和死人通通揉了个粉碎,用别人一碰就发痒的手碾碎在黑黢黢的指缝里。可人们知道,这女人的丈夫,也就是她儿子的父亲在其子六岁那年,人还活着就成了幽灵,游弋在远方炼狱般的军营,他在那儿只是活一个姓而已。对于当了上尉还轻飘飘的父亲,大家争论,他是不是白费力气在语法书上留下注脚,能不能读懂阿拉伯语,是不是找了个借口抛弃了化身幽灵的老婆。女人想把他裹进自己的阴影里;还有人争论,是不是他的离去让妻子性情大变——这些大家全不知道。他们口中的孩子面前有一方书桌,左边站着那幽灵,右边立着祈祷上苍降祸、饱受灾难摧残的女人。孩子是想象中的学生模样,他迷上了古来有之的作诗游戏。或许,他在十二音步的古老节奏里隐隐听到了远方营地的军号,听见磨难铸成的女人咕哝着的祷告;那女人想张开嘴巴,把平生所受的苦难与折磨喊出口,却像儿子找到诗句那样发现了上帝。跟我们想的一样,孩子在她断续的呐喊里给军号和祈祷许下姻缘,于是年纪轻轻便开始大量作诗,这里写几句拉丁语,那里留几行法语。他的诗句告诉我们,没有什么传说的神迹:它们出自一位生在外省、稍有天赋的少年之手,他的气焰仍未碰到合适的节奏和栖身之所,于是顺着节奏毫发无伤地化为慈悲。后来,少年的怒气绞着慈悲腾到空中,又重重地摔下来,怒火与慈悲互相助长,紧紧地缠在一起,沉重、衰弱,仿佛爆在手里的烟花结结实实地炸成了几瓣——未来这一切都将成为阿蒂尔·兰波名字背后的倚靠。方格本里写得满满当当的诗是初中生写得出来的谱子。大家知道这孩子成天赌气,强堆笑脸肯定不是他的强项,相片便可见一斑。各地信徒集来的照片像小餐包一样摞着,在一张张流转于指尖却丝毫未变的照片里,孩子膝盖上摆着夏勒维尔城里罗萨学校统一发的小军帽,胳膊绑着教士用的布条。他的袖章奇怪得难以形容,过去的妈妈们会在孩子初领圣体的时候,拿这种布条把孩子打扮得奇奇怪怪。往下看,孩子的小手指夹在封面兴许是菜绿色的祈祷经书里,另一只手藏在看不见的军帽帽檐里,他的眼神一如既往,像拧着的拳头,又坏又直地冲着正前方,好似看着摄影师的时候心里憋着一大股怨气。那个年代的摄影师全套着黑色的风帽,他们的手用过去修补未来,做着时间的买卖,孩子在惊慌失措的当口摆出了这副面孔。孩子接下来的人生和他受到的膜拜让我们知道,他外表下掩藏着无边的气焰:倒不是袖章和军帽让他生气,他气的是竟然把袖章和军帽摆在一起。跟大家说的一样,还俗的教士脚下躺着一片影子,那影子的主人正是队长和他身边那位由抗拒和苦难拼凑而成的女人。她抗拒一切,抗拒都是借着神的名头,是神用鞭子抽孩子的灵魂,让他变成了兰波:阴霾并非真人落下的影子,是他书桌两边逼真的小人像。说不定,孩子光是埋怨他俩就耗尽了全身气力,他恨军帽和祷告结合于此的诗句,却打心眼里喜欢诗句对他百般苛求。他为了应付诗的任务才摆出我们眼前这副面孔。这孩子永远一身气呼呼的样子,后面发生了什么,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恐怕他根本不恨爸妈:怨怼难成佳缘。作诗原本是要送人,在一送一还之间能有人还你一个貌似爱的东西:看,他们两人的手里拿着的不就是婚姻的花环吗?新娘厄运缠身,就算这个女人是苦难投胎,她终究比任何人都更有感受爱的天分,那么,付出爱又有何妨:她跟其他人一样向往着遥不可及的婚礼,不知丈夫知不知情。可她沉沦在祷告里,祈祷注定陷为黑暗,注定要让她用漆黑的手指——因为无法挽救又难被同情的命运已经没过了她的脖子——把那碎成一片片的快乐——因为她一样,她也憋着一口气——做成我们常能见到的送给孩子的礼物,做成鲜花和扯出来的假笑,做成雨果笔下矫揉造作却总归是事实的诗句,让她用手指把爱传递给没有经历过苦难的人,可这一切都与她无关。那花、那笑面,也跟其他一样,她要通通撕开:她不喜欢这个酷似自己的儿子,哪怕我们什么都不了解,仍能明白她不喜欢的其实是自己。她只怜爱身体里没有刻度却能吞噬万物的井,全部心思都用来在黑暗中摸索井壁,想要探到井底,好能望一眼开在边栏下的小花。为此,要作出更让她心痛的让步才行。她的儿子向来只知鲜花,不会摆表情。他打好领带,裤子平平整整,一副小大人的样子,嘴巴嘟成樱桃大小,为子之道的刻意好似在雨果笔下。然而这些全不及她的心意,大小细节一个不行,所以通通被她两根黑黢黢的手指碾成碎片,最终散落到井里。儿子为了排解别人难体会的愁绪,找到跟她差不多的出路,学会了摆弄其他人不玩的小玩意——自编自创的祷告。她读不懂含韵的语言写成的长诗,但靠着这一首首参不透的诗作,她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