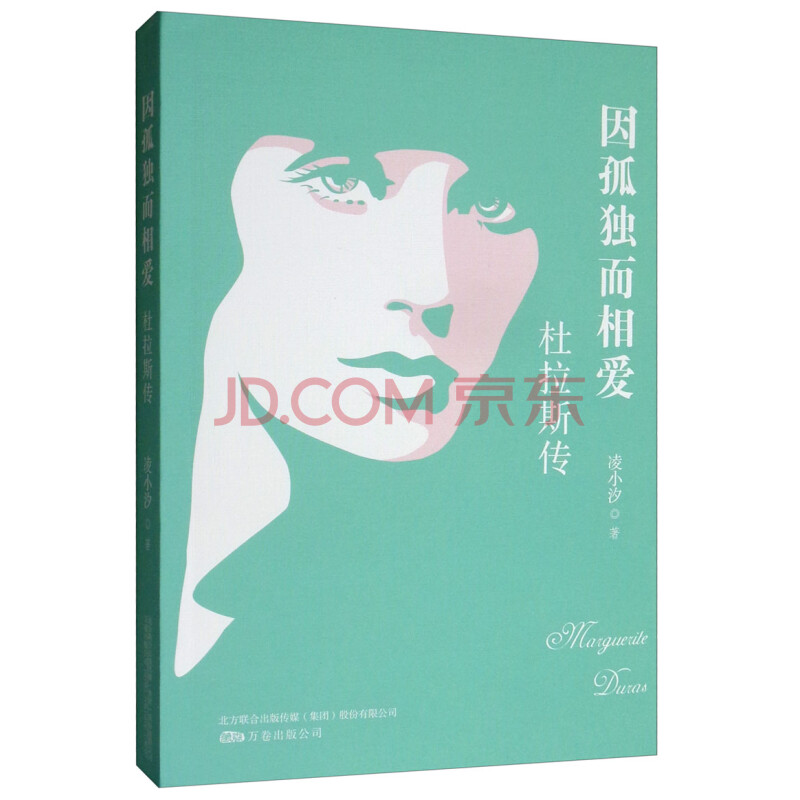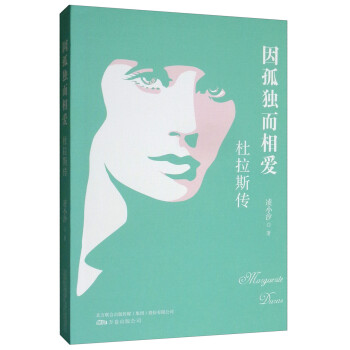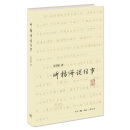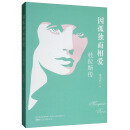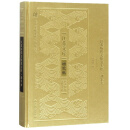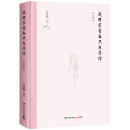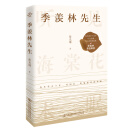内容简介
全世界永远的《情人》,玛格丽特·杜拉斯的美丽与孤独。探寻孤独、爱情、写作之于人生的意义,《因孤独而相爱:杜拉斯传》抒写杜拉斯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
精彩书评
★爱之于我,不是肌肤之亲,不是一蔬一饭,它是一种不死的欲望,是疲惫生活中的英雄梦想。
——玛格丽特·杜拉斯
目录
第一章 不会结束的童年
我出生在亚洲的河边
云南:甜的、涩的、野性的
从河内宅院到金边庄园
帕尔达朗的内内
百鸟平原
亲切的小哥哥
抵挡太平洋的堤坝
第二章 毁灭吧,她说
西贡市国立中学的少女
女人的美,是一种奥秘
莱奥,莱奥
肌肤有一种五色缤纷的温馨
吻在身体上,催人泪下
我们不能停止相爱
将来是什么?将来就是分开
他将至死爱着她
第三章 迷恋是一种吞食
十八岁,我已经老了
我有一个情人
未来信件:请给我谈爱情
战火纷飞的年代
死亡也能施洗礼
我的生活是一片沼泽
肮脏的人,我的母亲,我的爱
用身体参与写作
第四章 她以孤独打败时间
电影岁月:另一种爱情
1980年夏:最后的情人来临
为了创作您,我要先毁掉您
爱你,爱我,爱得更热烈
爱你备受摧残的面容
一生中黑暗的悲伤
在坟墓里,我永远十五岁
附录这就是一切
杜拉斯经典语录
杜拉斯相关评论
杜拉斯创作年表
参考资料
试读
《因孤独而相爱:杜拉斯传》:
在那里,七岁的玛格丽特除了在母亲的学校接受知识之外,她也像许多同龄的孩子一样,会趁父母不注意的时候,跑到街角的小卖部里去买糖果吃。有时,与小哥哥玩耍累了,就会坐在幽寂的百叶窗后,聆听湄公河上舢板艄公的长长号子:“来呦来呦噻,来呦来呦瑟,来呦来呦噻噻瑟……”艄公清越的声音掠过窗外的槟榔树,也掠过她那与年龄不相符的心智,只是彼时彼刻,没有人知道,这时光里的一切都即将和生死离别有染,年华的篇章将无辜碎裂,不忍卒听,不忍卒读。
金边虽风景优美,却依旧有着“热得要死”的气候,每年都有很多人因患热病死亡。1921年春,玛格丽特的父亲亨利再次病重,工作也随之被迫停止,初夏时,已然到了卧床不起的境况。
是年4月,亨利被送回法国进行紧急救治。玛丽带着孩子们为他送行,她有些不祥的预感,却又依旧怀有希望,自己的丈夫一定会和从前一样,经过治疗后将再次返回越南,返回他们相识的地方。可是他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金边,终是成为一家人的伤心之地。
同年9月,医院宣布了亨利的病情,声称他患的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病,身体已经极度虚弱,必须休长假进行严格的治疗……而事实上,病人膏肓的亨利已经无药可治。在医院日渐消瘦的他,躺在病床上回溯前尘往事,或许是依循内心深处对前妻爱丽丝的情意,深知自己时日不多之后,他还是选择了把生命中最后的时光,留给了他的另外两个孩子——与前妻所生的两个孩子:让与雅克。
在家乡的普拉提耶庄园,亨利安静地等待着死神亲临。他拒绝了一切外界的探访与医疗措施,他知道,死神召唤他太久了,他再也逃不掉了。去世的时候,帕尔达朗的天空异常清朗,他的眼睛一直看着窗外,唇边有浮动的微笑,仿佛与最好的记忆重逢。
“我母亲就是在这个大宅子里面得到父亲的死讯的。”
玛格丽特与母亲、哥哥们依然住在金边的大宅子里——那所得益于父亲职位才能住进去的古老王官,周围的花园里满是报丧鸟。也正是在那里,收到了父亲的死讯。
而她的母亲告诉她——在电报到来的前一天晚上,她就知道丈夫不在人世了。是夜,她看见一只飞鸟,疯狂地冲着她叫唤,然后拍打着翅膀,在屋内寻找,久久盘旋,直至最后消失在王宫北向的房间里……那只飞鸟,只有她一个人能看见,那个房间,正是丈夫平时办公的地方。
玛格丽特记得,就在得知父亲过世的消息的几天之后,她的母亲,再次向她证明了自己的预见能力,以及对死亡感知的能力。也是在半夜,她被母亲的尖叫声惊醒,她看到母亲脸上出现了一种平日生活中难得一见的恐惧与脆弱,母亲喊着“救命”,并向孩子们讲述了所见的一幕,就像讲述一个冗长的故事:她看见了她的父亲,在法国农场居住的亲生父亲,就坐在她的对面。
……
前言/序言
玛格丽特,在法语中,是一个与雏菊音义相同的词。玛格丽特·杜拉斯很喜欢自己的这个名字,就像喜欢波德莱尔的诗歌一样。
她曾说,波德莱尔是她最喜欢的诗人。他们都喜欢探索痛苦中的黑暗领域,喜欢在生命的黑洞中获取隐秘的恩泽,喜欢那些带有毁灭色彩的词:死亡,灰烬,疼痛,疲惫,虚无,眼泪,恐惧,血液……
恶之花,罪恶之花,痛苦之花,相传该花其色冷艳,其香浓远,其态诡俏,其格高幽,孤独地盛开在地狱边缘,美丽而沧桑,可迷惑众生。
“我是一朵花。我身体的各个部分都在阳光下爆裂,我的手指脱离了我的手掌,我的双腿脱离了我的肚子,直至我的发根,我的头颅。我感觉到初生时的疲惫,终于降临于世的骄傲的疲惫。”
名字是人生接受的第一种命运,其次则是地点。
玛格丽特·杜拉斯出生在越南。一个世纪前,在越南的嘉定区降临于世,带着殖民地永恒的疲惫,沐浴着暴烈的雨水与阳光,长大成人。从出生到十八岁,除几次短暂的旅程外,她都生活在那里。那里是她真正意义上的故土,一如她所说:“我,我曾有过森林、雨水,有过我的出发点。我的根在越南的土地上。”
浑浊的湄公河,如创世纪的水源,生命内外,一切由此滋生。贫穷与绝望,占据了她的童年与青春,痛苦的记忆侵袭生命,并贯穿她日后的所有作品。“我的一生都在耻辱中度过。”应该说,她在越南所经历的耻辱感,跟随了她的一生,并成为不可驱逐的阴影。
在殖民地,玛格丽特·杜拉斯的身份很尴尬——她分明是白种人,地位却比不上一个有钱的本地人,尤其是父亲去世后,这种尴尬,更是无处不在。她曾被自己的同胞驱逐出贵族网球场;她曾目睹母亲被地籍管理员骗光全部积蓄,继而在苦难的折磨下带着整个家庭一步一步陷入疯狂;她曾在少女时代,穿着破旧的裙子,涂着鲜艳的口红,在轮渡上遇见第一个情人……
如此,在后来的写作中,回忆便成了她的线索、道路,一遍一遍带她重返那片茫茫泽国。一切的故事,都是从那个源头而来。摇摇欲坠的吊灯,不断倾泻在棕榈树上的雨水,酷热的凝重的金属一般的时间,软糯而黏稠的越南话,幽深的热带森林,黑豹与爬虫出没的沙滩,被太平洋冲毁的堤坝……以及,爱。
写作与爱情是玛格丽特·杜拉斯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两件事情。
爱情有无限可能,却始终不能成为生命中最大的自由。于是她用文本重新构造世界,构造无数的生命。她把故事写在纸上,写在图像上,写在声音里……写,不停地写,与酒精一起,与情欲一起,只有写作,才能让内心的暴力找到宣泄的缺口。
她的爱是一曲绵长的挽歌,带着无尽的庄严与哀荣。从十五岁半遇见中国情人开始,她就在用一种特别的方式,索取爱,像暴烈地填补某种饥饿一样。
“迷恋是一种吞食。”她说。在她的世界里,迷恋带着饥饿的色泽,是一个女性而孤独的词。她将这个词从身体抽离,并一寸一寸嵌入内心,与欲望融为一体。
即便是到了迟暮之年,她与小情人扬·安德烈亚在一起,那种索取欲,也依旧猛烈异常。写作,恋爱,只争朝夕。她飞扬跋扈,喜怒无常,专横得像一个女王,却又孱弱孤苦,深情柔软,像一个老小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