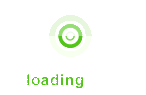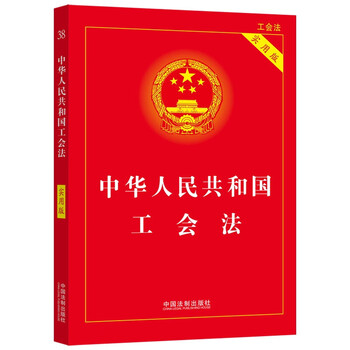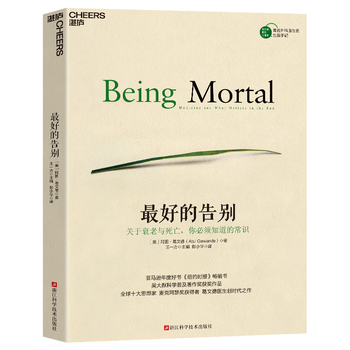内容简介
《众生家园:捍卫大地伦理与生态文明》(In Defense of the Land Ethic:Essays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1989)是J.贝尔德•卡利科特的代表作之一。本著致力于梳理、捍卫和扩展奥尔多•利奥波德的环境哲学核心理念——“大地伦理”(land ethic),其论域覆盖了当代西方环境哲学的重要话题,反映了北美环境哲学产生的独特历史背景,同时预见性地涉及了当代环境哲学的前沿论题,为当代环境伦理的哲学和科学观念基础做了有力的论证。
目录
导论真正的工作
第一编动物解放与环境伦理学
第一章动物解放:一项三边事务
第二章评汤姆·里甘之《动物权利案例》
第三章动物解放与环境伦理学:重归于好
第二编一种整体主义环境伦理
第四章环境伦理要素:伦理关注与生物共同体
第五章大地伦理之观念基础
第六章生态学之形而上学内涵
第三编环境伦理学之非人类中心主义价值理论
第七章休谟是/应当二分法及生态学与利奥波德大地
伦理之关系
第八章论非人类物种之内在价值
第九章内在价值、量子理论与环境伦理学
第四编美洲印第安人之环境伦理学
第十章传统美洲印第安人与西方欧洲人对自然之态度:
一种概观
第十一章美洲印第安人之大地智慧?:澄清论题
第五编环境教育、自然美学与外星生命
第十二章作为教育者的奥尔多·利奥波德论教育,及其当代
环境教育语境下之大地伦理
第十三章利奥波德之大地审美
第十四章伦理关注与外星生命
注释
索引
译后记
致谢
试读
当1我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一所大学得到我的第一个职位时,我便满怀热情地开始了我的哲学生涯。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特别是在学院与大学的校园里;那也是一个危险的时代,特别是在美国南部,我在那里找到自己第一份真正的工作。对一位理想主义的青年学人而言,当时正有三种严重的社会现象,既作为挑战也作为机遇矗立在人们面前:民权运动、和平运动与环境运动。对我而言,这三者中存在最大哲学机遇与智慧挑战的,似乎就是被称为“安静的危机”[quiet crisis,此乃斯图尔特?尤德尔(Stewart Udall)的著名用语]之环境危机。
我被卷入美国南部的民权运动与和平运动,未能得到当时雇主的理解。所以,1969年,我在威斯康星州(Wisconsin)的中部沙县找到一份新工作。当时我并未意识到,自己已处于正在兴起的生态意识(ecological consciousness)与良知(conscience)的精神中心。
环境保护学院(School of Conservation)[即现今之自然资源学院(College of Natural Resources)],为威斯康星州立大学斯蒂文斯点(Wisconsin State University?Stevens Point)[即现今之威斯康星斯蒂文斯点大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Stevens Point)],铸造了鲜明个性。加盟该校之哲学系不久,我即建议开发一门全新的、叫“环境伦理学”(Environmental Ethics)的课程。它被设想为一门可以吸引大多数森林、野生物管理,及其他相关专业学生的课程,亦可额外允许我拓展如此预感:生态学(ecology)是一个蕴含着许多革命性哲学观念的宝库。随着时间的推移,哲学界少数其他学人也在不同地方推出类似课程。因此,起初,环境哲学仅仅是学院与大学周日课程中的一种相关物,有常任教职的哲学家们在这些学校纯属偶然地被激发开设和教授这门课程。在环境哲学家中没有或很少有一个共同体,直到尤金?C.哈格罗夫在20世纪70年代2后期创办了《环境伦理学:环境问题之哲学方面的跨学科期刊》(Environmental Ethics: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Dedicated to the Philosophical Aspects of Environmental Problems, 该刊于1979年创刊)。
自此,我们这些曾相对孤立地在此领域工作的人对于什么是环境伦理学与环境哲学开始形成一些很不相同的观念。有些人将它理解为应用伦理学的一个分支,就像生物医学伦理与企业伦理所做的那样――这二者也产生于大致相同的氛围与时期。[2]据此,新的、奇异的技术――像核动力与遗传工程――已给人类带来新的、奇怪的环境危险。对此,以前的人类道德哲人未曾想见(或者,当代领先的元伦理学家们并不准备屈尊关注)。所以,环境哲学的任务便是将环境哲学家们自己喜欢的标准的道德理论――康德的道义论(deontology)、边沁的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密尔
又译作“穆勒”。――译者注的功利主义、罗尔斯的正义论等――应用于由新技术所造成的新的伦理困境,这些新技术已如此剧烈、危险地改变了“人类的”环境。由于西方道德哲学已然压倒性地(若非全部地)属于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cism),亦即排他性地聚焦于人类的利益与人类的内在价值(或人类的经验),所以环境进入伦理学(如此视野下的环境伦理学)仍属于人类相互活动的领地。可以说,环境被如此对待:在人类道德主体与道德客体间,它是一个价值中立的向量。
将环境伦理学想象为一种应用伦理学,环境伦理学通常便是问题导向的。比如,学者们可能关注燃煤电器与其他使用或制造烟囱的工业所造成的酸性气体问题,努力找出谁应当因酸雨问题而受到谴责,以及如何对那些其“自然资源”已然受损的人们做出公正的补偿。或者,学者们可能会关注核设施的处所,以及以不公正、不自愿的形式将危险强加于一个国家的不同人群所引发的伦理问题。除了显然的伦理问题,像酸雨与核电站选址之类的议题还涉及复杂的技术问题(如人们对阳光中悬浮物的反应,以及低水平辐射扩散所造成的致癌潜在威胁问题)、复杂的经济问题(如工厂除尘的成本效益,以及确定每一美元旅游收入的准确增值因素),以及复杂的国际法与公共安全问题。
其他环境哲学家担心:在人们关注此类困惑时,如规则、平衡、表格、图表、合法技术,以及有关环境议题的自由主义、功利主义、平等主义等理论的相对伦理优势,更为深层的哲学问题,诸如自然环境自身的价值,以及我们对自然本身的责任(若有的话),却被忽略3了。他们觉得,若环境伦理学仅满足于将西方的规范伦理理论应用于新的、复杂的环境议题,将此理论做一种新的应用,那么最基础的伦理问题在环境伦理学中就将没有地位。这些环境哲学家将致力于拓展传统的西方伦理理论,他们将非人类存在物纳入伦理学的直接受益者之中。[3] 然而,传统西方伦理理论的弹性是有限的,因此,最合理的拓展至动物而终――甚至并非所有动物均被包括在内。[4] 被设想为对道德的增加性拓展,能够超越物种界限的环境伦理学便因此而与动物福利伦理学(animal welfare ethics)高度一致――作为“动物解放”(animal liberat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