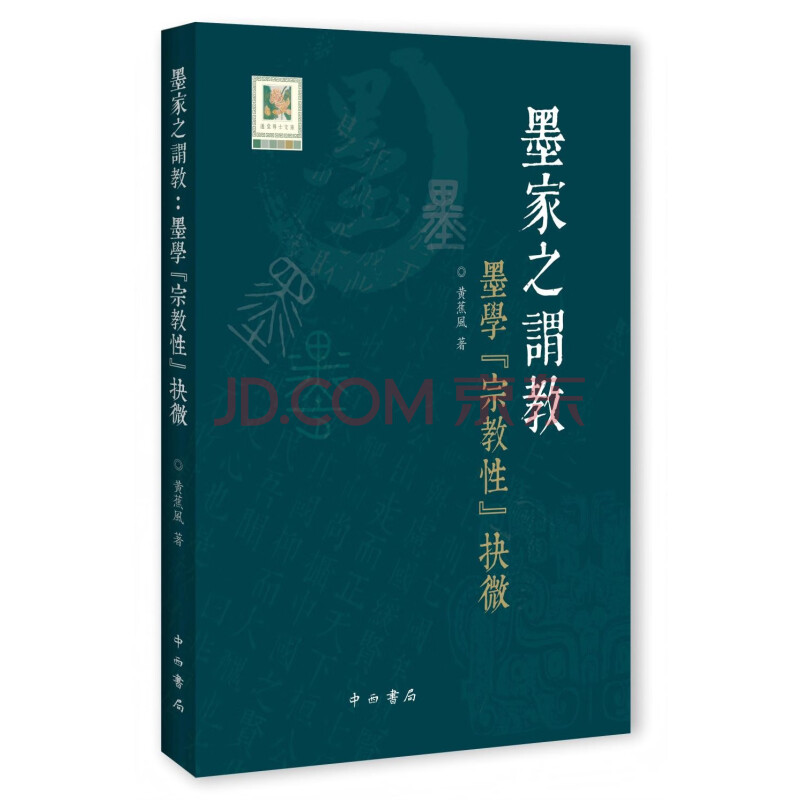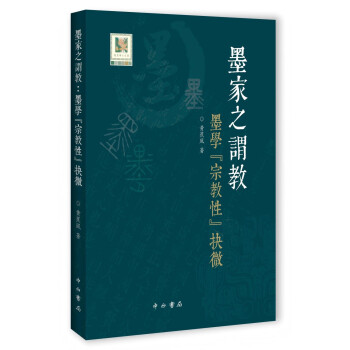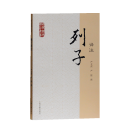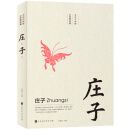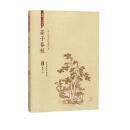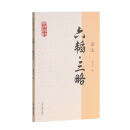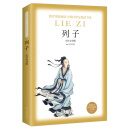内容简介
本書圍繞"墨家之謂教"這一核心問题,從墨家的宗教思想、墨家涉及的宗教倫理辯難、墨家的宗教形態以及墨家與基督教之間的對話四方面探究墨家的"宗教性"。首先分析《墨子》書中的《法儀》篇,作為墨家判斷言論、事理之效能、效用的"三表法",以及"天志""明鬼""非命"三論,深入探究墨家思想的宗教维度。在此基礎上,嘗試從宗教的角度對墨家所面臨的一些經典質疑給出新的回應,如反乎人情(非禮非樂、節葬節用)、陳義過高(兼爱不可能)、邏輯不自洽(尊天事鬼却又非命)等。然後運用宗教學的研究方法推测墨家的宗教形態,就墨家之特性、信仰中心、神論模式,墨子作為"教主"的人格特徵,以及墨家的建制組織,分别展開研討。最後考察代以來中國基督教徒關于"墨教"的論述,呈現作為"墨教"的墨家與基督教之間的對話成果。本書以宗教之維介入墨學研究,有利于創造性地诠釋千年绝學墨學,開創當代墨學研究的新路径。
目录

试读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人们讨论“墨家之谓教”或是“儒家之谓教”,均是在追问同一个问题:除了自域外传入的佛教以及吸收佛教资源后完成创教的本土宗教道教(这其中亦包括诸般被称为“小传统”的民间信仰)以外,长期以来被人们目为思想学派的儒家、墨家,是否同诸宗教一样,具备被称为宗教的要素。
儒墨二家之思想分歧,不在“要不要复古”,而在“如何复古以改造社会”。今人或以墨家“非儒”、儒家“辟墨”,谓儒墨之间冰炭不能兼容,此实是将二家主张推至极端所産生的误解。尤于墨学而言,其观点特别容易被无限推衍,例如将“非乐”引申为“无乐”,将“节葬”引申为“无葬”,从而得出墨家主张“禁止一切音乐”和“不需要服丧葬埋”的极端结论。
墨子并非否认血亲关系存在厚薄、多寡的社会现实,而是借兼爱论设置一个伦理道德下限,即爱利自己的同时不能戕害别人。也就是说,墨家是设置一个道德下限作为社会群体必须遵守的共义,而伦理高标则是在保住这个底线的基础上赋予人们建构其情感关系的自由。
“尊天事鬼”作为墨学核心义理,体现了墨家神义论和酬报神学的独特看法。借用鬼神威吓伸张正义———“善必得赏,恶必得罚”,是墨子解决现世“德福不一致”之伦理困境的手段。
前言/序言
序一
长期以来,学界对于墨家,主要是将其作为先秦诸子之一来进行研究。从先秦诸子百家的角度来看,墨家与其他诸子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其乃是宗教性相对较强的一个学派。惜乎百多年来,学界对于这一点的重视始终不够。
即如本文所言,近代以来,儒家衰微的同时,“诸子”逢时复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支流和小群的墨家被学人重新发掘出来,用以比附和对接西方先进文化,蒙尘千年的墨家思想一度得到高度重视。当代学人研究墨家主要是遵循哲学史、思想史以及墨家现代转换的“新墨家”理路,多是继承近代墨学复兴的学术理路。当代墨学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在墨学精神、墨子伦理、墨家道德、墨学与当代社会之关系、墨学的现代性阐释等议题,“墨教问题”则很少有人关注。而目前学界有关墨家宗教问题或曰墨学宗教向度的研究,多注目于墨家宗教思想;即便在此领域,也以“非命”“尊天”“事鬼”等“墨学十论”的义理研讨为主,缺乏系统性研讨。
在我看来,儒墨在渊源上多有重叠之处,学界多认为儒出于上古的巫史,与祭祀礼仪关系密切。而墨家,《汉书·艺文志》说是出于“清庙之守”。“清庙”学界多认为是“明堂”,“清庙之守”是管理郊庙祭祀礼仪的官。《吕氏春秋·当染》载:“鲁惠公使宰让请郊庙之礼于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后在于鲁,墨子学焉”,这帮助墨家与巫祝有渊源关系。吕思勉说:“明堂为神教之府。明堂为神教之府教中尊宿,衣食饶足;又不亲政事,遂有此高深玄远之学。儒墨二家都推崇尧、舜、禹这些古代圣王,传承“六艺”:“孔子、墨子皆修先圣之术,通六艺。”(《淮南子·主术训》)“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韩非子·显学》)尽管相较而言,墨家更推崇大禹一些,但墨子最初学儒,所以儒墨可以说是“同源一体”。后来墨家从儒家分化出来,与儒家分庭抗礼,取得了平分秋色,甚至后来者居上的地位。儒墨互相攻击,不但拉开了战国百家争鸣的序幕,而且儒墨之争贯穿于整个战国时期,“是先秦各学派中思想斗争最激烈的”。《淮南子·要略》载:“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这帮助墨子最初受业于儒家,后因不满儒家维护“尊尊亲亲”,大讲礼乐,对儒家强调的繁文缛节和靡财害事的丧葬报有疑虑,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儒墨于是成为旗鼓相当的显学。“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韩非子·显学》“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于杨,即归墨。”(《孟子·滕文公下》)
其实儒墨互攻之外,儒家也有对墨家的肯定。墨子劳苦功高,舍身忘己,消弭战争,孟子认为这是一种与儒家一样“士志于道”的精神,对此表示由衷的赞叹:“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上》)
秦汉之人经常把“孔墨”或“儒墨”相提并论。《庄子·天运》:“天下大骇,儒墨皆起。”《文子·自然》:“孔子无黔突,墨子无暖席。”《吕氏春秋·当染》:“孔墨之后学,显荣于天下者衆矣,不可胜数。”《吕氏春秋·有度》:“孔墨之弟子徒属,充满天下,皆以仁义之术教导于天下。”班固《答宾戏》:“是以圣哲之治,栖栖遑遑,孔席不暖,墨突不黔。”《盐铁论·相刺》:“今文学言治则称尧舜,道行则言孔墨,授之政则不达。”因此,我赞同韩愈“孔墨相为用”之论。
如果从宗教视角来看,儒墨都有宗教的渊源与内涵。我觉得儒家的形成主要是传承并发展了上古圣王的道德传统,春秋时代从孔子开始发生了“神文”向“人文”的转型;而墨家的形成主要传承了上古圣王的事功传统,春秋时代从墨翟开始未曾发生“神文”向“人文”的转型。所以,尽管有“儒家是教非教”的“儒教问题”,但宗教只是儒家次要的或者说附属的属性,以祭祀为代表的宗教仪式也主要是形式的意义,而“墨家之谓教”的“墨教问题”可能是墨家主要的或者说根本的特性,从宗教角度研究墨子的教主人格、墨家的宗教形态、宗教思想、宗教功能、宗教伦理等问题可能更合乎墨家的本质。只是近代以来对宗教的相对消极的认识,使得学者不愿从正面肯认“墨教问题”,在思想史研究上留下了巨大的空白。黄蕉风博士长期以来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这部作品就是他最新的研究成果。
黄蕉风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围绕墨子的教主人格、墨家的宗教形态、宗教思想、宗教性质、宗教功能、宗教伦理等方面展开学术讨论,并将其称为“墨家之谓教”的“墨教问题”。他认为所谓“墨家之谓教”这一问题略有三层含义:其一,墨家是否为宗教?若是,则其为何种类型之宗教;若否,则何以历代有人以墨家为墨教?其二,若墨家诚非宗教,则其是否具有“宗教性”,或曰墨家是否是“准宗教”?其三,墨家肖似宗教之处主要体现在思想义理上,还是体现在建制组织上?他指出,“墨家之谓教”的“墨教问题”一直以来为近代墨学发展史所遮蔽,世人在“墨家之谓教”的“墨教问题”上多持“墨家非宗教”的观点。“墨教问题”是近代以来与“儒家是不是宗教”或曰“儒家之谓教”相类似的问题。黄蕉风的问题意识是从清末民初的墨学复兴浪潮中对墨子学说及墨家学派的创造性诠释和创造性建构而来的,他认为墨学因其具有与科学、民主、博爱、自由、平等、人权、理性等与西方文明若合符节的思想资源而重新得到时人的重视。墨学在此时担当两个作用,一是对接西方文化、比附西学价值;二是取代儒学,成为“中体西用”的新范式。但是逐渐形成了“在一方面高扬墨子积极救世的人文主义情怀和墨学中的自由民主科学人权精神,一方面又贬墨子宗教教主式的权威人格和墨学中有涉宗教信仰的思想为封建迷信,对后者轻视或干脆避而不谈”,使得以宗教维度来诠释墨家思想的学术研究不多,缺乏系统性探讨。
本书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对墨家的宗教向度进行系统研讨。作者在中西古今文化冲突融汇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立足墨家元典,从文本解读入手,通过正本清源、接续传统、返本开新,推动了墨家宗教方面研究的深化和拓展。其中涉及儒墨关系的研究,黄蕉风认为这是自“儒墨”形成以后的大问题。墨家从儒家分化出来以后就成为儒家最早的反对派和论敌。《墨子·非儒》对“孔某”讽刺、挖苦,差不多是“凡儒家支持的,墨家就反对;凡儒家反对的,墨家就支持”,孟子则骂墨家“无君无父,是禽兽也”,荀子在《荀子·非十二子》中谈到“不知壹天下、建国家之权称,上功用,大俭约而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辨异、县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墨翟、宋鈃也”。“儒墨互攻”是中国思想史上最早、最激烈、影响最深远的学术论战,是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的前奏。墨家也崇尚尧舜之道,特别推崇大禹。对此,黄蕉风认为“墨子之学,乃学儒而反儒,脱儒而近儒”。这个表述很到位,帮助了儒墨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