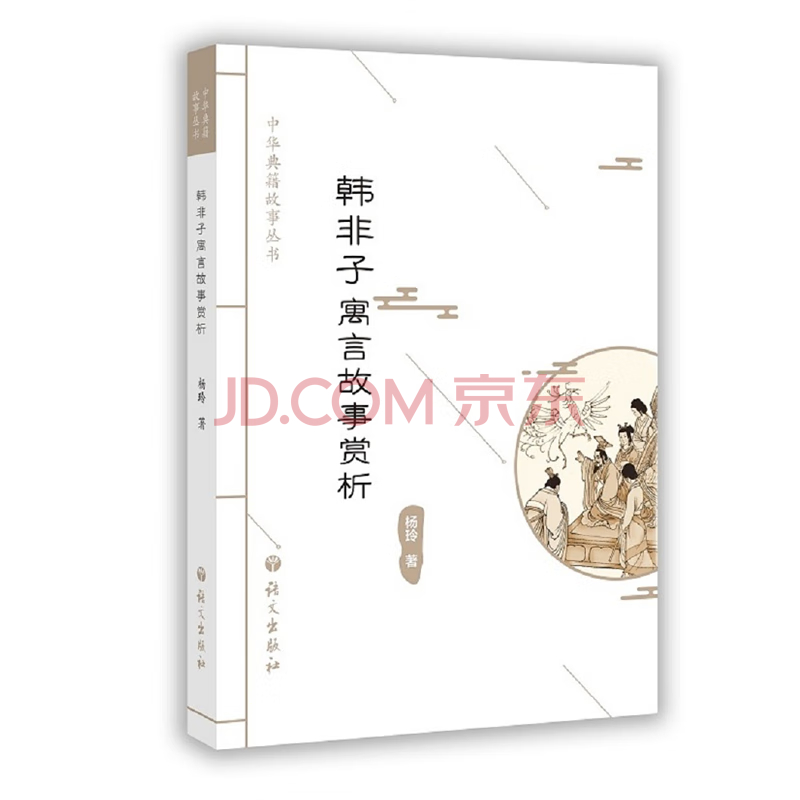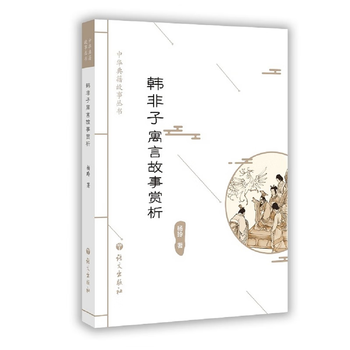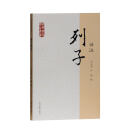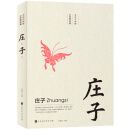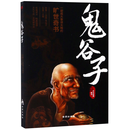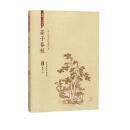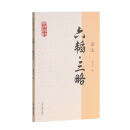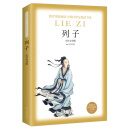内容简介
本书精选了《韩非子》中《说林》《喻老》《十过》等二十章的寓言故事,其中既有耳熟能详的“老马识途”“自相矛盾”“买椟还珠”等,也有深具启发意义的“郢书燕说”“自见之谓明”“赵襄主学御”等,共计189则寓言故事,几乎囊括了《韩非子》中所有的优秀寓言故事。本书对所选的每篇寓言均进行了简要注释和贴合现实社会的赏析,有助于读者理解寓言故事、丰富古代文化知识、启迪人生智慧。本书的作者是研究法家思想多年的古代文学专业教授,所选的寓言故事以陈奇猷先生《韩非子新校注》为底本,参考多家注本而成,具有一定的可读性。
精彩书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讲中国故事是时代命题,讲好中国故事是时代使命。”
前言/序言
说到先秦诸子,国人立刻想到的是儒道法墨;说到先秦法家,国人首先想到是《韩非子》;说到《韩非子》,国人脑海中浮现的是那个宁可相信尺寸而不相信自己脚的郑人,那个躺在大树下等着再次捡到兔子的农夫,还有那个因为夸耀自己的矛最尖锐盾最锋利而被别人问得张口结舌的楚人……。诸如《郑人买履》《守株待兔》《自相矛盾》等产生于《韩非子》中的寓言故事在中国已是妇孺皆知,但是对于韩非在寓言上的成就,《韩非子》寓言在中国寓言史上的地位,我们了解得却不够,对《韩非子》寓言的价值和意义认识很有限。
“寓言”一词出自《庄子》。《庄子·寓言》有:“寓言十九,藉外论之。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陆德明《经典释文》解释说:“寓,寄也。以人不信己,故托之他人,十言而九见信也。”《庄子》所说的寓言指寄寓性的言论。庄子之所以要用寓言说理,是因为他知道一个人不会轻易相信另一个人,一个人说的话即使完全真实也不是那么容易可以让他人接受。但是如把自己要说的话托付给第三方来说,别人就不会怀疑。这就像父亲不能为儿子做媒找媳妇。父亲夸赞儿子,在别人听来不免掺杂私情,因而没有可信度。所以,为了取得读者的信任,让他们相信自己说的话,庄子把要讲的道理用寓言故事表达出来,以此达到目的。由此可知,《庄子》中的寓言主要是作为一种说理方式和议论的论据而存在的。但是因为这些寓言故事在论证《庄子》思想观点的同时,还起到因小见大、深入浅出的比喻说明作用,从而与后世作为文学体裁的“寓言”不谋而合。当代研究寓言的著名学者陈蒲清先生认为,寓言必须具备两个基本要素:一是有故事情节,二是有比喻寄托(《中国寓言史》,第2页)。也就是说寓言一定是比喻,但比喻未必是寓言,只有有故事情节的比喻才是寓言。由此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先秦诸子典籍中比喻频见,但真正以寓言著称的只有《庄子》和《韩非子》。庄、韩二人是先秦诸子中最擅长创作寓言,寓言作品数量最大,质量最高的两家。战国寓言作品计一千两百余则,源自《庄子》的有186则,源自《韩非子》的有323则(不同的统计者略有差异,多的至四百,但都不少于三百余则),《列子》99则,《吕氏春秋》283则,《战国策》54则。可以看出《韩非子》寓言所占比例最大。战国寓言创作至韩非达到高峰,韩非是战国寓言的集大成者。他所编著的《储说》《说林》是我国最早的寓言专集,也是世界现存最早的寓言集(赵逵夫《论先秦寓言的成说》,《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公木先生评价说:“它们(指《储说》《说林》)的出现,不但突破了先秦寓言依附散文而存在发展的窠臼,使先秦寓言有了光灿夺目的收尾,而且还使我国寓言文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独立存在的新阶段。”(《先秦寓言概论》,第71页)丰富多彩的寓言成为《韩非子》在文学方面最显著的一个特点,所以刘勰在《文心雕龙·诸子》中说:“韩非著博喻之富。”意即韩非以举事例做比喻说明道理而著称。这些事例就是寓言故事,它们是韩非阐述治国理论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借助这些寓言故事,深奥枯燥的思想变得浅显易懂、生动有趣,鲜明地体现出寓言是“哲理的诗篇”、“比喻的最高境界”的特点。虽然这些寓言产生于两千多年前的战国,但今天仍然有显著的时代价值和意义。
韩非子寓言的价值和意义是多方面的。
从文学角度说,这些寓言故事不仅是形成韩非子散文峻峭犀利文风的关键因素,同时还是中国古代小说的雏形。《和氏璧》中塑造的执着悲壮的卞和形象,《纵鳖饮水》中卜子妻笨拙却不失可爱的想法和举动,无不显示出早期小说的特点。
从思想上说,《韩非子》寓言从不同角度解说、传播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治国观念。《扁鹊见蔡桓公》以治病喻治国,告诉为国者要具备见微知著的眼光和消灭隐患于萌芽状态的能力。《棘刺为猴》提醒执政者不能沉溺于动听的言语,而要从实际出发辨别言语的真实性和可操作性,如此才能避免在治国中误入歧途。
从文献角度说,韩非子寓言以历史故事为主,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还来自于一些已经亡佚的典籍,因此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譬如《自见之谓明》通过“楚庄王”与杜子的对话说明人容易发现别人的缺点,却看不到自己的缺点;有国者容易看到其他国家的问题,却常常认识不到本国的不足。“楚庄王”与杜子二人的对话中提到庄跷为盗于楚一事,而庄跷实为楚顷襄王时人,因此有人认为这是韩非的一个错误。在另一则寓言《春申君之妾》中,韩非开首即言“楚庄王之弟春申君”,而史书的记载却是楚申君为臣于楚顷襄王、考烈王时代,而非“楚庄王”时。于是有学者认为这又是韩非的一个错误。但经过钱穆、杨宽、周勋初等先生考证,这里的“楚庄王”就是楚顷襄王(详见钱穆《先秦诸子系年·楚顷襄王又称楚庄王考》),而非那个一鸣惊人、问鼎中原的楚庄王——楚穆王之子芈旅。同时通过以上两个寓言故事我们还知道,春申君是楚顷襄王的弟弟,这是《史记》中没有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