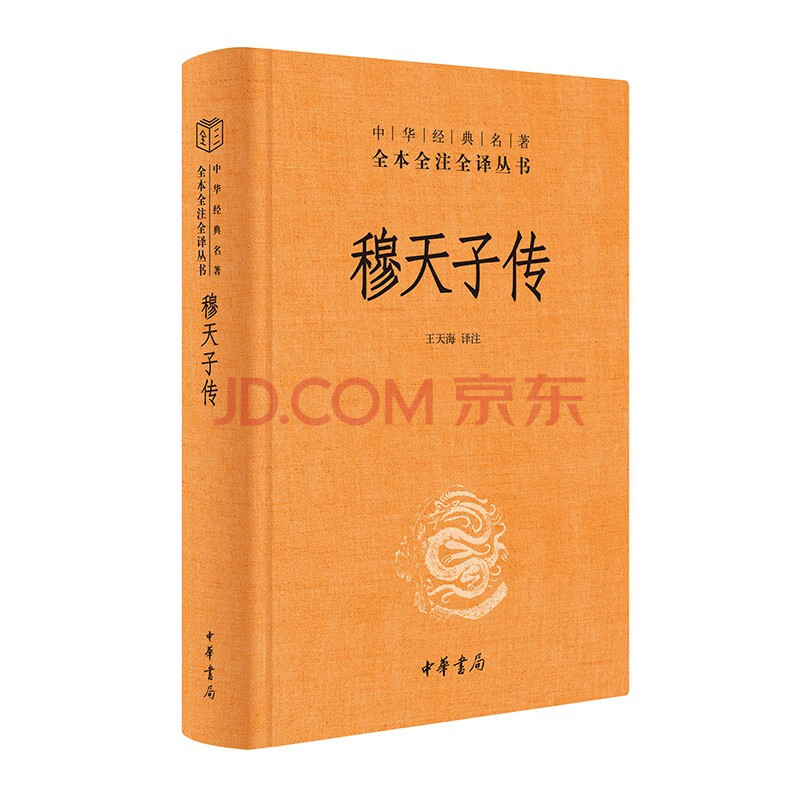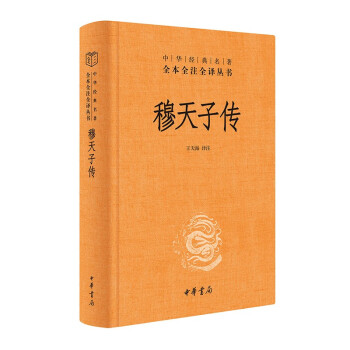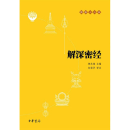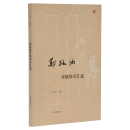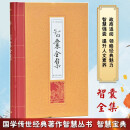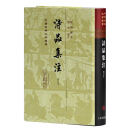内容简介
1700多年前,战国魏襄王墓被盗,一批竹简古书重见天日,这就是著名的“汲冢竹书”,其中只有一部先秦文献较完整地流传到今天,这就是《穆天子传》,又名《周王游行》。该书记述了西周中期周穆王远征西域的事迹,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全书共六卷。前四卷记述周穆王从宗周出发,北征犬戎,继而出雁门、入河套、祭河伯、登昆仑、会见西王母、狩猎大旷原,最后返回宗周的经历。卷五专记周穆王东巡河南诸地事,是穆王巡狩中原的实录。卷六原为杂书中的一篇,名为《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主要记述周穆王东巡河济之间,其所宠爱的盛姬去世,穆王为其举办盛大隆重葬礼事。全书雄奇浪漫,颇具小说色彩,故一度被认为是虚构的小说,而实际上它应该是一部记载周穆王西征东巡的实录性散文,是一部具有很高史料价值的历史文献。本次以上海涵芬楼景印天一阁刊本《穆天子传》作底本,注释中汇校勘、集释、案语为一体;题解疏解该卷内容与大意,各卷题解之后皆列有《周穆王日程经历名物一览表》,以供参考查检;译文文句畅达,便于读者阅读。并附录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发表的相关著作和论文,为读者进一步研究提供思路与线索。
目录
前言 ……………………………………………………………… 1
卷一 ……………………………………………………………… 1
卷二 ……………………………………………………………… 59
卷三 ……………………………………………………………… 139
卷四 ……………………………………………………………… 183
卷五 …………………………………………………………… 247
卷六 …………………………………………………………… 318
附录:《穆天子传》序 ………………………………………… 397
参考文献 ………………………………………………………… 410
试读
3.2
乙丑①,天子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②,西王母为天子谣③,(徒歌曰谣。)曰:“白云在天,山?(“陵”字。)自出④。道里悠远,山川间之⑤。(间,音谏。)将子无死⑥,(将,请也。)尚能复来。” (尚,庶几也。)天子答之,曰:“予归东土,和治诸夏⑦。万民平均⑧,吾顾见汝⑨。(顾,还也。)比及三年,将复而野⑩。(复,返此野而见汝也。)”
【注释】
①乙丑:丁谦《干支表》:“距前一日,觞西王母于瑶池。”天海案:顾实作“七月二十九日”,亦距前一日。“乙丑”上原文有“ ”字,《道藏》本标有“□”阙文,梅鼎祚本标“阙”字,皆在“乙丑”之上。作“ ”字或标“□”阙文,皆不可通,此据删。
②瑶池:湖泊名。郝懿行云:滛,明藏经本作“瑶”,《西山经》云:“槐江之山,爰有滛水。”滛水,当即“瑶池”,是“滛”“瑶”古字通用也。小川琢治云:瑶池,是湖水之所在也。接巴里坤近傍,有巴尔库勒淖尔,为汉代之蒲类海。……据徐松《西域水道记》(卷三),则在今之镇西府西北四十余里。顾实云:瑶,《北堂书钞》百十一引同,但十六又引作“滛”。王贻樑云:瑶池,愚疑为今新疆和硕县南、库尔勒东北之博斯腾湖。西汉时名海,东汉时名秦海,亦即《水经注》之敦薨薮。此处湖光山色甚美,颇合“瑶池”之名。天海案:王贻樑之说可参。
③谣:不用乐器伴奏的清唱。檀萃云:谣者,盖西王母传道于穆王之微言,如《汉武内传》所载诸歌曲,但辞致浑融不露耳。陈逢衡云:《艺文类聚》九百四十三引、《太平御览》六十七引“天子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天子谣”,又五百七十二引“谣”作“歌”。……郭注见《尔雅·释乐》言,但以人声,不用丝竹也。顾实云:此谣辞与下吟辞,皆周人纯粹之四言诗也,是亦西王母必为中国女子之证也。卫挺生云:言西王母之谣吟二首,皆周时四言诗之佳作,自无疑义,然此皆穆王之侍从文官意译西王母伊兰语之诗辞而成之周代型古诗。……诗之意境之佳,不必为中国女子。诗之格调与词语之佳,则才艺并高侍从文官之功也。……不能以诗证明其为中国女子也。王贻樑云:顾实说非,此辞可由中原人译写,如近人以七言诗形式等译作外国人诗一样,何能即以据而断定其必为中国人呢?郭侃云:《玉篇·言部》:“谣……独歌也。徒歌曰谣。”《诗·魏风·园有桃》:“园有桃,其实心殽,心之忧矣,我歌且谣。”毛亨传:“曲合乐曰歌,徒歌曰谣。”《列子·周穆王》:“西王母为王谣,王和之,其辞哀焉。”《列子》语可为“穆王对歌西王母”之证,但因《列子》成书时代及真伪的争议,或此魏晋时所辑之《列子》文即取自《穆天子传》。
④白云在天,山?自出:“?”字,即“陵”字古文。《山海经·西山经》正引作“陵”字。檀萃云:“白云在天”者,肃肃出乎天也;“山陵自出”者,赫赫发乎地也。洪颐煊云:《文选》沈休文《早发定山诗》注、《太平御览》八引作“丘陵”。陈逢衡云:《列子·周穆王篇》:“遂宾于西王母,觞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王谣,王和之,其辞哀焉。”张湛注:“徒歌曰谣,诗名《白云》;和,答也,诗名《东归》。”衡案,《白云》《东归》皆后世摘取诗中字面以标题之,非当日有此名也。郝懿行云:李善注沈约《早发定山诗》引此文云“丘陵自出”,其注谢朓《拜中书记室辞隋王笺》引此文仍作“山陵自出”。褚德彝云:“自出”二字疑作“阻之”,“阻”字古文、“之”字篆文与“自出”字同。顾实云:下言“山川”,则此当作“丘陵”,山莫大于昆仑,犹尚称昆仑之丘也。郑杰文云:出,当为“止”之形讹。古文“出”作“出”,“止”作“止”,形近易讹。又,这首谣辞的下两个叶韵字“之”“来”在上古韵中同为之韵。“止”正为之韵。“山陵自止”言在天的白云飘到此处为山陵自然阻止,以喻穆王远道来此,且与下诗意正合。王贻樑云:褚说“自出”为“且之”,可参。天海案:褚德彝所说可从。译文且按“阻之”而译。
⑤道里悠远,山川间之:间,间隔,阻隔。檀萃云:“道里悠远,山川间之”,不能两者交通成和而生物也。洪颐煊云:里,《太平御览》八引作“路”,八十五引作“理”。陈逢衡云:上言“道里悠远,山川间之”,隐有谕王不可轻出之义。郝懿行云:李善注谢朓《拜中书记室辞隋王笺》引作“道路悠远”,《太平御览》五百七十二卷引此文“悠远”作“攸远”。郑杰文云:今检《事类赋注》卷二引亦作“理”。顾实云:谏,原作“间”。《颜氏家训·书证篇》云:“《穆天子传》音谏为间。”段玉裁曰:“案颜语,知本作山川谏之,郭读谏为间。”今据改,注同。王贻樑云:以上下文义察之,当作“间”字为是,改之不确。
⑥将子无死:希望您不会死去。意即希望您长寿。将,请求,希望。顾实云:一部《诗经》十五国风所咏,泛称男女曰子。泛称在上者亦曰子。独二雅斥及王政,往往曰天子,曰王。今西王母为天子谣,遽面斥穆王曰子,则非泛泛之称可比。据《尚书·洛诰》曰“朕复子明辟”,又曰“考朕昭子刑”,乃周公以叔父之亲,而称成王曰子也。然犹未也,桓十五年《左氏传》,载祭仲女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将享子于郊”,则女称其父,亦得面斥之曰子也。……然则《穆传》西王母者,确即穆王之女也。此谣辞曰“将子无死,尚能复来”,不能不认为有亲属上之意味者也。天海案:子,先秦尊称也。顾实之说近迂。
⑦予归东土,和治诸夏:我将返回东方,和谐治理中原各国。诸夏,指周代分封的中原各诸侯国。洪颐煊云:归,《山海经·西山经》注引作“还”。……治,《山海经·西山经》注引作“理”,是唐时避讳所改,《太平御览》五百七十二引作“洽”。陈逢衡云:穆王虽勤远略,然拳拳于中夏如此,故犹为西周之令主。顾实云:穆王自称曰予,称西王母曰汝,西王母虽为己女,而建邦于西方,则诸侯也。证以《尚书·文侯之命》篇,亦有称予、称汝者,可知周天子之出辞有体也。前封赤乌氏曰“大王亶父始作西土”,与此曰“予归东土”,明明东土、西土二名词,皆出自穆王之口,则西周以前之作西土,实逾葱岭以西,而其东土乃明指中国文言也。抑且于此可见上古东西一家,中外一人,自有区分东土、西土而为其治之必要也。卫挺生云:西王母对穆王受献而不奉献,其自视甚高,最多视穆王同等。波斯民族之王者,由来自称“万王之王”。故其称穆王曰“子”、曰“汝”,自称曰“我”。穆王亦以平等视之,而称之曰“汝”、曰“而”即“尔”,而自称曰“予”、曰“吾”。故二人之间皆平等对称,无所谓亲属父女之称呼也。郑杰文云:唐高宗名李治,故唐人改“治”为“理”,“洽”乃“治”之形讹。
⑧万民平均:万民齐心,天下统一。平均,平定统一。陈逢衡云:平均,《艺文类聚》四十三引作“乐均”。天海案:《礼记·乐记》:“子夏对曰: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正义:“修身及家,平均天下者,言君子既闻古乐,近修其身,次及其家,然后平均天下也。”《史记·滑稽列传》:“东方生曰:天下平均,合为一家。动发举事,犹如运之掌中。”
⑨吾顾见汝:顾,再来。檀萃云:帝王之道,以在宥为登真,治国、治身在于和,治均平所以得大还而相见也,彼此皆取喻于微言。然皆和平、中正,有雅颂之遗音,不若后世之激切而入于幻也。洪颐煊云:顾,《太平御览》五百七十二引作“愿”。陈逢衡云:此二诗宋赵德麟《侯鲭录》引“吾顾”作“吾愿”,是宋时所见本俱作“愿”也。顾实云:“顾见”二字,程本误作夹注。郑杰文云:今检涵芬楼影宋本《太平御览》卷五百七十二仍作“顾”。天海案:作“顾”是。
⑩比及三年,将复而野:比及,等到。而,同“尔”,即你。野,古韵读yǎ,与“夏”叶韵。陈逢衡云:尔,洪本作“而”。案,《艺文类聚》四十三引作“而”,此下洪本俱从《山海经》注改。……王母云“尚能复来”,是期望未定之辞,王答以“比及三年,将复尔野”是相见不远之义。郝懿行云:《太平御览》五百七十二卷引此文“而野”作“于野”。顾实云:答辞曰“比及三年,将复而野”,则穆王又所以有十七年之西征也。郑杰文云:今检涵芬楼影宋本《太平御览》卷五百七十二引仍作“而”。
【译文】
乙丑这一天,穆天子在瑶池上向西王母敬酒,西王母为穆天子唱道:“白云悠悠飘天上,山峦绵绵来阻挡。道路漫漫远又长,山水间隔阻友邦。祝愿您万寿无疆,希望您再来我邦。”穆天子答唱道:“我将返回东方,和谐治理华夏。万民安乐一统,我将再来见您。等到三年之后,将又来此原野。”
前言/序言
《穆天子传》是一部奇书,更是一部珍贵的历史古籍。说它奇,是因为它所记述的西周中期周穆王远征西域的事迹具有浪漫、雄奇的色彩; 说它珍贵,是因为它长埋地下数百年(《穆天子传》荀勖序文中称五百七十九年),是汲冢竹书中唯一流传至今的先秦文献。令人遗憾的是,汲冢竹书由于盗墓者的损坏、地方官府的收藏不慎,虽经西晋饱学之士荀勖等人整理、编校,留下的仍然是残阙之文。所幸的是,《穆天子传》毕竟是其中“差为整顿”的一种(见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引晋王隐《晋书·束晳传》),又赖晋人郭璞作注,故能流传到今天。
《穆天子传》自郭璞作注后,冷落千有余年,方有清人檀萃为之注疏(檀萃《穆天子传注疏》八卷,有石渠阁本、碧琳琅馆丛书本)。此后,清末至民国时期,研究《穆天子传》一时兴起了热潮,中外研究者不下数十家。新中国成立后,自顾颉刚、岑仲勉二先生著文研究以来,四十余年间,专门论述《穆天子传》的文章也有二十多篇。1994 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王贻樑、陈建敏的《穆天子传汇校集释》一书,可以说是对《穆天子传》研究前所未有的一次“总账式整理”(见王贻樑、陈建敏《穆天子传汇校集释》中方诗铭《序》)。它的价值不仅在汇诸家之校,集前贤之释,更在于随处可见作者新颖、独到的见解与思索。但是,迄今为止,《穆天子传》研究中仍存在着不少疑难问题,未能寻绎出令人信服的2
答案。这只有期待地下文物的发现,也需要人们进一步深入研究、探讨, 才能使《穆天子传》研究结出更丰硕的成果。在这里,笔者拟在前人整理研究《穆天子传》的基础上,略谈一些粗浅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