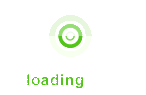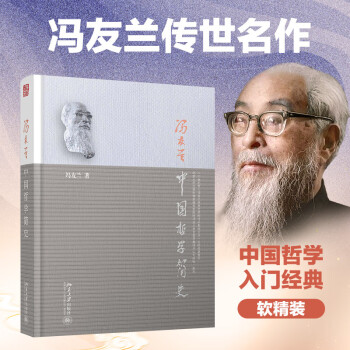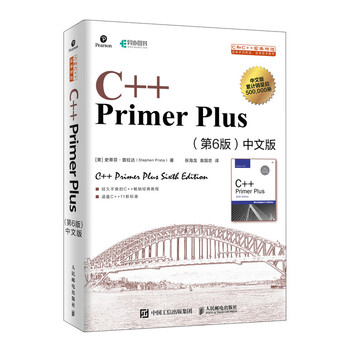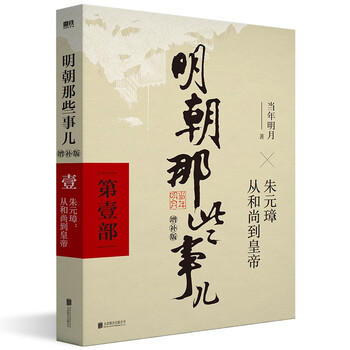内容简介
胡里奥·科塔萨尔终其一生都在经历一场诗意般的突围:用幻想构建现实,用行动打破幻想。他的作品如爵士乐般充满着幻想与即兴的成分,就像随时可能从人嘴里吐出兔子。
本书作者跟随传主脚步跑遍法国、西班牙和阿根廷,采访了科塔萨尔的妻子、亲友和同事,并实地考察了他创作《跳房子》的房间,结合历年书信与档案,探寻他的创作秘籍。本书此前已被翻译成俄语和土耳其语,如今又为中文版重新修订,堪称科塔萨尔“传记的完美形态”
目录
目录
修订版前言 两个家和一位朋友
推荐序 永远在成长的少年
前言 为什么是科塔萨尔?
第一章 1914—1939
为何会出生在比利时?
班菲尔德:童年的王国
布宜诺斯艾利斯。马里亚诺·阿科斯塔师范学校
美学派诗人
玻利瓦尔、教育和杜普拉特夫人
第二章 1939—1953
奇维尔科伊? 外省主义
未取得学位的大学教师? 庇隆主义
重返布宜诺斯艾利斯? 私人生活
《动物寓言集》
巴黎之梦? 根提利街 10 号(第 13 区)
第三章 1953—1963
爱伦·坡? 罗马之行
重返巴黎? 新的短篇小说
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翻译《追寻者》
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中奖彩票》
《跳房子》:名利双收
第四章 1963—1976 183
局外人? 对现实的承诺
故事、杂记及趣事
《装配用的 62 型》
南锥体《曼努埃尔之书》
第五章 1976—1982 254
阿根廷:“不受欢迎之人”
《曼努埃尔之书》
旅行及支持桑地诺事业
《八面体》
卡罗尔·邓洛普和马特尔街
第六章 1982—1984 295
《不合时宜》
最后一次阿根廷之行
蒙帕纳斯,1984 年:缘何魂断法兰西
后记
文学与爱:科塔萨尔的巴黎,巴黎的科塔萨尔
胡里奥·科塔萨尔年表
参考文献
试读
对于我这一代的拉丁美洲作家来说,60年代打开了不止一种视角,因为那是20世纪一个无与伦比的十年,充满了挑战、险阻与质疑。就像一直以来那样,进入写作的宇宙,不光需要文学英雄,也需要亟待推翻的陈旧偶像。然而,除了文学领域的这些偏好与排斥,更普遍的是对既定秩序和主流生活方式的反叛,写作的行为与改变世界的行动观念密不可分。显然,我们国家边缘化的现实摆在面前,一切有待改变。但我们追求的不仅仅是现实的改变,还包括所有构成贫穷和落后现实的社会以及个人行为习惯的改变。一个反叛的统一战线。
20世纪60年代令人眼花缭乱。“咆哮的二十年代”也相形见绌。切·格瓦拉1967年在玻利维亚的死亡为渴望新世界的焦灼增添了一缕道德的光辉,这个新世界应该在我们认为应当告别的旧世界的废墟上建造起来,因为披头士乐队在1962年发布他们的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就已经为这一切埋下了第一枚炸药。就在这新世界徐徐从地平线上升起的时候,胡里奥·科塔萨尔用其出版于1963年的《跳房子》为它设定了游戏规则。这些规则首先在于不接受任何既定前提,以尽可能不恭敬的方式颠倒世界,毫无顾忌或妥协。
带着对过去时代(它总是更好的)的怀旧之情可能会发现,那时候的事业,那些值得为之主张和斗争的事业,是真实可触的。我们生活在一个激进的氛围中,从这个词最好的意义上来说,是指一种无情的激进主义。它由伯特兰·罗素等老一辈的人共享,并被如今的若泽·萨拉马戈继承。那时的原则是活生生的文字,不像今天,是亟待挖掘的遗物。“事业”这个词具有一种神圣的光环。
如今并不是没有事业。然而,在我看来,能够将年轻人凝聚起来的事业更多时候是虚拟的,是有些抽象的概念,比如“全球化”。反对货币调整和私有化教条或是对抗环境污染,这些抗争并不那么容易,因为目标过于模糊。20世纪60年代涉及的是美国黑人民权运动,越南战争以及希腊、拉丁美洲或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独裁统治。单单一场像伍德斯托克音乐节那样盛大的摇滚音乐会便可以诠释所有的反叛精神。甚至连大学的衰老都变成了人们走上街头的原因之一,因为高等学府已经变成了暮气沉沉的木乃伊。
1968年春天巴黎街头的反叛活动以及同年在墨西哥城特拉特洛尔科广场上发生的学生大屠杀,起初都是由学术的陈腐所引发的,后来转变为对僵化且虚伪社会进行深刻变革的呼声。胡里奥·科塔萨尔的精神漂浮在这段动荡历史的水面上,因为人们被无情地划分为克罗诺皮奥、埃斯贝兰萨和法玛[ 克罗诺皮奥、埃斯贝兰萨和法玛是科塔萨尔在其作品《克罗诺皮奥与法玛的故事》中创造的三个虚构的生物或者说人格类型。——译注]。还有其他文学爆炸时期的作家记录了这些事件。通过第一手见证人的记载,我们了解到了这些事情的面貌。在一篇令人难忘的报道中,卡洛斯·富恩特斯向我们描述了1968年的巴黎,而埃莱娜·波尼亚沃斯卡则在《特拉特洛尔科之夜》中讲述了墨西哥的大屠杀。
青年的反叛是对存在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猛烈冲击,因为这是一次直抵本质而非流于表面的质疑。旧有的世界不再适用了,它已濒临枯竭。古老的体系,不变的真理。祖国、家庭、秩序,良好的行为、举止以及穿着方式。在《跳房子》中,科塔萨尔继续在那整个儿结构上放置炸药。那不仅仅是长发、草鞋以及镶有孤星的毡帽的问题了。我们所有人都想成为克罗诺皮奥,嘲笑那些埃斯贝兰萨,并唾弃法玛。
这些归根结底是超越了形而上学的伦理范畴,最终会带来政治性的后果。流亡的科塔萨尔成了秘密革命者在地下室阅读的作家,因为他提出了非存在的方式,用来抵抗那些拉丁美洲社会所提供的无耻的存在方式。在这片土地上,仅仅废除不公是不够的,还需要寻找个人行为的新模式。归根结底,反叛不仅仅是针对社会,也是针对每个人自身,或者说,是针对被社会塑造的我们。
也许,试图从一本书中汲取政治教训,始终是一种幻想。这本书和《跳房子》一样,率先提出要系统性地摧毁整个西方价值体系,却没有提供任何方法论。这仍然算是一次摧毁行动,没有更多的追求,因为答案中蕴含着错误。科塔萨尔的政治方案是后来提出的,先是针对古巴,而后针对尼加拉瓜,不过他的文学作品几乎从来没有提到过这些,甚至连《曼努埃尔之书》也没有。不过,他的公民行为却体现了他的政治观点。身为一个有信仰并能够捍卫信仰的作家,他的行为在今天看来也是非常奇怪的。
科塔萨尔在这场行走在刀锋上的旅途中,有许多东西要教给我们,即那些对社会抱有承诺的作家不应该牺牲自己的创作自由。当他在马那瓜接受尼加拉瓜共和国授予他的“鲁文·达里奥”文化独立勋章的时候,曾表示说,写作的自由就像是远距离迁徙中保持完美队形飞翔的鸟儿的自由。它们在队形中不断地变换位置。虽然是同样的鸟,但它们总是在换位。我只是在凭记忆重述这个关于作家自由的比喻。
也许,在《跳房子》的年代,科塔萨尔最有价值的真正提案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