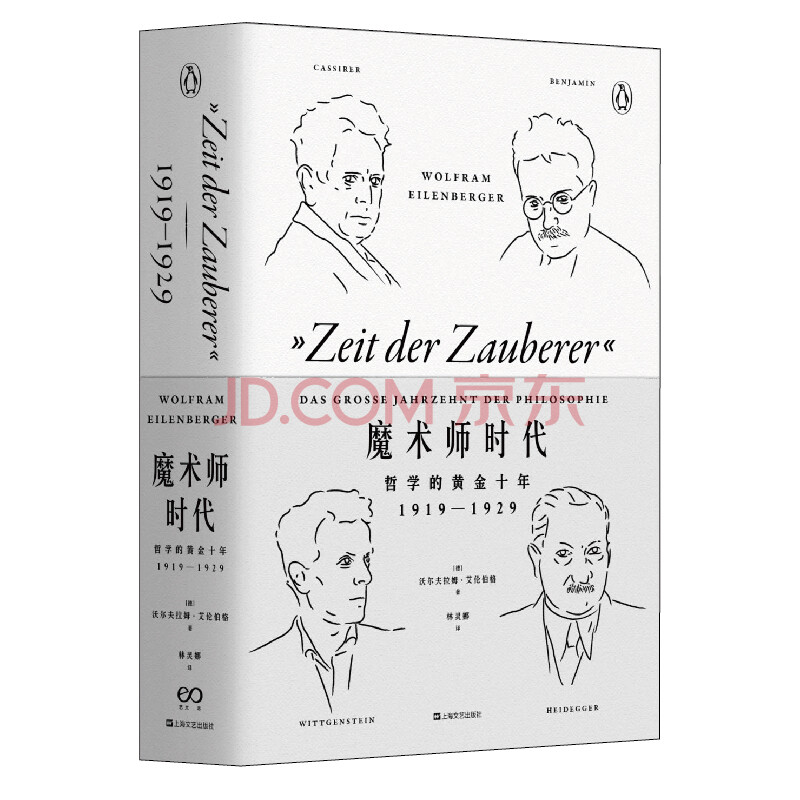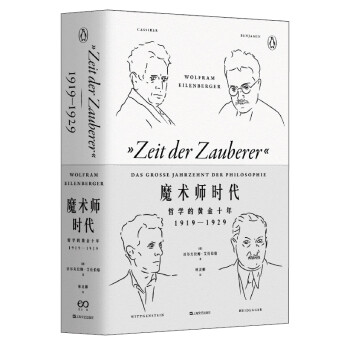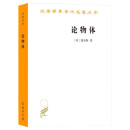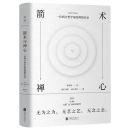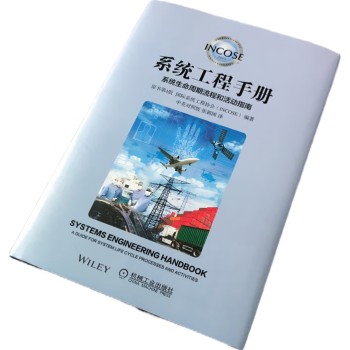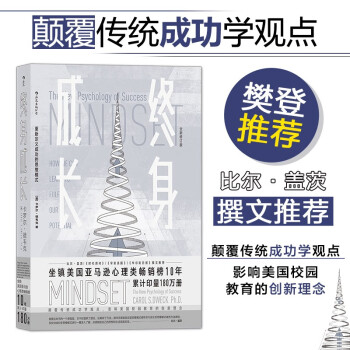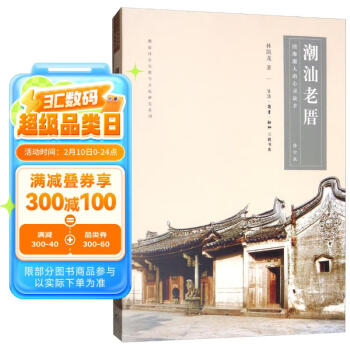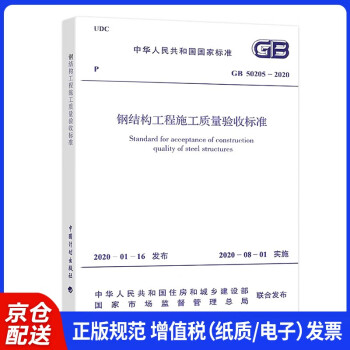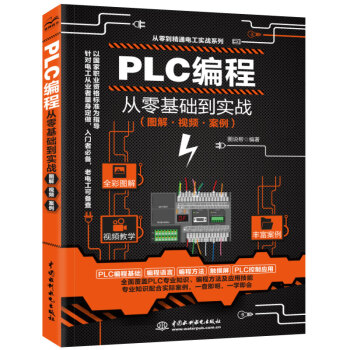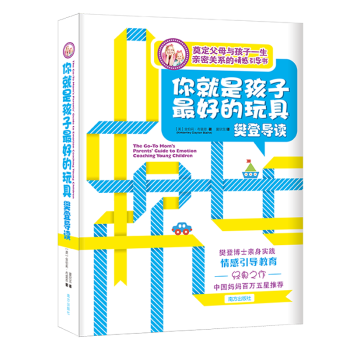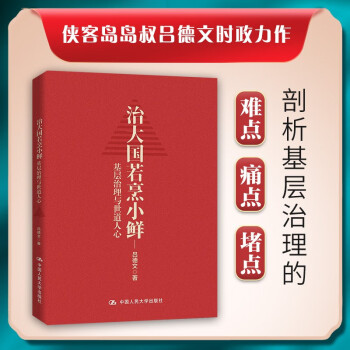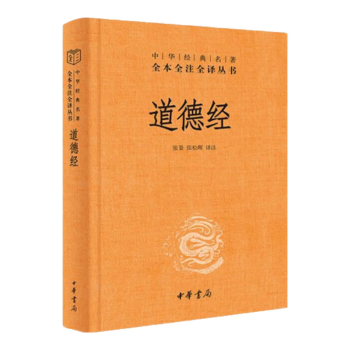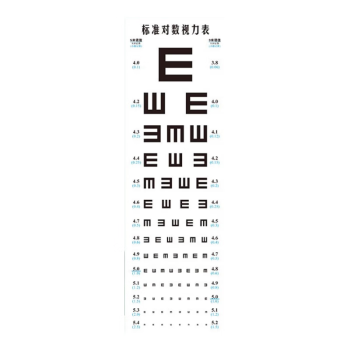内容简介
20世纪20年代,一个处在多彩生活与经济危机之间的年代,一个一战刚刚结束、纳粹主义正在酝酿的年代,一个德国哲学的黄金年代。
马丁·海德格尔的事业平步青云,并邂逅了与汉娜·阿伦特的爱情。跌跌撞撞的瓦尔特·本雅明在卡普里岛疯狂迷恋上了一个来自拉脱维亚的无政府主义者,也正是这段爱恋使他自己成为了一名革命者。天才维特根斯坦是亿万富翁之子,他在剑桥被誉为哲学的上帝,而这样的天之骄子却来到了上奥地利州偏远地区担任乡村小学教师,过着完全赤贫的生活。最后还有恩斯特·卡西尔,他在迁居到汉堡中产阶级区的几年前,亲身经历了正在抬头的反犹主义。
本书除梳理了海德格尔、本雅明、维特根斯坦和卡西尔在1919-1929年间的各异的日常生活、情感经历和思想状况,还力求将四位哲人的思想予以对观,展现了他们在面临时代根本问题时各自的回答和应对方式。借助作者出色的叙述,我们在这四位卓越哲学家的生活道路和革命性思想中,看到了当今世界的根源。回望20世纪20年代,既是感悟又是警醒。
目录
第一章 序言 魔术师
第二章 跳跃 1919
第三章 语言 1919-1920
第四章 形成 1922-1923
第五章 你 1923-1925
第六章 自由 1925-1927
第七章 拱廊街 1926-1928
第八章 时间 1929
结语
著作目录
参考文献摘选
后记
试读
新的自我意识
实际上,本雅明论述的说服力有多大,主要取决于人们对浪漫派那两个基本思路的看法。那两个基本思路涉及到的是普遍存在的所有事物与自身和与他者的关联,人们在多大程度上觉得这两个思路是合理的,就会在多大程度上相信本雅明的观点。其实这两个基本思路也并不像第一眼看上去那么不合理。瓦尔特· 本雅明起码可以给他的父亲指出全人类身上存在的一个基本现象:人类具有自我意识。这个事实无可争议,每个人都能具体地感受到自我意识,根本无需对此存在任何理性怀疑。最终,每个人都拥有这么一种特殊的神奇能力。所谓自我意识,指的是通过自己的思考能力来思考自己的想法。我们所有人都可以独立地“思考”自己的“想法”。这样,我们每个人都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认知过程,在这个认知过程中,不但批评的客体(也就是我们思考的对象——我们自己的想法),而且批评的主体(正在进行思考的思维)都可以感受到一种变化,并感受到批评的客体和主体实际上是合为一体的。对于浪漫主义者来说,正是自我意识能够进行自省的这种基本状况,成为了批评活动与他者产生关联的一个典型例子,这个例子对于每种形式的关联都适用。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普遍适用的例子,它可以用来说明,当“一个存在物被另一存在物所认识,并与被认识者的自我认识叠合” 时,发生了什么。
事实上,处于变化中的这种事物的自我关联在持续产生着奇迹。人是具有自我意识的主体,本雅明能够给一个具有思考能力的主体——包括他的父亲解释清楚自己的想法。当一个人思考自己与自己的关联基础、自己与世界的关联基础时,这种奇迹就以一种特别明显和有效的方式发生了。伟大的艺术作品事实上就是这么一种自省过程的结果。因此,伟大的艺术作品在自我关联和与他者关联方面,内容特别丰富多元,并且具有启发性和自身特色,因此也可以促进人们的认知:
批评就如同在一个艺术作品身上进行实验,通过实验,艺术作品的反思被唤醒了,艺术作品被带入了意识领域,以及对其自身的认识。只要批评是对艺术作品的一种认识,那么批评便也是艺术作品的一种自我认识;只要批评指的是评价一个艺术作品,那么这种评价也是在艺术作品的自我评价中进行的。
对于本雅明来说,艺术批评概念的哲学核心存在于浪漫主义之中,就算浪漫主义者自己也有可能对此理解得不够清楚。要清楚理解这个哲学核心,需要观察一个持续较长的时间维度(整整150 年),还得进行尖锐的分析。换句话说,也就是需要进行批评。本雅明正是想把毕生精力都投入到批评这个任务当中。尤其是因为,批评活动也会对他以及在他自身内部产生作用,他批评的“作品”会不断发生变化,他也会由此认知自我。事实上,每个可以对自己的思维进行思考的人——其实每个人都有这种能力——都有可能是自己的一件作品。每个人都可以练习以批评的眼光检验自己和认知自我。在一定程度上,每个人都能以批评的方式成长和塑造自我。每个人都能成为真正的那个自己。这种成长方式,就是一种批评。或者也可以简单说成:从事哲学。(P44-46)
变形
维特根斯坦决定放弃家里留给他的遗产,他是否真的意识到,这个决定会产生多大影响?他有没有跟哥哥姐姐们商量过这个事儿?要不要最好再深思熟虑一下?不,他不打算再考虑了。“这下好了,”维特根斯坦家的公证人叹息道,“您真是下定了决心要在金钱上自杀。”确是如此。维特根斯坦下定决心不会动摇。他还是身着白色少尉制服,没有丝毫犹豫,几次打断公证人的问话,强调自己的决定不会改变,哪怕他今后再无经济方面的避难所,哪怕条约中没有任何特殊的附加条款,哪怕他再无退路不可反悔,哪怕他签字之后真的要永远和绝对放弃他所有财产,无可挽回。金钱上的自杀,说得好。
维特根斯坦刚回到维也纳还不到一周时间。他是从意大利战俘营归来的最后一批军官。此刻,1919 年8 月31 日, 他坐在维也纳一家气派的律师事务所里,把他的全部财产——转让给他的姐姐赫尔梅娜、海伦娜和哥哥保罗。维也纳,这个曾经骄傲的帝国首都,如今只是阿尔卑斯山脚下一个破产迷你共和国的首都。在一战后的第一个夏天,维也纳最终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面临着战后灾难,大多数奥地利国民主张与同样陷入瓦解状态的德国结盟,但是遭到了战胜国的禁止。96% 的奥地利儿童在1919 年夏天遭受着营养不良的折磨。通货膨胀使得食品价格爆炸式地飞涨,货币处于一种自由落体状态——城市风气也是如此。哈布斯堡王朝的旧等级秩序完全崩溃,而新秩序也仍未全部运作起来。一切都跟原来不一样了,变形了。当时30 岁的路德维希· 维特根斯坦经过几年的战争岁月也已经变成另一个人了。
1914 年夏天,一战爆发仅仅几天之后,维特根斯坦带着根本改变生活的希望自愿报名入伍,成为一名下士。他出身维也纳最上流的社会,欧洲最富有的工业家庭之一,剑桥大学的学生,当时已是哲学界百年一遇的天才,他的老师伯特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