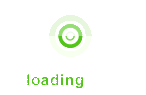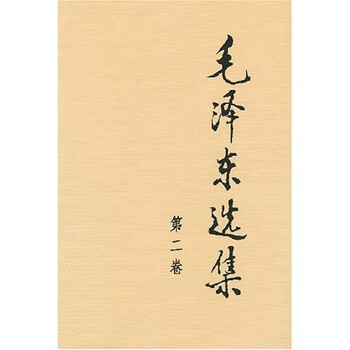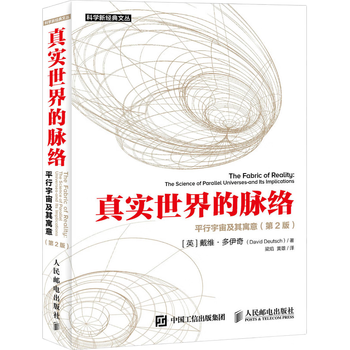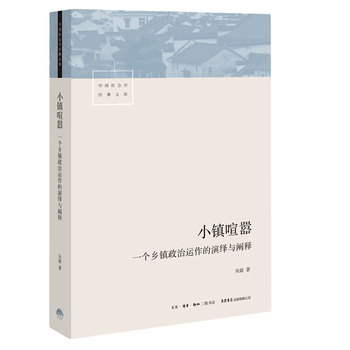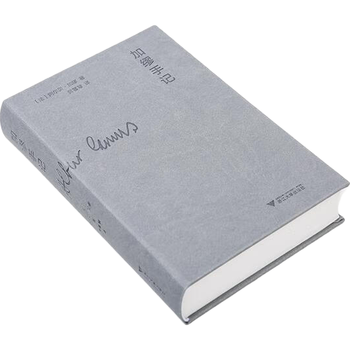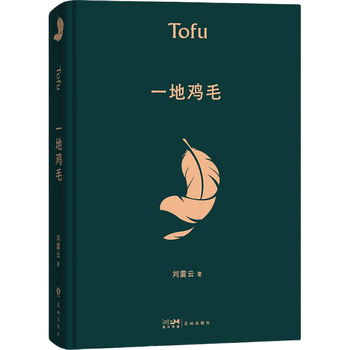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部用平凡人眼光叙述中国社会近百年变迁的回忆录,既是个人史、家庭史,也是社会史。全书以作者早年乘坐的“绿皮火车”为意象,串联起两代人的生命轨迹:从未谋面的父亲、一生坚毅的母亲、努力上进的兄姐、困难时期的生活点滴、面粉厂当工人、改变命运的高考、跻身大学讲台实现理想。从民国军阀混战、抗战岁月,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和平建设、“上山下乡”、改革开放,举凡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重要节点都有涉及。书中配有家庭相册、书信、车票等200余幅珍贵图像,图文并茂,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和历史价值。
精彩书评
那时那人那事体,历历在目,一帧帧精细入微的细密工笔;此情此景此风云,摄人心魄,一幅幅自然挥洒的大小写意。
——刘梁剑(华东师范大学暂学系教授)
一个家庭,因自尊而有尊严,在时代的风雨阴晴中,不投机,不亏欠别人,清白自守,也努力上进,以勤奋和坚韧,挣得属于他们的收获也创造生活的乐趣。天光云影,点点滴滴,在一颗纯净心灵上的留痕如今,通过这本书,呈现给了我们。
——刘时工(华东师范大学暂学系副教授)
目录
上编 亲恩难忘
第一章 从未见过的父亲
1.父亲的身世 2.父亲的经历 3.父亲的品性 4.父亲的精神遗产 5.母亲了愿 6.儿女寻根
第二章 一生坚毅的母亲
1.母亲的曲折求学路 2.母亲的教书生涯 3.母亲的为人 4.母亲独自抚养我们五兄妹长大
5.母亲对我们的教育 6.追寻母亲的过往踪迹
中编 酸涩往昔
第三章 三年困难时期点滴
1.幼年不知饿汉饥 2.吃起了“大锅饭” 3.跟母亲遛“黑市” 4.挖野菜
5.我们家的自救行动? 6.告别饥饿
第四章 南下北上本地转
1.大哥的南下之行 2.大姐的北上见闻 3.我们仨的就地转经历
第五章 我的两个发小
1.我们仨结缘 2.回忆赶场 3.感念发小送温暖
4.踏上求知路 5.《金色的炉台》?
第六章 哥哥姐姐的插队生活
1.酉阳、秀山、黔江、彭水 2.“喜看稻菽千重浪” 3.接受“再教育”?
4.一串小插曲 5.危险无处不在 6.回家了! 补 记
第七章 职业生涯的第一站
1.我当上了工人 2.追求政治进步 3.参加民兵训练 4.成为宣传队员
5.被抽去当“吼帮” 6.我要读书
下 编 小花采撷
第八章 改变命运的高考
1.我的高考动力 2.紧张备考
3.走进考场 4.二十多年的梦,终于圆了!?
第九章 我的大学生活
1.泡在教室和图书馆 2.黏在食堂
3.聊在宿舍 4.乐在操场
第十章 川大的老师们
1.教公共课的老师们 2.教专业课的老师们
第十一章 在丰台的五年
1.新的工作环境 2.上司杨部长
3.我的几位同事 4.我的几位好友
第十二章 考研往事
1.报名遇挫 2.复习备考
3.我又进考场了 4.人大的读研生活
第十三章 丽娃河畔的教研室同仁
1.坦对死神的蒋老师 2.魂入学术的江老师
3.大儒风范的张老师 4.温暖如春的来老师
5.淡定自若的徐老师 6.曾经与如今的同仁
结语 绿皮火车:相随半生的长情
1.购票难 2.上车不易 3.硬座、硬卧、软卧和短途闷罐车厢
4.吃喝 5.睡觉 6.闹心事不少
7.乐趣亦多多 8.下车
后 记
试读
吃起了“大锅饭”
1960年,国家已经进入困难时期。头脑中的饥饿记忆,始于城市组织人们吃集体食堂的“大锅饭”。当时,居民由政府按职别、年龄,决定配给口粮的多少,小学生的定量是每月十六至二十一斤。
上学没几周,班主任老师郑重宣布:从今天起,同学们都要吃集体食堂了!总算能与住读生一起享受“打平伙”(聚餐的一种方式)待遇,走读生们笑开了花。我们班的同学多为六七岁,尚处于发蒙年龄,从老师的描绘中,我们懵懵懂懂地以为:吃大锅饭,如同登云梯观景,风光无限。
开饭时,按八人一桌,每班分成五桌,由班主任指定的班干部担任桌长。吃饭时,桌长叫上两个同学,先到窗口端回饭菜,再分到同学们碗中。全校几百个学生,突然集中在一起吃饭,舀菜盛饭的几个窗口,桌长们的脑袋,似雨后林中的蘑菇,齐刷刷地冒出,可忙坏了厨房大师傅。吃饭时,食堂没有足够的桌凳,那也无妨,大家围成一圈蹲着吃,小同学们干脆坐地上。
刚开始吃大锅饭时,光景不错。早饭每人一碗稀饭、一个馒头、小半勺咸菜。中饭或晚饭,每人一碗米饭、两勺菜。这么多人聚一块,大家有说有笑,又喊又叫,叽喳之声,胜晨鸦斗嘴,似要掀翻房顶。然好光景维持了没几天,早饭的馒头便没了踪影,只剩一大盆稀饭。干货沉底,分稀饭时,个个眼睛盯着桌长的饭勺,那情形,像饭盆里都能捞出眼珠子来,人人都盼望那最后一勺,能倒进自己碗里。中午和晚上,红苕代替了米饭,菜也经常省了。此时,桌长手中饭勺的稳定度,决定了大伙肚皮的瘪或鼓。
我们的桌长生于干部家庭。她刚入学,因根正苗红,爱帮助同学,深得老师喜爱和同学拥戴,就顺理成章地当了班长。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如何合理运用“权力”真是难为了这位七岁多的小班长。记得那天晚饭分红苕,她就不免尴尬:公平分配吧,自己是住读生,晚上肚子一旦“闹革命”,可不比走读生;走读生可从泡菜坛中捞块老姜嚼嚼,再不济,还可喝碗白开水。“以权谋私”吧,败坏了形象,同学们会怎么看自己?这班长,还当不当得下去?当然,这只是我如今的主观猜测,当时的她,恐怕压根想不到这些。但不管怎样,大红苕在她手中,抓起又放下,放下又抓起,足以表明她的矛盾心理。如此反复几次,勾得我们眼热心痒。想起玩“击鼓传花”时,都怕花落在自己面前,但此刻,我却盼望她抓红苕的手,刚好在自己这儿松开。小心脏真有点受不了!最终,面子抵不过肚子,两个壮硕点的红苕,出乎意料地落入了她自己碗里。因为饥饿感强烈,这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于今想来,古代西方的“切饼”论,将操刀权与选择权相分离,人性自觉与规则制约相统一,挺公平,也挺合情。[3]
吃饭时,食堂会提供几大桶腌菜汤,不限量,随便喝。低年级同学个子小,“抢汤”占不了便宜。于是,每次食堂关门前,总会看见几个瘦小同学,围着大木桶转圈,用铁勺捞残存的菜叶。桶又高又大,他们小半截胳膊泡在汤里,捞得格外吃力。
捞腌菜的阵营里,少不了我二哥。他那时已八岁多,个头却比六岁孩子高不了多少。所以,他的“捞姿”更独特:脚离地,半个身子悬在桶沿,像拦腰架在单杠上,随时准备练空翻。一次,一位小同学捞来捞去,突然感觉铁勺比平时重,他以为捡到“刨财”(发横财),兴奋地大喊“我捞到菜头了!”提起勺子一看,原来是只死耗子!一旁惊呆的二哥,从此不再光顾腌菜汤。
臭烘烘的腌菜在操场坝晾晒,饿慌了的小同学,目光总在上面扫。想伸手,又怕被捉到,不光要挨老师的“刺”,更怕被同窗指为“偷儿”。但毕竟是孩子,自制力有限,没几天,课间休息时,总能看见几个人抓起腌菜,快速塞嘴里,个别的还因塞多了,在操场“哇哇”狂吐。此刻,道德觉悟在“饥寒起盗心”面前,垂头丧气得很。
那时,二姐读小学五年级,我和二哥分别读一、二年级。二姐一贯自我要求严格,我没二哥爱“翻筋”(好动),体力消耗小点,虽感肚子饿,但喝两口自来水,也勉强能忍。二哥虽饿得蔫不拉唧,但“傲兮拉弥”(清高要面子)的个性使然,他哪怕饿得眼冒金星,也不去碰操场的腌菜。
转眼元旦节到了。那天中饭,食堂除了按定量供应外,还额外熬了几大桶红苕稀饭。无限量的红苕稀饭,极大地满足了大家的口腹之欲。很快,食堂便见一群又一群的学生,挺着西瓜肚,迈着八字步,打着“横锤”(用衣袖擦鼻子嘴巴上的饭嘎巴),鱼贯而出。唯有二哥,完全不顾胃容,一碗接一碗地灌,最后,肚皮鼓成了顺风船帆。他直不起身,也弯不下腰,更躺不了地,只好半跪着,半个多小时后,才一步一步挪回家。
为驱饿,学校在教学楼外的水池里养了小球藻,说是可以补充营养。这家伙繁殖力超强,没几天,一池春水绿莹莹、酽湩湩[4],看着犯腻。喝这“营养汤”,得眼一闭、嘴一张,啥都不想。所以,虽可尽情消受,却没人去舀,更没人去抢。
最让我难忘的是,班里一位小男生,可能因为在家中面条吃多了,接着又一口气奔到教室,随着一个饱嗝,他胃里的面条,一下子吐了出来。随后,他快速捧起课桌上吐出的碎面条,一股脑儿喂回了嘴里。
那时,大哥读初三,大姐读初一,同母亲一起,在中学食堂吃大锅饭。
每天早上,大哥大姐端起各自的饭盒,到食堂买稀饭。食堂熬的稀饭,看起稠乎乎,其实撒了碱。两人手捧饭盒,边走边吃。清香的稀饭,仰脖喝倒是痛快,但不过瘾。于是,锑勺慢慢送进嘴里,细细品味道,直到米粒在唾液酶作用下,生出甜味,才缓缓咽下去。饭吃完,锑勺在盒壁,刮出刺耳的“吱吱”声,再伸长舌头,舔残存的饭汁。大哥正处于身体发育快速期,第一节课结束,肚子就咕咕响,后面三节课,只能硬扛。
中午和晚上,三人从食堂买回米饭或红苕、一碗少油无肉的炒蔬菜。米饭说是每人三两,怎么看都缺分量,红苕则出奇的苗条。一次,母亲看着六根比胡萝卜略粗的红苕,实在气不过,直接找到食堂:“你们自己看看,让我们几个人怎么分?怎么吃?”食堂师傅自知理亏,只得补了三根。至于菜,去晚了便没有了。于是,咸菜下饭或只啃红苕渐成常态。
我们仨从小学食堂吃完饭回家,总能赶上母亲和大哥大姐端起饭碗。眼馋的二哥,忍不住围着饭桌“巡视”,见到哥姐不小心掉在桌上的一颗饭粒,手快如闪电,捡起放嘴里。逢此,母亲会拨一点碗里的饭,或掰块红苕,递给他。一开始,二哥“不要、不要”地谦辞。禁不住米饭的诱惑和母亲的催请,半分钟不到,他就抓起了筷子。
那年月讲究精神变物质,肚子可贫困,精神须繁荣。所以,学校的秋游照旧进行。看山岭景色,踏河滩浅草,不能空着肚子,食堂便临时下放“大锅分配权”,让家长给孩子自备吃食。
这事对那些家庭经济宽裕,有钱买高价食品的家庭来说容易;对那些父母单位没条件办食堂,只能自己开伙的人家也不难。难的是那些吃食堂大锅饭,家中子女多,父母工资低的家庭。怎样让乘兴而去的孩子,不致因肚皮抗议而败兴?当爹妈的自有招数:设法借来少量面粉,和着菜叶调成糊,倒进锅里摊出有盐没油的不成形面饼。记得当时我带的,就是母亲做的浆糊烙饼。饼子太软,母亲特地用饭盒装。但班上个别同学,却是空手去的。
秋游那天,终于放敞[5]了,同学们狂追疯跑,全然不觉肚子饿,只是到了饭点,才感到前胸贴后脊。老师示意带了吃食的同学,分点给眼巴巴看着的同学,大家积极响应,“亲亲以睦”的传统美德,不经意间得到了传承。
也有“吃福喜”(白吃)的例外。二姐班上组织郊游,班里一位同学的爹是公安局局长,大伙跟着沾光,不仅坐上难得一享的大汽车(一般都坐敞篷卡车),且每人发一个牛皮菜大包子。过河时,一位同学乐极生悲,包子掉下了河。迅雷不及掩耳,他一个鱼跃下水,捞起发泡的包子,三下五除二,吃得渣也不剩。
几个月后,小学的大锅饭取消了,我和二姐、二哥的粮食关系,转到了母亲所在中学的食堂。能与母亲和哥姐一起吃饭,真是开心。只是,各单位继续规定员工吃集体伙食,我们的大锅饭,只是换了场所而已。
最初,粮食尚有粗细搭配。细粮是米面,粗粮是红苕。但好景不长,粗粮很快成了主角,以红苕和包谷面为主。
吃红苕时,母亲按各自的定量和胃口大小,大致分配一下。我从小听母亲讲“孔融让梨”,懂点儿“兄友弟恭”之理。一次母亲分红苕,我看了看自己的,又看了看大哥的,随即拿出一个,还给母亲:“我吃不了这么多,这个给大哥。”为此,母亲没少赞扬我,我俨然成了现代版“孔融”。
刚吃包谷羹时,我迫不及待地喝了一大口。不料它太烫,进嘴就想吐出来,又不舍得吐,只好含着大口哈气,硬生生地让它在口中冷却。结果,天堂板(上颌)烫出几个似泡非泡的疙瘩包。后果很严重,教训很惨痛,由此我悟出了一个道理:吃苦头容易使人变聪明。羹喝完,舌头沿碗沿,认真仔细地舔(以致现在我只要揭开酸奶瓶盖,就有伸舌头的冲动),再用开水涮碗,扫清残余。吃了被烫的苦头,我们很快总结出“喝羹经”:将一碗羹放在半盆凉水中,等碗的边缘变冷,先慢慢喝出一个豁口,满碗羹羹,便断崖似的与碗沿分离,自动往嘴里垮塌。一碗喝光,碗似水洗,光滑洁净。
有段时间,粮食供应特别紧张,粗粮也成了稀缺品。于是,粗粮退位,“瓜菜代”登场。
“瓜”是磨成粉的土茯苓(菝葜的干燥根茎),雅号“代食品”,很快成了主角。馒头因掺杂大量土茯苓粉,成了枣红色,吃嘴里,像嚼细木屑,有点割喉咙,但比起饿肚子,根本不算个事。红馒头虽没白墡泥(观音土)耐看,但至少有点营养;虽能引起腹胀便塞,但不像白墡泥,完全不能消化。因此,比起农村人吃光草根树皮,再去吞白墡泥,城里人能有红馒头果腹,已经算是“洪福齐天”了。
菜以白茎牛皮菜为主。食堂的大锅,天天都在煮,大家的饭碗,顿顿被光顾。听说烂了的牛皮菜,吃多了会中毒,但只是“听说”,我们周围的人都不曾中招。毕竟,那年头想海吃一顿牛皮菜都是奢望。
电影《洪湖赤卫队》上映后,每到饭点,学生们饭碗敲得叮当响,唱着“洪湖水呀长又长,人心向着吃饭堂。拿起钵钵打三两呀,还有一碗白菜汤”,涌进大饭堂。吃饭速度之快,堪比如今唯独对美食激情四溢的“干饭人”:带着一口气干掉一锅的猛劲,顷刻便见碗底。
前言/序言
自序
转眼就到了“古稀”。回望来时人生路,感慨着那些难以忘怀的曾经,有酸涩苦楚,有曲折坎坷,还有许多明媚艳丽,许多深情厚谊……那么悠长,那么深刻,那么镌骨铭心。
我生于普通知识分子家庭,千遍万遍,道不尽对父母的感激!是他们给了我生命,让我拥有了一个家。这个家,虽然简陋、清贫,却为我提供了生存的养料,给了我一个还算健康的身体。
我父母皆在民国时期受过系统教育。他们经历过军阀混战、民族危亡、内战硝烟,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和平建设时期。他们独立的人格品性,在困苦中挺立的脊梁,靠不断拼搏以实现目标的进取心,以仁心贯穿的善行,既是我立世的标杆、职业生涯的基点,也熏陶了我的心性。他们给予我无穷的精神力量,陪伴和激励着我一天天长大,成为现实中的自己。
家是暖身的港湾。这份暖,首先来自我母亲,一位慈爱、善良、坚韧、智慧且能干的女性。几十年间,她孤身一人,忍辱负重,含辛茹苦,为我们五兄妹遮风挡雨,在独自一人抚养我们的同时,为我树立了为学为人的风骨典范。
这份暖,也来自我的哥姐和亲人。他们几十年如一日地关爱我,这份爱如阳光似美酒,明媚香醇,陪我走过风雨,度过艰辛,让我感受和收获了源源不断的脉脉暖情。
情是润心的玉液。这份情,来自我的老师们。他们书山开路,学海领航,用知识和智慧滋养我的头脑和心灵,使我的事业之舟得以遂行。
这份情,也来自我的同学、朋友、同事和学生。他们淡若清溪,亦如沙海浓荫,顺利时祝福庆贺,遇难时施以援手,让我的人生之旅充满温馨。
感恩改革开放!相对公平的社会环境,给了我选择的机会、奋斗的动力和发展的空间,让我得以到四川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求学和深造,最后到华东师范大学从教,从而圆了我自幼的两个梦:读大学、做园丁,实现了我的人生理想。一路走来,屡有所成,花开时新……
谨以此书,献给所有爱我和我爱的人!
——摘自郑忆石著《绿皮火车:我的回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6年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