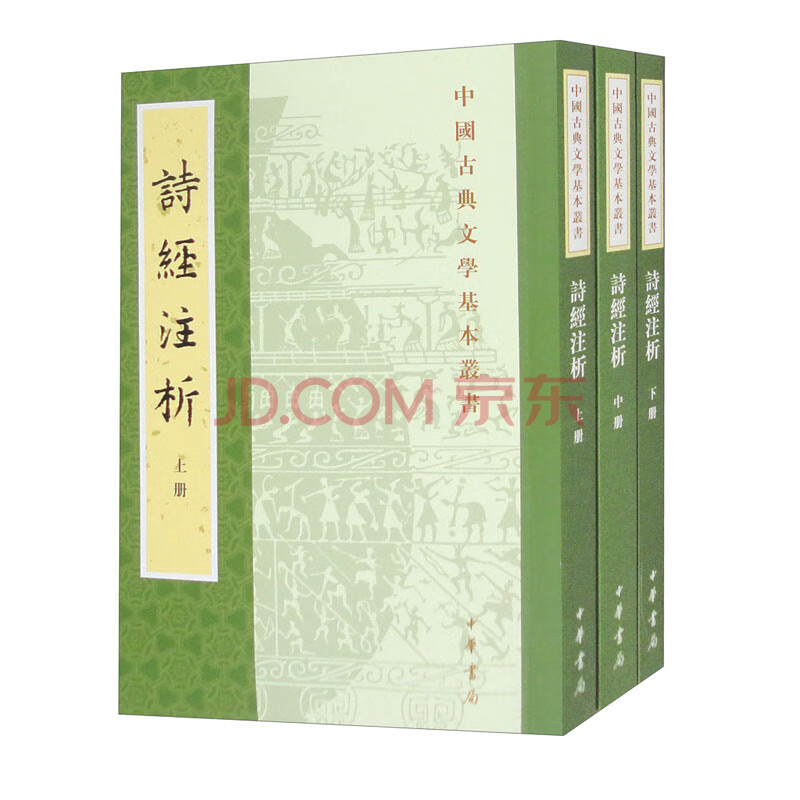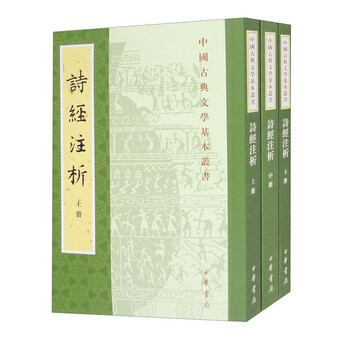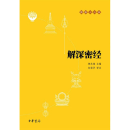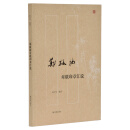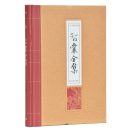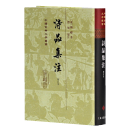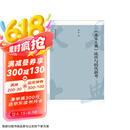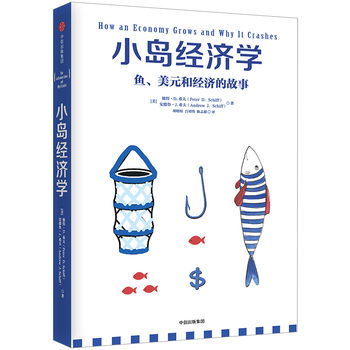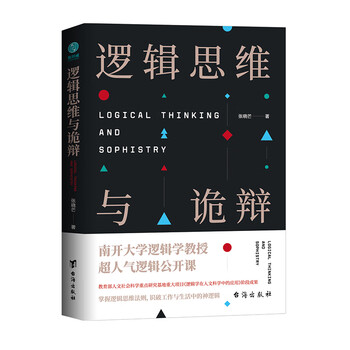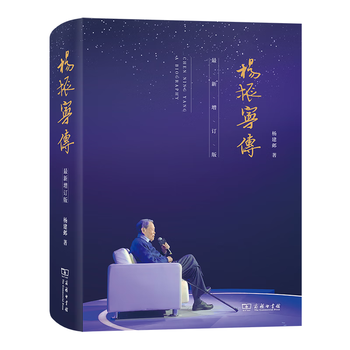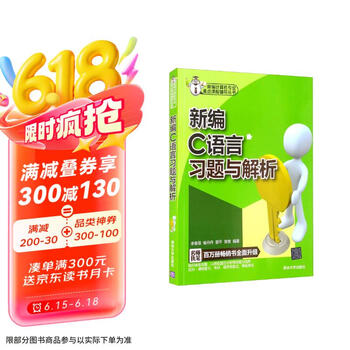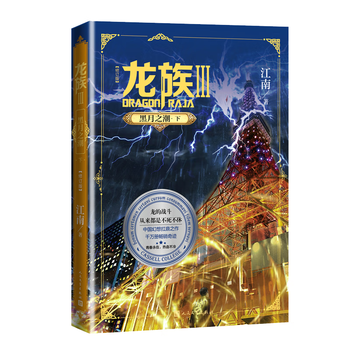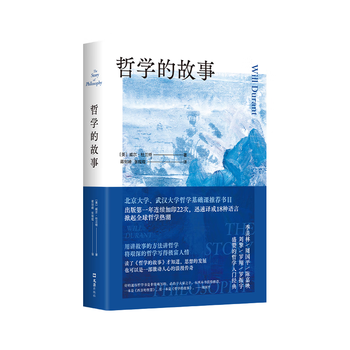内容简介
就诗论诗,决不等于一空依傍。秦火以后,汉时说诗者分成今、古文两派,鲁、齐、韩、毛四家;自毛传以来,直至清代,对诗经作各方面研究注释的著作更多至千余种。如此庞大纷繁、学说林立的局面,虽然使得学者们不免有“诗无达诂”的感慨,然而毕竟为理解这三百零五篇诗开拓了一条通道。我们作今注,是站在前贤奠定的基础上,择善而从,特别注意不盲从一家。譬如,毛传是很早注释诗经的著作,历来奉为圭臬。它的优点是去古未远,训诂多精确之处。缺点是文字简奥难通,以致于郑玄作笺,孔颖达作疏,陈奂再作疏,累累不穷。因为时代的隔阂,今人已看不懂,其价值是无法不打折扣的。其次,毛公作传时,训诂学尚在草创期,箪路蓝缕之功虽不可没,筒陋粗疏之失也是难以讳言的。以毛传为不可踰越,不符合学术发展的事实。再如郑笺,从王肃毛诗问难对它进行批驳开始,责难者代不乏人,甚至斥之为“不守家法之大贼”。直到今天,仍有人砣砣于左郑右毛。实际上,郑笺虽有不少主观武断的地方,但它熔今、古文为一炉,参稽各家,自成一说,是诗经学上的一大进步,郑笺出而三家诗逐渐式微便是明证。又如朱熹诗集传,研究诗经开一代风气,而训诂不及漠学诸家。但我们仔细分析,觉得朱熹就诗论诗,注释中不乏合情合理、通俗易懂之处,还是应当采纳的。至清代,学术的发展使诗经研究大大地向前迈进,但门户偏见并未完全消除。譬如陈奂诗毛氏传疏,唯毛传是尊;而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则明显倾向三家诗说。这两本著作虽然观点互相龃龉,却不妨碍我们择取各自的合理部分。总之,爬梳抉剔,去疵存瑜,是我们的努力目标。此外,在注释中,我们还致力于运用说文、尔雅、广雅等字书,揭示诗经中不少字词的本义、引申义或假借义的关系。有些关键字,甚至不避重复地训释。这样做09日在帮助读者将眼光扩展到先秦古汉语词义的演变上去,或许能通过读诗得到更多的收获。解放后,甲骨金石文字的研究大大发展,地下文物屡见出土,这些成果开拓了我们的眼界,也丰富了本书的内容。学术是永远向前发展的,诗经研究也必然会不断攀向新的高峰。可以说,这是我们在众多注本之后仍希望将自己的一点心得奉献给读者的原因之二。
目录


前言/序言
诗经注析同读者诸君见面了。近年来,诗经今注或今译本已经出版了好几种,我们为什么还要来做一番似乎叠牀架屋的工作呢?这是要在序言中向读者交待一下的。
诗经作为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是可以传之永久的;但自从被捧上儒家经典的宝座之后,诗旨遭经师的歪曲,每首诗都被套上“思无邪”的灵光圈,打上“温柔敦厚”的标记(我们并不反对温柔敦厚,但以此概括全部诗经,却不符合事实),成为“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金科玉律和辅成王道的“谏书”。自汉魏以迄清末,诗经的研究基本上循着这样一条经学轨迹在行进。当然,经学作为传统文化中很丰富的一部分,值得认真研究总结,但造不是我们写这部书的动机。我们的愿望,是想恢复诗经的客观存在和本来面目。拨开经学的雾翳,弹卸毛序蒙上的灰尘,揩清后世各时代追加的油彩,她的面容是能够豁然显露的。南宋治诗大师朱熹,攻讦毛序,废序不用,提出“就诗论诗”的原则。尽管他并没有真正做到这一点,但开创风气,意义是至为钜大的。今天,我们的治学眼光应该更加客观,可以更彻底地就诗论诗。毛序中正确的自当吸收,但大部分必须否定。诗经就是诗,准确地说,就是歌曲,一首首颂德的歌、祭祀的歌、宴饮的歌、恋爱的歌、送别的歌、讽刺的歌,等等,如此而已。我们在每一篇诗前面都加一段“题解”,便是想制作开放“诗”的殿堂的第一把钥匙,也可以看作是我们出版这本书的原因之一。
当然,就诗论诗,决不等于一空依傍。秦火以后,汉时说诗者分成今、古文两派,鲁、齐、韩、毛四家;自毛传以来,直至清代,对诗经作各方面研究注释的著作更多至千余种。如此庞大纷繁、学说林立的局面,虽然使得学者们不免有“诗无达诂”的感慨,然而毕竟为理解这三百零五篇诗开拓了一条通道。我们作今注,是站在前贤奠定的基础上,择善而从,特别注意不盲从一家。譬如,毛传是最早注释诗经的著作,历来奉为圭臬。它的优点是去古未远,训诂多精确之处。缺点是文字简奥难通,以致于郑玄作笺,孔颖达作疏,陈奂再作疏,累累不穷。因为时代的隔阂,今人已看不懂,其价值是无法不打折扣的。其次,毛公作传时,训诂学尚在草创期,箪路蓝缕之功虽不可没,筒陋粗疏之失也是难以讳言的。以毛传为不可踰越,不符合学术发展的事实。再如郑笺,从王肃毛诗问难对它进行批驳开始,责难者代不乏人,甚至斥之为“不守家法之大贼”。直到今天,仍有人砣砣于左郑右毛。实际上,郑笺虽有不少主观武断的地方,但它熔今、古文为一炉,参稽各家,自成一说,是诗经学上的一大进步,郑笺出而三家诗逐渐式微便是明证。又如朱熹诗集传,研究诗经开一代风气,而训诂不及漠学诸家。但我们仔细分析,觉得朱熹就诗论诗,注释中不乏合情合理、通俗易懂之处,还是应当采纳的。至清代,学术的发展使诗经研究大大地向前迈进,但门户偏见并未完全消除。譬如陈奂诗毛氏传疏,唯毛传是尊;而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则明显倾向三家诗说。这两本著作虽然观点互相龃龉,却不妨碍我们择取各自的合理部分。总之,爬梳抉剔,去疵存瑜,是我们的努力目标。此外,在注释中,我们还致力于运用说文、尔雅、广雅等字书,揭示诗经中不少字词的本义、引申义或假借义的关系。有些关键字,甚至不避重复地训释。这样做09日在帮助读者将眼光扩展到先秦古汉语词义的演变上去,或许能通过读诗得到更多的收获。解放后,甲骨金石文字的研究大大发展,地下文物屡见出土,这些成果开拓了我们的眼界,也丰富了本书的内容。学术是永远向前发展的,诗经研究也必然会不断攀向新的高峰。可以说,这是我们在众多注本之后仍希望将自己的一点心得奉献给读者的原因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