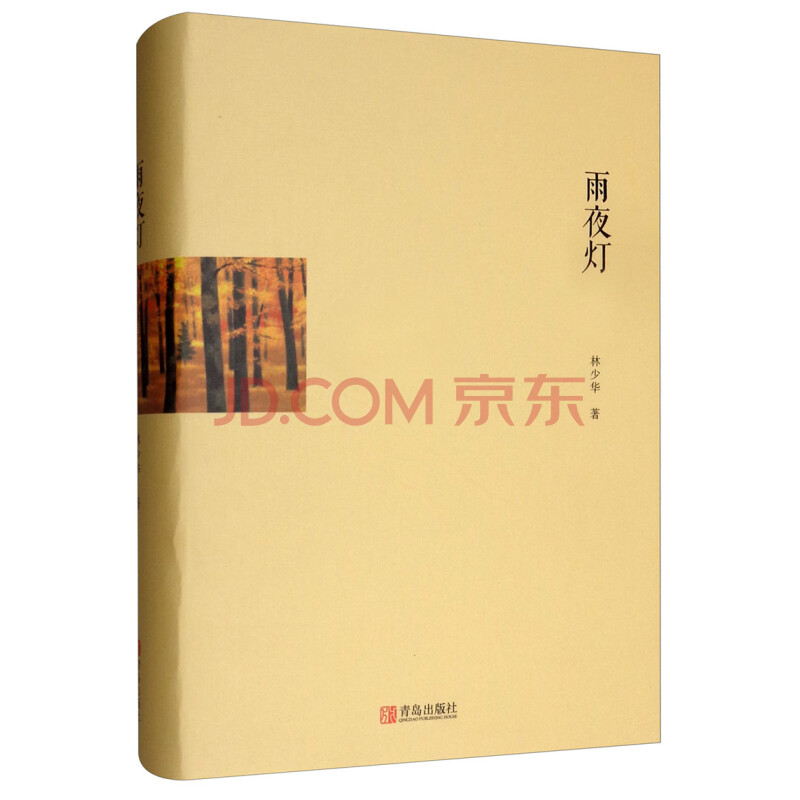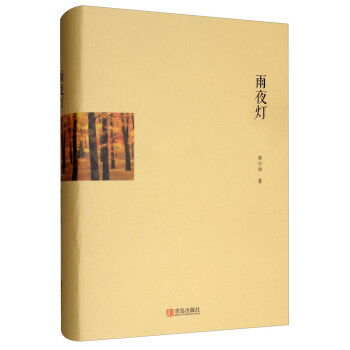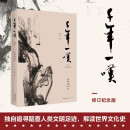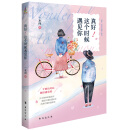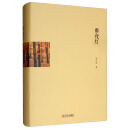内容简介
《雨夜灯》主要内容包括不想回城,中国何必在舌尖,教育就是留着灯,诗意正在失去。
目录
第一编 不想回城
无法洄游的“鲑鱼”
往日故乡的腊月
拜年:难忘磕头
春节的喜鹊
夜半听雨
倪萍的姥姥和我的姥姥
青州的柿子
永恒的风景
“初恋”:我的
第一份工作
醉卧钱塘
乡间使生活更美好
不想回城
城乡差别和牙医
保守也是优势
一贫如洗和“一富如洗”
“香车美女”和三轮摩托
并非另类的婚礼
换了人间
第二编 中国何必在舌尖
“高墙”与“鸡蛋”之间的困惑
城管的眼睛和我们的眼睛
领导说“蒲公英是杂草”
贪官其实很可怜
警车开道与“回避·肃静”
我为什么要改洗脚馆为图书馆
中国何必在舌尖
有钱人“比较研究”
数量关乎尊严
农村:拒绝儿子
车:买还是不买,这是个问题
“少不入川……”
“甄嬛体”和“杜甫很忙”
候机大厅里的讲演
美女有树好看吗?
……
第三编 教育就是留着灯
第四编 诗意正在失去
试读
《雨夜灯》:
地无分南北,山无分东西,春节拜年是中国人的传统习俗。不用说,这一习俗原本主要流行于亲朋好友尤其亲戚圈这一群体之中。而我以至我的家族大体算是离群索居者。虽是山东人,但闯关东时还是烟台叫登州府的时代,只知晓祖籍登州府蓬莱县,至于何乡何村有何亲人,早已无从查考了。及至我,虽然出生在东北平原一个足够大的村庄,但还没懂事就随父母迁居县城,辗转之间后来落户在一个只有五户人家的小山村,五户各依山坡而居,往来极少。长大后我只身去省城念书,毕业后只身南下广州,只身东渡日本,二十多年后又只身北上青岛。这就是说,无论祖辈父辈还是我本人,许多岁月都是在背井离乡举目无亲的环境下谋生或求学的,都是广义或狭义上的异乡人。所以,拜年时基本无亲可拜。我猜想这未尝不是我性喜孤独一个客观原因。
不过回想起来,有亲可拜时形成的拜年体验在我也是有的。只是太久远了,得回溯到半个多世纪以前。
我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上小学的。上学前在爷爷奶奶家即我出生的地方断断续续住过两三年。前面说了,那是东北平原上一个大村庄。几代繁衍下来,林姓成了那个村庄的大家族。仅太爷辈就有五位,爷爷辈有十二位。叔叔辈简直数不胜数,有的还穿着开裆裤,后面露着屁股蛋,前面不时闪出“小鸡鸡”,活像打篮球时吹的口哨。姑姑们的数目也肯定不止一个排。大的已经是生产队妇女队长或嫁人了,小的还鼻涕一把泪一把追着母亲要奶吃。幸也罢不幸也罢,我们这支在家族中属长子系列,太爷老大,爷爷老大,父亲在大大小小叔辈中排行第一,也是老大。这么着,我也是老大,在同辈中率先来到这个世界,而且遥遥领先,后续部队若干年后才出现在地平线上。于是尴尬景象出现了,我的辈分最小。也就是说村里大凡林姓都是我的长辈。平时无所谓,尴尬出在春节拜年。
记忆中,拜年主要活动是跪下磕头。当然是晚辈给长辈磕,也就是我要给村庄里的大约一半人磕头。如果把他们全部召集起来齐刷刷列队“稍息”站好或坐好,由我一次性磕完倒也罢了,问题是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因为磕头要讲辈分,讲个体针对性。初一早上,先对着挂在北墙正中家谱上的已故列祖列宗连续磕三个头,再给爷爷奶奶分别磕一个。然后由爷爷领着出门去林氏长辈家里磕。住的并不集中,有的住村东头,有的住村西头。村路满是雪,早晨的太阳照射下来,雪地忽一下子蹿出无数金星金线,刺得眼睛几乎睁不开。路旁院子里偶尔蹦出一个“二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