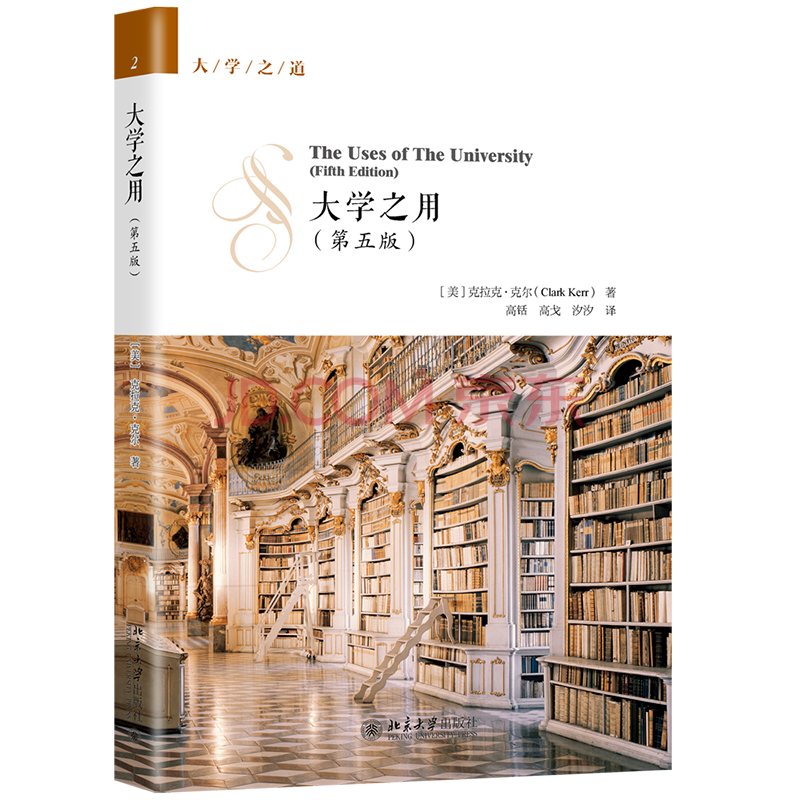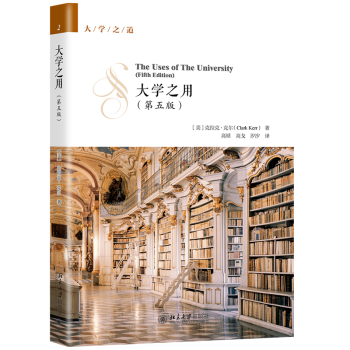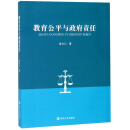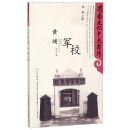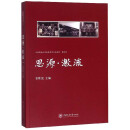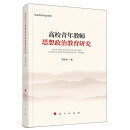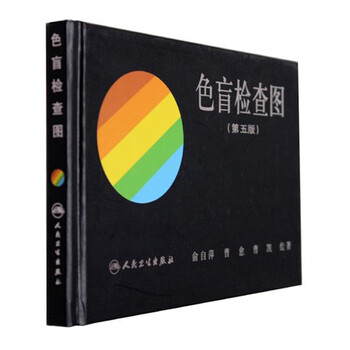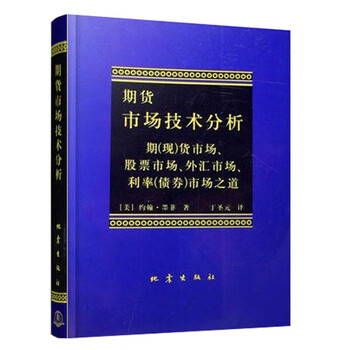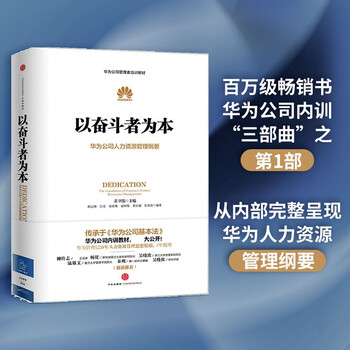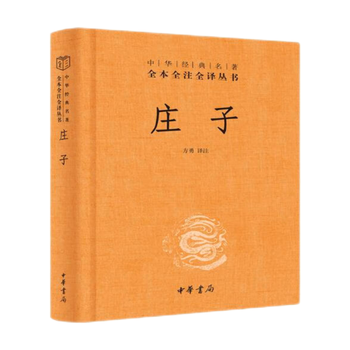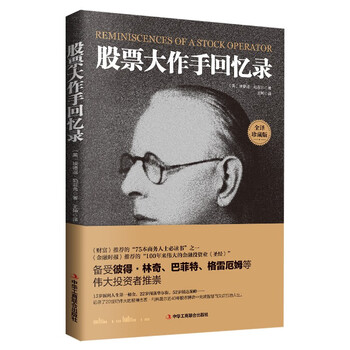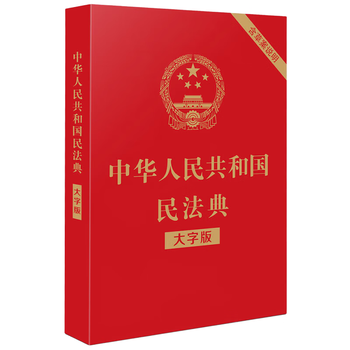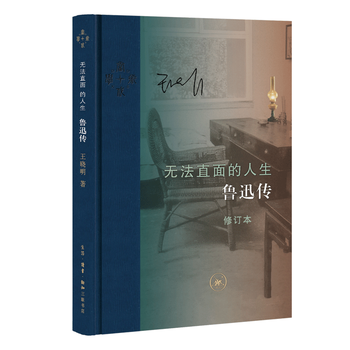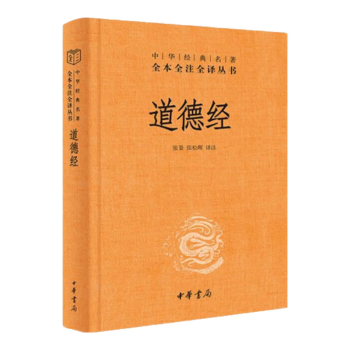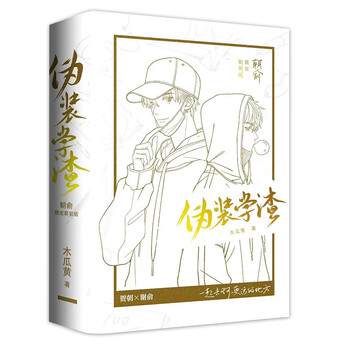内容简介
《大学之用(第五版)》是论述现代研究型大学的奠基之作。其基础是克拉克?克尔1963年4月在哈佛大学戈德金讲座上的著名演说。由于教育家本人对于高教问题持之以恒的深度关注,之后每隔10年都有相关重要文献纳入本书。通过回顾大学的西方历程,特别是美国大学在20世纪的系列转变,本书呈现了研究型大学的价值与困境、高等教育机构的领导人如何保护大学的自主性和公众福利等系列重大问题。
精彩书评
任何一本书都没有对现代研究型大学提供过如此深入的描述,或者对它特有的紧张与问题做出过如此深刻的评论。……任何人想了解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美国研究型大学的话,就必须从仔细阅读本书开始。
——哈佛大学前校长,德里克·博克
这仍然是对研究型大学这一美国出色而不被理解的发明所做的介绍。或许这是大学校长所写的博学、巧妙和紧凑的书,可是又很明智地能经受时间的考验。
一一西北大学,克里斯托弗 詹克斯
美国高等教育的传奇人物之一所写的新经典。每一新版都包含重要而准确的预测。
一一哈佛文理学院前院长,亨利·罗索夫斯基
目录
高等教育的新世纪(2001年序)
1963年序
第一章 巨型大学的理念
第二章 联邦拨款大学的现实
第三章 才智之都的未来
第四章 20世纪60年代造反以后的再思考
第五章 试图改革的失败
第六章 对研究型大学黄金时代的评论
第七章 一个新的时代?从增加联邦财富到增加州的贫困
第八章 艰难的选择
第九章 狐狸世纪的“才智之都”?
专名对照表
试读
巨型大学的理念(第一章开篇部分)
大学开始时是一个单一的共同体——老师和学生的共同体。甚至可以说,它具有灵魂,即某种生机勃勃的核心原则。今天,大型的美国大学就是用一个共同的校名、共同的校务管理委员会和有关的目标结合在一起的一系列共同体及活动。对这种巨大的转型,有些人表示遗憾,许多人表示同意,还有少数人感到得意。但是,这应当得到所有人的理解。
今天的大学某种程度上或许可以通过它同过去的情况作比较而得到了解——同红衣主教纽曼的学术修道院作比较,同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的研究机体作比较。这些都是它从中派生的理想类型,它们仍然构成它的一些居民的幻想。可是现代的美国大学既不是牛津大学也不是柏林大学,它是世界上的一种新型机构。作为一种新型的机构,它不是真正的私立,也不是真正的公立;它既不完全是世界的,也不完全脱离世界。它是独特的。
把“大学的理念”表达得最好的或许是红衣主教纽曼在一个多世纪以前从事建立都柏林大学时所说的话。他的观点反映了当时他所在的牛津大学的发展现状。红衣主教纽曼写道,一个大学是“一切知识与科学、事实与原则、探究与发现、实验与思辨的至高保护力,它划出才智的领域,使任何一方既不侵犯也不投降”。他赞成“博雅知识”(liberal knowledge),说“有用的知识”是“一堆糟粕”。
纽曼特地同培根的幽灵作斗争,培根在大约250年前曾经谴责“那种对心智的崇拜……人们由此过多地脱离对自然的思考以及对经验的观察,一直在自己的理性和幻想中反复折腾”。培根相信知识应当是为了人类的福祉和裨益,认为它“不应当像只满足取乐和虚荣的妓女,或者为主人驱使的女奴;而应当是能传宗接代和愉悦欢娱的妻室”。
纽曼对此回答称:“知识可以是它本身的目的。人类心智的构成特点在于:任何一种知识,如果真的是知识的话,就是它本身的酬报。”他在一次对培根的尖锐攻击中说:“先生,你会说,功利哲学至少起了它的作用。我承认——它目标低下,但它完成了它的目标。”纽曼觉得其他机构应当从事研究,因为“如果大学的目的是科学与哲学的探索,那么我真不明白大学为什么要招收学生”——这个看法赢得了今天学生们挖苦式的模仿,他们时常认为他们的教授对他们根本不关心,关心的只是研究。纽曼说,大学的训练“旨在提高社会的智识风尚,培育公众的心智,纯洁国家的情趣,为大众的热情提供真实的原则,为大众的渴求提供确定的目标,使时代理念开阔而清醒,使政治权力便于行使,使私人生活的交往温良优美”。它使人“能出色地担任任何职务,能熟练地掌握任何问题”。
这个美妙的世界就在它被如此美妙地描绘时就已永远地破碎了。1852年,正当纽曼写作(《大学理念》)的时候,德国的大学正成为新的楷模。民主、工业与科学革命都在西方世界大力进行。“在任何社会里游刃有余”的先生们很快对什么都不在行了。科学开始取代道德哲学的地位,研究开始取代教学的地位。
用弗莱克斯纳的话来说,“现代大学的理念”已经在诞生了。弗莱克斯纳在1930年说,“大学不是处在一个时代的社会总体组织外部,而是在其内部。……它不是分隔开的,不是历史的,尽可能不顺从于或多或少的新势力和新影响。正相反……它是时代的表述,也是对今日和未来发生着的影响”。
很清楚,1930年时“大学已发生了深远的变化——通常朝着它们所参与的社会演变的方向”。这种演变使系科成为大学,出现新的系科;越来越多的研究所出现了;成立了巨大的研究型图书馆;把进行思索的哲学家变成实验室里或者图书馆书库里的研究者;从专业人员手中取来药物交到科学家之手,等等。不是关心学生个体,而是关注社会的需要;不是纽曼的“自然规律的永恒真实性”,而是新事物的发现;不是多面手,而是专门家。在弗莱克斯纳的话里,大学成为“一个有意识地致力于追求知识、解决问题、鉴别成就以及培训真正高水平人才的机构”。一个人不再可能“精通一切”——纽曼的万能通才人物一去不复返了。
但是正当弗莱克斯纳写到“现代大学”的时候,它却又不存在了。洪堡的柏林大学正在被玷污,就像柏林大学曾经玷污牛津大学的灵魂那样。大学包罗了太多的东西。弗莱克斯纳自己抱怨说,它们是“中等学校、职业学校、教师培训学校、研究中心、‘进修’机构、生意事务——如此等等,一股脑儿”。它们从事“难以置信的荒唐活动”,处理“一大批无关紧要的事务”。它们“不必要地使自己丢份儿、庸俗化和机械化”。最糟糕的是,它们成了“公众的‘服务站’”。
甚至是哈佛大学。弗莱克斯纳核算:“哈佛的总支出中不到1/8用于大学应当进行的大学核心学科。”他奇怪的是:“谁把哈佛逼上这条邪路?谁也不是。它喜欢这样;这种事情喜欢这样。”这显然不讨弗莱克斯纳的喜欢。他希望哈佛摆脱商学研究生院,如果它必须存在的话,就让它成为“波士顿商学院”。他也不要新闻学院和家政学院,不要足球课、函授课程以及其他
前言/序言
高等教育的新世纪(序言)
我在1963年哈佛大学所作的戈德金演说戈德金演说全名为“戈德金演说——论自由政府与公民责任之要旨”,最初为纪念埃德温·劳伦斯·戈德金(1831—1902)而创设于1903年。该演说在哈佛大学公共行政研究生院主持下每年举行一次,此研究生院在1966年改名为约翰·F.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译者注中说:“美国的大学正处在历史的转折点:虽然维系着往昔,却正在摆向另一个方向。”我想我知道它们当时正在摆向何处,而历史已经证明我总的说来是对的,我当时正瞩目于20世纪末的远景。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21世纪,我再一次看到美国的大学处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可是,这一次我看到这种转折在来自许多方向的风势中飘忽摆动——可不是温和的微风!所以我加了新的一章,回顾1963年的情景,勾画2000年所显露出的一些未来的可能,以及一些行动的方针。我知道自己不再具有1963年时的正常视力,但仍然想看看路途上出现了什么——我看到路上满是坑坑洼洼,盗贼密布,通向不明的终点。
因此,《大学之用》的第五版以对比1963年与2000年情况的新的一章收尾。前面的第一、二、三章是我原来的戈德金演说。然后是我就20世纪其余时期大约每隔10年的发展态势所写的一些论述,它们也收录在其后各版中。
第四章写于1972年,所涉及的是60年代学生造反以后我的一些反应。我在1963年的演说成了学生活跃分子的靶子。他们不喜欢我所描述的新的大学世界。学生们却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也是不喜欢这个新世界的病态的,而且是其最早的和主要的批评者。“巨型大学”(multiversity)成了“克拉克·克尔的巨怪”,甚至暗指我是“典型的法西斯主义理论家”。“只要加一句话,克尔的书就会成为典型的法西斯主义理论家的著作。”随后,在伯克利的斯普劳尔广场上我被简化为“法西斯分子”。人们可能会认为一个大学校长的明智做法是什么也不要写,或者要写的话就只写些老生常谈。我为了当一名诚实的和现实的评论者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第五章写于1982年,它回顾了学生造反以后尝试学术改革的十年。这个时期产生了许多宣言但没有多少持久的效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师生积极分子治校方法的“参与性民主”只是昙花一现。主要的长久性改革是设置了一批颂扬族群、种族和性别多样性的课程,通常在大的大学中会影响到1%或者不到1%的课程设置。学术改革的这一经验说明,一些教授在注视外部世界时可以多么激进,而当他们向内注视自己时又是多么保守——这是一种分裂的人格。
第六章是我在1995年版中增加的三篇评论中的第一篇。回顾起来,现在我注意到它们总体上都有着悲观的调子:本科生“自由教育”的衰亡,大学被学科领域、意识形态、性别和族群地位所分散割裂。但与此同时,可以清楚看到美国的大学已成为世界上至高无上的研究机构。它取代了德国大学在19世纪末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领导世界的地位。
1963年的社会氛围是愉悦、快活的,但到1994年我写论文的时候,社会情绪却主要是沮丧和疑惑。为什么精神有这么大的变化呢?随着经济生产率增长降到历史低水平以下,资金的流入减少了。联邦政府在“二战”以后对高等教育的巨大热情(表现为对研究、发展和学生拨款及贷款的支持)已经消竭。
学生入学的快速增长趋势已经放慢,虽然人们所预计的80年代“人口萧条”并未出现。
学术改革运动已经失败。最后一次企图恢复重视本科生及其自由教育的努力——在圣克鲁斯加利福尼亚大学——落败了,早些时候在芝加哥大学的哈钦斯试验和哈佛大学的“红皮书”改革也是如此。大学界分裂为一系列互相争斗的成分。经济萧条减少了国家对高等教育的资助。1963年的“光明在前”变成了1994年的“暗云四起”。
当时我并没有认识到90年代中期学术界情绪的变化究竟有多大。它已成为各界中最糟糕的状况。高等教育在1980年已进入萧条状态而且持续如此——学术大萧条。
第七章也写于1994年,它继续讨论这一萧条,特别注意到了高等教育外部资金的减少。它也痛感高等教育“行会”地位的瓦解以及亨利·罗索夫斯基所谓的专业人士“公民道德”的沦丧。
第八章是1995年版增加的评论中的最后一篇,继续描述似乎会在今后出现的一些艰难选择,特别是高等教育长期面对的却从未找到满意结果的一些选择。一个就是如何更好地使用资金,另一个是高等教育如何更好地帮助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可是,在探讨美国高等教育的未来时(这是我在1963年就已开始的工作),我以谨慎的乐观态度结束了此章。
第九章为这一系列论文作结。一本书能持续如此之久,这要归功于哈佛大学出版社,尤其是主编艾达·唐纳德的善意与持久的兴趣,现在我谨将这些论文呈献给他。这一章提出了摆在面前的一些挑战,它们的复杂性使我们在1963年所面临的任何情况都相形见绌。本章结束时我的态度可以称之为“谨慎的困惑”,但我深信,新知识仍然在使世界运转,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