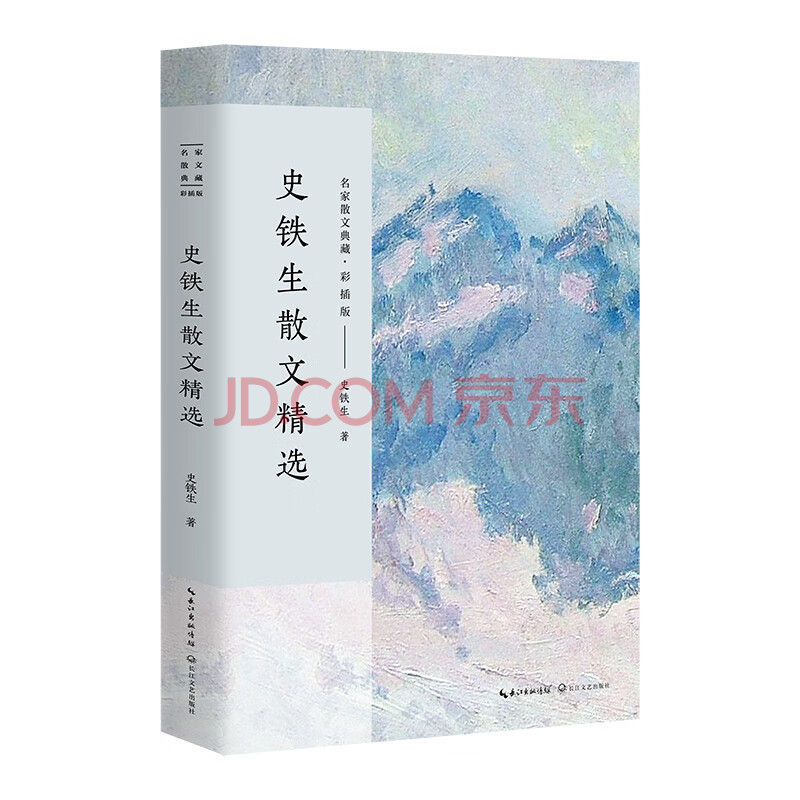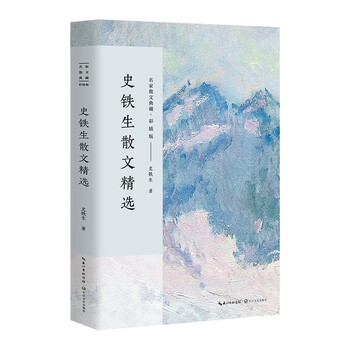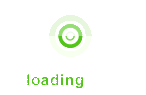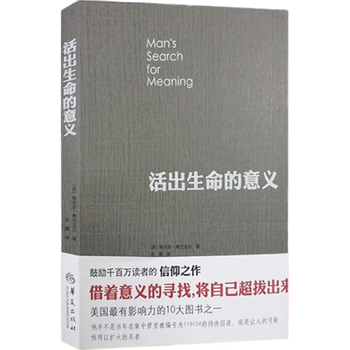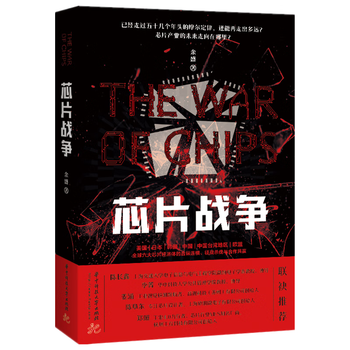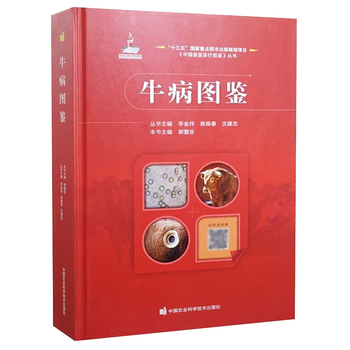内容简介
文坛大家史铁生先生以他质朴通透而又充满生命哲理的作品,被誉为中国当代文坛大美的收获。在或冥思深沉,或幽默旷达,或深情回望的文字中,史铁生以不羁的心魂漫游于世界和人生的无疆之域,在生命深刻的困境中,对人性、神性和人生*意义进行着艰苦卓绝而又辉煌壮丽的追问与眺望。他的作品和为人一样,豁达、温暖而宽容,照亮了在黑夜中前行的我们。
为展现这位当代文坛大家的风貌,我们特精心制作出版了这部《史铁生散文精选》(彩插版)。收入了作者如《我与地坛》、《秋天的怀念》、《好运设计》、《病隙碎笔》、《故乡的胡同》、《人间智慧必在某处汇合》、《悼路遥》、《给盲童朋友》、《给杨晓敏的信》等散文名篇。
全书力求将史铁生先生各时期的散文经典之作收入其中,展现他的精神追寻之旅和人生哲理之思,从而宽慰并照亮当代人的心灵,厘清前行道路上的迷思,有益于我们当下的生活。
目录
目 录
亲情卷
秋天的怀念 / 003
合欢树 / 005
我21岁那年 / 008
地坛卷
我与地坛 / 023
想念地坛 / 042
生命卷
好运设计 / 049
爱情问题 / 069
足球内外 / 080
病隙碎笔3 / 092
病隙碎笔4 / 117
上帝的寓言 / 124
游戏?平等?墓地 / 126
轻轻地走与轻轻地来 / 135
扶轮问路 / 140
哲理卷
无病之病 / 149
没有生活 / 153
墙下短记 / 156
记忆迷宫 / 165
宿命的写作 / 172
复杂的必要 / 175
熟练与陌生 / 177
放下与执着 / 180
诚实与善思 / 185
无答之问或无果之行 / 196
神位·官位·心位 / 205
昼信基督夜信佛 / 211
人间智慧必在某处汇合 / 228
往事卷
我的梦想 / 239
故乡的胡同 / 243
有关庙的回忆 / 246
黄土地情歌 / 256
相逢何必曾相识 / 264
悼路遥 / 271
书信卷
给盲童朋友 / 277
给安妮?居里安的信 / 279
给杨晓敏的信 / 284
给肖瀚 / 290
试读
秋天的怀念
双腿瘫痪后,我的脾气变得暴怒无常。望着望着天上北归的雁阵,我会突然把面前的玻璃砸碎;听着听着李谷一甜美的歌声,我会猛地把手边的东西摔向四周的墙壁。母亲就悄悄地躲出去,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偷偷地听着我的动静。当一切恢复沉寂,她又悄悄地进来,眼边红红的,看着我。“听说北海的花儿都开了,我推着你去走走。”她总是这么说。母亲喜欢花,可自从我的腿瘫痪后,她侍弄的那些花都死了。“不,我不去!”我狠命地捶打这两条可恨的腿,喊着:“我可活什么劲!”母亲扑过来抓住我的手,忍住哭声说:“咱娘儿俩在一起儿,好好儿活,好好儿活……”
可我却一直都不知道,她的病已经到了那步田地。后来妹妹告诉我,她常常肝疼得整宿整宿翻来覆去地睡不了觉。
那天我又独自坐在屋里,看着窗外的树叶“唰唰拉拉”地飘落。母亲进来了,挡在窗前:“北海的菊花开了,我推着你去看看吧。”她憔悴的脸上现出央求般的神色。“什么时候?”“你要是愿意,就明天?”她说。我的回答已经让她喜出望外了。“好吧,就明天。”我说。她高兴得一会坐下,一会站起:“那就赶紧准备准备。”“哎呀,烦不烦?几步路,有什么好准备的!”她也笑了,坐在我身边,絮絮叨叨地说着:“看完菊花,咱们就去‘仿膳’,你小时候最爱吃那儿的豌豆黄儿。还记得那回我带你去北海吗?你偏说那杨树花是毛毛虫,跑着,一脚踩扁一个……”她忽然不说了。对于“跑”和“踩”一类的字眼儿,她比我还敏感。她又悄悄地出去了。
她出去了,就再也没回来。
邻居们把她抬上车时,她还在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我没想到她已经病成那样。看着三轮车远去,也绝没有想到那竟是永远的诀别。
邻居的小伙子背着我去看她的时候,她正艰难地呼吸着,像她那一生艰难的生活。别人告诉我,她昏迷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我那个有病的儿子和我那个还未成年的女儿……”
又是秋天,妹妹推我去北海看了菊花。黄色的花淡雅,白色的花高洁,紫红色的花热烈而深沉,泼泼洒洒,秋风中正开得烂漫。我懂得母亲没有说完的话。妹妹也懂。我俩在一块儿,要好好儿活……
1981年
合欢树
十岁那年,我在一次作文比赛中得了第一。母亲那时候还年轻,急着跟我说她自己,说她小时候的作文做得还要好,老师甚至不相信那么好的文章会是她写的。“老师找到家来问,是不是家里的大人帮了忙。我那时可能还不到十岁呢。”我听得扫兴,故意笑:“可能?什么叫可能还不到?”她就解释。我装作根本不再注意她的话,对着墙打乒乓球,把她气得够呛。不过我承认她聪明,承认她是世界上长得最好看的女的。她正给自己做一条蓝底白花的裙子。
二十岁,我的两条腿残废了。除去给人家画彩蛋,我想我还应该再干点别的事,先后改变了几次主意,最后想学写作。母亲那时已不年轻,为了我的腿,她头上开始有了白发。医院已经明确表示,我的病目前没办法治。母亲的全副心思却还放在给我治病上,到处找大夫,打听偏方,花很多钱。她倒总能找来些稀奇古怪的药,让我吃,让我喝,或者是洗、敷、熏、灸。“别浪费时间啦!根本没用!”我说。我一心只想着写小说,仿佛那东西能把残疾人救出困境。“再试一回,不试你怎么知道会没用?”她说每一回都虔诚地抱着希望。然而对我的腿,有多少回希望就有多少回失望。最后一回,我的胯上被熏成烫伤。医院的大夫说,这实在太悬了,对于瘫痪病人,这差不多是要命的事。我倒没太害怕,心想死了也好,死了倒痛快。母亲惊惶了几个月,昼夜守着我,一换药就说:“怎么会烫了呢?我还直留神呀?”幸亏伤口好起来,不然她非疯了不可。
后来她发现我在写小说。她跟我说:“那就好好写吧。”我听出来,她对治好我的腿也终于绝望。“我年轻的时候也最喜欢文学。”她说。“跟你现在差不多大的时候,我也想过搞写作。”她说。“你小时候的作文不是得过第一?”她提醒我说。我们俩都尽力把我的腿忘掉。她到处去给我借书,顶着雨或冒了雪推我去看电影,像过去给我找大夫,打听偏方那样,抱了希望。
三十岁时,我的第一篇小说发表了,母亲却已不在人世。过了几年,我的另一篇小说又侥幸获奖,母亲已经离开我整整七年。
获奖之后,登门采访的记者就多。大家都好心好意,认为我不容易。但是我只准备了一套话,说来说去就觉得心烦。我摇着车躲出去。坐在小公园安静的树林里,想:上帝为什么早早地召母亲回去呢?迷迷糊糊的,我听见回答:“她心里太苦了。上帝看她受不住了,就召她回去。”我的心得到一点安慰,睁开眼睛,看见风正在树林里吹过。
我摇车离开那儿,在街上瞎逛,不想回家。
母亲去世后,我们搬了家。我很少再到母亲住过的那个小院儿去。小院儿在一个大院儿的尽里头,我偶尔摇车到大院儿去坐坐,但不愿意去那个小院儿,推说手摇车进去不方便。院儿里的老太太们还都把我当儿孙看,尤其想到我又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