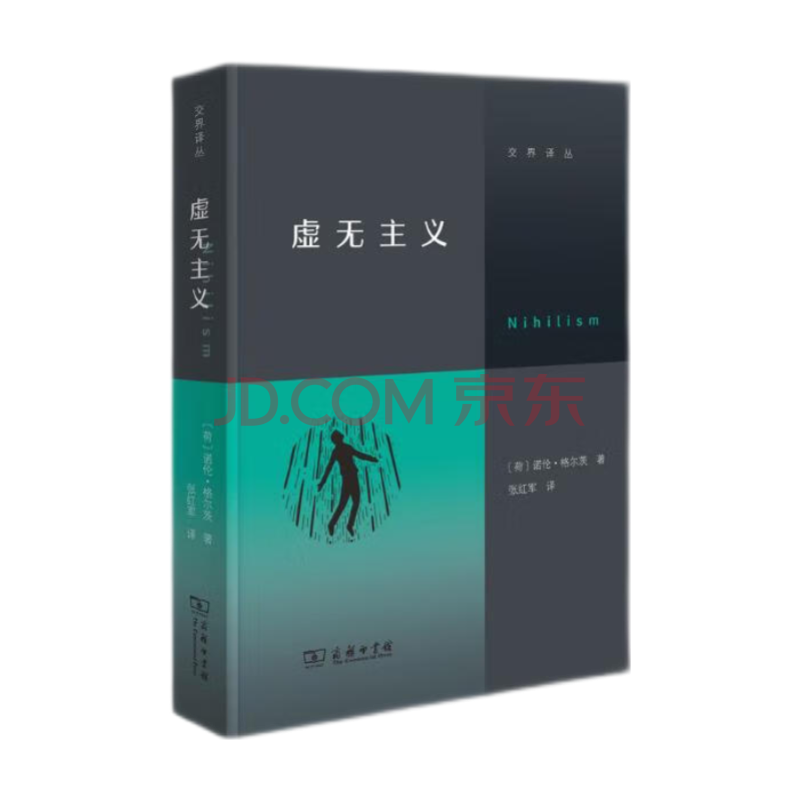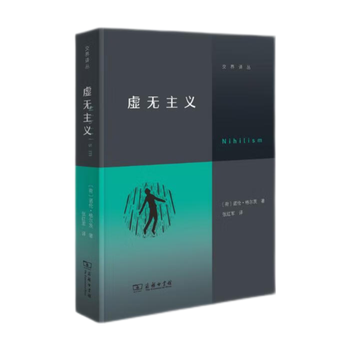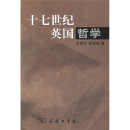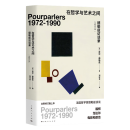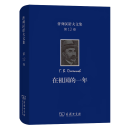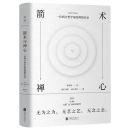内容简介
当某人被贴上虚无主义者的标签时,通常并不意味着赞美。虚无主义究竟是什么?是浑浑噩噩?还是认为生活不值得?或是相信一切都无所谓?诺伦?格尔茨指出,如果我们学会辨认虚无主义的多种类型,那么我们就能学会区分有意义与无意义。从苏格拉底、笛卡尔,到汉娜?阿伦特、让-保罗?萨特,本书选自“麻省理工学院基本知识系列”丛书,围绕公共话题,为大众读者提供专业概述。它追溯西方哲学中的虚无主义历史,对人们所熟知的哲学家及其思想提供了一种颇有新意和启发性的理解。结合当代社会的日常情景,以生动有趣的案例,在与“悲观主义”“犬儒主义”和“无动于衷”的对照下澄清何为“虚无主义”,以及什么是虚无主义的思维方式,直击现代人灵魂,引发共鸣与反思。
精彩书评
格尔茨的精妙而有说服力的作品有效地解释了虚无主义如何为自我探究和创造力提供动力。
――《出版人周刊》
这是对政治和个人哲学中一些紧迫问题的精彩介绍。那些想探索尼采思想、存在主义和后现代性在西方世界中的相互作用的人将会喜欢这本书。
――《精选》
目录
第一章 为什么“一切都无所谓”有所谓?
第二章 何谓虚无主义的历史?
第三章 虚无主义(不)是什么?
第四章 虚无主义是什么?
第五章 虚无主义在何处?
第六章 何谓虚无主义的未来?
词汇表
注 释
参考文献
延伸阅读
索 引
试读
第五章?虚无主义在何处?
既然在前面几章中我们已经就“虚无主义是什么”这个问题进行了非常详细的分析,那么在这一章中我们就可以开始分析“虚无主义在何处”这个问题了。虚无主义不只是对生活本来就有意义的观念的拒绝,还能被视为一种回应焦虑的特定方式,而这种焦虑来自发现生活本来毫无意义的事实。虚无主义者不像悲观主义者那样绝望,不像犬儒主义者那样厌恶一切,不像凡事无所谓者那样超脱。虚无主义者可以是乐观主义的、唯心主义的和富于同情心的,因为他们的生活目标是幸福,就像童年那样快乐和无忧无虑,就像他们在发现生活缺乏意义前那样快乐和无忧无虑——他们曾认为自己长大后应该能从生活中发现这种意义。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虚无主义者回应生活的无意义性的方式如果被简化成一组单独事件,就不能被正确理解。一方面,虚无主义就像一种疾病,一种能够在个体之间快速散播、具有传染性的态度。另一方面,虚无主义之所以具有传染性,是因为虚无主义的生活方式是虚无主义者生来就有的且和他人共享的生活方式的产物。
考虑到被一群不计后果的人包围的危险,我们可能会期待社会应该积极加入与虚无主义的斗争。尽管“虚无主义者”作为一个负面标签被应用于日常生活,但我们发现虚无主义的逻辑得到社会各个组成部分的支持。但虚无主义的传播可能不只由于虚无主义的态度在个体间的相互传染,还可能由于那种鼓励虚无主义态度的文化助长了其传染性。本章将要探讨的,正是这种文化影响。在电视上、教室里、工作中和政治事务中都可以发现虚无主义。
家里的虚无主义
既然虚无主义来自摆脱对自由的焦虑的欲望,认为当代通俗文化会拥抱虚无主义便不会令我们惊讶了——如果我们求助于通俗文化是为了娱乐、舒适和消遣,那么通俗文化和虚无主义至少已经共享了减轻压力的目标。但通俗文化值得关注的地方,不是它是否吸引虚无主义者,而是它是否有助于诱导人变得虚无主义。
父母们一直都在担忧通俗文化的败坏性影响,关心诸如看电视是否会让孩子变蠢或玩电子游戏是否会让孩子变得更加暴力这样的问题。这种关切主要考虑的是通俗文化的内容,而非消费通俗文化的设备。其中一个原因是,在屏幕前消磨时间已经变得如此平常,以至于我们不再质疑这种行为。换句话说,我们只是质疑人们在看什么,而没有问过为什么。
作为一种休闲行为的观看,在屏幕出现之前很久就已经存在了。但因为有了屏幕,我们就不再需要去别的地方观看什么东西了。哲学家金特?安德斯在他1956年的论文《作为幻影和矩阵的世界》中指出,收音机和电视有助于创造他所谓“大众中的人”(the mass man)。收音机和电视节目让对话和他人的对话充斥整个家庭,却让消费这些节目的人的对话变得不仅困难还招人讨厌。还有,为了让每个人都能观看屏幕,电视重新规定了整个家具的布局结构:人们不能面对面地坐着,而都面对着屏幕坐着。由于供人消费的事件都是为了消费而被记录和重演的,收音机和电视不仅让离开家去目击事件变得没有必要,还使得事件的演出按照消费的需要来记录和重演。于是,收音机和电视提供给我们的,并非真实生活的经验,而是一种伪现实。我们可以在我们的伪生活(坐在他人旁边消费,而非和他人一起消费)中伪经历(坐在沙发里消费)这种伪现实(为了大众消费而上演的事件)。
对安德斯来说,真正值得争论的事情,是收音机和电视重塑了我们所认为的“经验”“交流”,甚至是“亲密”。我们和节目中人物形成关系的方式,不同于我们与舞台上人物形成关系的方式,因为收音机和电视让人物和我们近距离接触,以至于他们似乎就在对我们讲话,似乎他们让我们走进了他们家里,正如我们让他们走进我们家中那样。哲学家西奥多?阿多诺在他1954年的论文《怎样看电视》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即这样的亲密关系让我们很容易就认同电视节目中的人物,尤其是在把他们置于熟悉的场景、熟悉的情境和熟悉的矛盾冲突中来描述时。尽管这些人物可能有类似于我们自己的工作、家庭和问题,但他们生活的稳定性和安全性不同于我们的。
情景喜剧中的家庭或许会碰上麻烦,但不消30分钟(如果除去广告就剩下22分钟),麻烦就会解决。不管为了创造喜剧性和戏剧性的张力会有怎样的混乱突然暴发,这种混乱终将消失,并且似乎不会再次出现,而秩序终将恢复。程式化的节目让人觉得非常舒适,因为它让我们觉得那些似乎令人担心的情境最终会完美收场,让我们觉得我们行为的后果其实并不重要。正是这种对舒适的需要,把我们拉到屏幕前,去观看程式化的节目。
但我们知道这样的节目是令人舒适的,并不意味着我们知道这样的节目会对我们产生别的影响。阿多诺关注的是,在我们感到舒适的同时,这样的节目还会在我们内心引发一种沾沾自喜的感觉,尤其是我们在每一集节目结束返回现实的时候。于是乎,电视不仅在娱乐我们,还在教育我们:维持现状是善;破坏现状
前言/序言
中译本序言
如果允许我用一个关键词来描述我们这个时代,我会选择“虚无主义”这个概念,因为我们仍然身处现代性的时代,而“虚无主义是现代性的精神本质” 。
虚无主义作为概念最早出现在18世纪,在19世纪发展成为社会思潮,在20世纪更是风起云涌,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到了21世纪,虚无主义俨然成为我们所面临的最大难题。也许会有人认为我是危言耸听,在他们看来,人类文明已经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因为不断地发展、进步和创新而能够保持生机勃勃,也因此能够摆脱生老病死的周期循环。但是,人类文明从传统到现代的“进步”是有代价的。其中,最沉重的代价就是虚无主义。
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虚无主义是和尼采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都知道他的名言:“虚无主义站在门口了:我们这位所有客人中最阴森可怕的客人来自何方呢?” 就此而论,我们和尼采,或者说尼采和我们,乃是同时代的人。显然,虚无主义在这个历史时刻出现在我们面前并非偶然。在我看来,其主要原因是轴心时代的没落,是原本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一系列价值观念出现了问题。按照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理论,在公元前800—前200年这几百年的时间里,人类各大文明相继构建起各自的核心理念,如希腊的哲学、中国的先秦诸子百家、印度的奥义书和佛陀、伊朗的琐罗亚斯德以及巴勒斯坦的犹太先知等等。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理论虽然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但仍然不失为一种解读人类文明的理论框架。它认为轴心时代的起因是人类开始意识到整体的存在、自身和自身的限度:“人类体验到世界的恐怖和自身的软弱。他探寻根本性的问题。面对空无,他力求解放和拯救。通过在意识上认识自己的限度,他为自己树立了更高的目标。他在自我的深奥和超然存在的光辉中感受绝对。” 过去我把轴心时代的问题解释为虚无主义的挑战,现在我会在“虚无”和“虚无主义”之间做一区别:人类文明面对“虚无”而为自身寻求安身立命的基础和根据,但也由此产生了“虚无主义”问题。
轴心时代形成的文明理念固然具有多重作用:它是关于世界的某种合理性的解释,是维系一种文明之整体性的价值观念,也是个人安身立命的基础和根据。然而,这些价值观念毕竟只是极少数圣贤的“发明”或“创造”,绝大多数人则浑浑噩噩、懵懂无知,往往把这些价值观念视为天经地义、自然而然的客观存在或永恒之物。在一个相信传统、依赖传统的社会中,这些价值观念通常很少引起人们的怀疑,即使有人怀疑,也只是导致对既有价值观念的修补和完善而已。然而,近代以来从西方社会传播出去的各种思想革命、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等等,最终导致全世界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人类文明从此开始被无限开放的未来指引着,迈向发展、进步与创新的方向。正是在这一转型过程中,轴心时代形成的传统价值观念逐渐失去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力,人类个体也逐渐丧失安身立命的基础和依据。不仅如此,人类个体还逐渐认识到,他们曾经依赖的价值观念不过是少数圣贤的发明创造,而被这些发明创造所遮盖的,是圣贤们早已发现的生命/生活的虚无本性。正因为如此,我认为虚无主义从人类文明一开始就存在,它因为传统价值观念的阻击而蛰伏了两千多年,但最终还是在尼采所处的19世纪开始“显山露水”,并在今天完全、充分地暴露出来。
不仅如此,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虚无主义隐含于人的“本性”之中。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人是一种居于存在与存在者“之间”的存在者,即“此在”(Dasein)。存在是一切存在者的基础。但只有此在既是存在者,同时又是能够“去存在”(to be)的存在者。这意味着唯有人可以追问自己的存在,而且存在只有通过人这种存在者才能呈现出来。然而因为只有存在者是看得见的,存在在呈现为存在者的时候隐而不显,所以看起来人在追问存在而实际上追问的是存在者,也就是始终把存在当作存在者来把握。海德格尔称之为“存在的遗忘”。如果说存在是人的“本性”,那么可以说人始终在遮蔽着自己的“本性”。海德格尔因此写道:“但真正的虚无主义是在什么地方活动呢?在人们缠住熟悉的存在者不放的地方;在人们以为只要一如既往、按照现在时兴的样子去抓住存在者的地方。这样,人们就把存在问题拒之门外,把存在当作一个‘绝无’(nihil)来对待,而这个无,只要它在那儿,它就以某种方式‘是/在’。把这个存在忘得精光,只知道去追逐存在者,这就是虚无主义。” 就此而论,虚无主义就植根于人的“本性”之中,当他去思自己的本质即存在的时候,存在对他来说相当于虚无,所以无从思起,而他以为把握到的存在始终只是存在者。
如果读者诸君阅读了《虚无主义》这本书,一定会发现海德格尔意义上的虚无主义,与本书作者诺伦?格尔茨意义上的虚无主义是不同的。的确,虽然我还没有说几句话,也已经在好几种含义上使用虚无主义这个概念了。但如果怎么说都是虚无主义,那么虚无主义这个概念也就失去意义了。鉴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