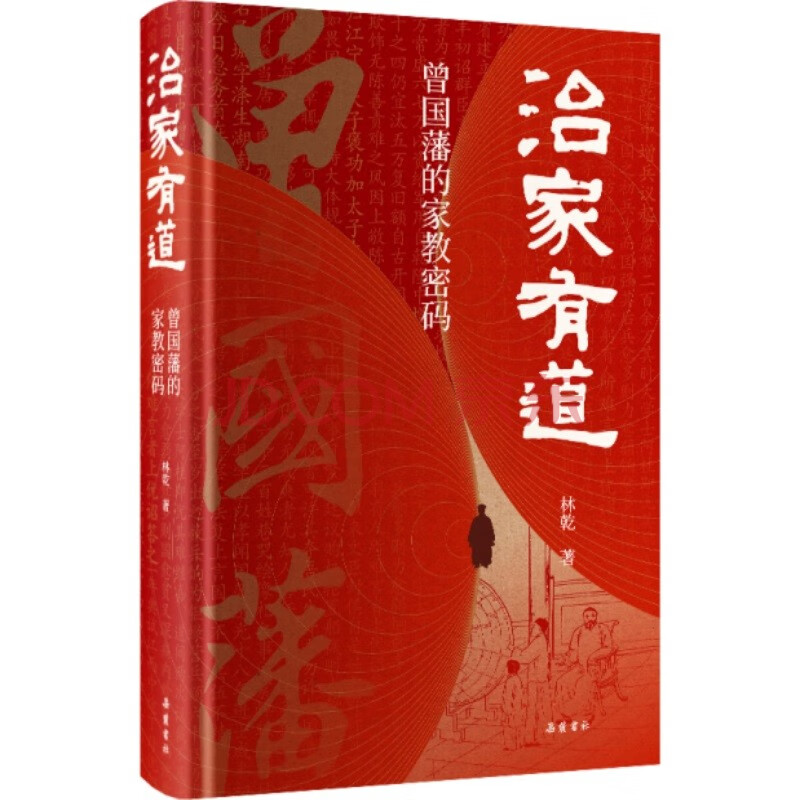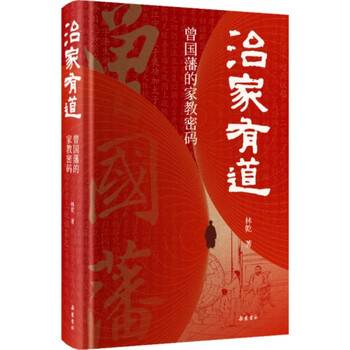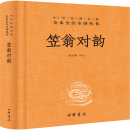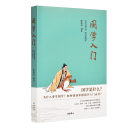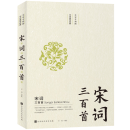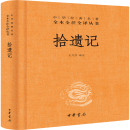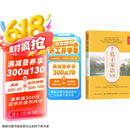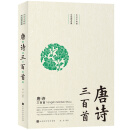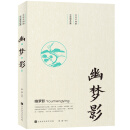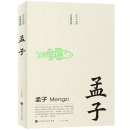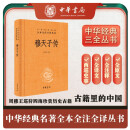内容简介
近现代中国经历了上百年的战乱。但无论社会如何动荡与变幻,曾氏家族总是有子弟成才,有所成就,家族总能够安安稳稳地延续下来,其中必然有原因。这本书就是在挖掘其中暗藏的秘密。
《治家有道》在探寻一个家庭兴旺发达的原因,而其着眼点仍在个人。作者以历史学家的敏锐与细致,根据曾国藩的日记、曾国藩与家人的书信等古籍文献,对曾国藩家训的由来与演变、曾国藩所推崇的一些做法进行解析,总结了一些很有价值,也有可操作性的方法。这些方法既适用于个人,也适用于家庭。
前言/序言
“三代而下,教详于家”,这是明人张一桂对中国古代重视家庭教育的一句经典概括。
多年前我去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参观美第奇家族王宫,颇感惊讶的是,这个家族创造长达三百年的辉煌,特别是在文艺复兴中所发挥的至关重要作用,令人遐思不已。反观中国,也有创造历史的家族,如汉魏到南北朝时期,出现有名的政治门阀,乃至有“王与马共天下”的境况。但进入皇权越发强盛的隋唐以后,这样的家族几成历史的陈迹。百年家族颇不易寻觅。个中原因,值得我们深思。
当曾国藩与他的九弟曾国荃一起受封爵位的时候,曾家也成为中外瞩目第一家,保持或延续家族的荣耀,曾国藩担当起了关键先生,而且,他扮演这样的角色,早在他考中进士,步入翰林院之初,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我个人以为,曾国藩家训中,最可贵之处,是他总结了四类家族(即官宦之家、商贾之家、耕读之家、孝友之家)的“兴衰周期率”。我想,孝友之家是曾国藩特别的“标目”。与我们的常识性判断恰恰相反,他认为官宦之家最易衰败,商贾之家次之,而延续长久的大多是耕读之家和孝友之家。这使我想到南方许多大户人家,特别是徽州地区,几乎门楣上都写有这样一副对联:
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
这可以说是中国家族文化传承的核心价值。为此,第一,曾国藩提出,愿代代出秀才,秀才是读书的种子,世家的招牌,礼仪的旗帜。
第二,曾国藩提出,不以官位高低作为贤肖的标准。这反映出曾国藩对世事的洞明和透彻,也与常人所理解的迥然有别。一般人认为,只有家族出了高官显宦,才能光宗耀祖。曾国藩的四弟曾国潢就这样认为。为纠正这种错误的认识,曾国藩举出历史上很多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例证,包括汉朝的霍光、隋朝的杨素、盛唐宰相李林甫等等。他说这些人生前何尝不是赫奕一时,但不旋踵或遭灭族之诛,或被抄家流配。因此他告诫家人,对权力要有万分的敬畏,不可有丝毫的崇拜,提出“一入官场,即戴罪之身”的著名警示。
第三,曾国藩提出,凡家道长久者,不恃一时之官爵,而恃长远之家规;不恃一二人之骤发,而恃大众之维持。这一思想极为可贵。在传统社会,家族往往因“一人得道”而发迹、兴盛,反之亦然。道理很简单,家族是一个共同体小社会,每一个家庭成员都有责任维护家族的声誉。如果家族中出现“败类”,影响绝非仅其个人。曾国藩认识到,一个家族,如果靠一时的官爵,是断断无法维系长久的,因而,比起“个人”的因素,全家族都要遵守的家规更可靠更持久。而纳入家法族规的内容,一定有长久积累的过程。为此,他早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就提出:后辈子女无法则,立见消败,即便自己贵为宰相,又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他一再要求主持家政的四弟曾国潢“立规条”,要求妻子“事事立个一定章程”。后来,逐渐形成与时俱进又有曾家特色的三代家训。
第四,曾国藩高度重视教育,认为一个担当公职的人,不但要“在邦无怨”,还要做到“在家无怨”。他通过自己多年的阅历体会,认识到人的天赋都差不多,而子女成才与否,是否走正路,关键在于教育。为此他提出“子弟之贤否,六分本于天生,四分由于家教”。他以下围棋为例说:生来就是围棋国手的,那是天赋,“屡学而不知局道,不辨死活者”,那是愚人。“此外,则皆相近之资”,这种情况下就看教育者的作用,“教者高,则习之而高矣;教者低,则习之而低矣”。他又以学习书法为例,说生来笔姿秀挺的,在于天赋,“屡学而拙如姜芽者”,那是愚人。此外“皆相近之姿,视乎教者何如。教者钟(钟縣)、王(王羲之),则众习于钟、王矣;教者苏(苏轼)、米(米芾),则众习于苏、米矣”。如果家长不能正确对待子女的教育,不能及时发现他们的短长,因慨叹子女没有天赋而放弃教育,“是犹执策而叹无马,岂真无马哉”。这就是说,子女都有成为千里马的可能,而能否使潜在的千里马变成现实中的千里马,就在于家长的教育。
早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前,曾国藩就有志编一部《曾氏家训》,并与他的九弟详细道及。但他很快就放弃了,为什么要放弃?他在日记中说:“因采择经史,若非经史烂熟胸中,则割裂零碎,毫无线索……故暂且不作《曾氏家训》。若将来胸中道理愈多,议论愈贯串,仍当为之。”实际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曾家正在发达的路途中,而这一过程的家训积累似乎更有价值。后来曾国藩戎马控惚,几乎没有闲暇时间,就明确以家书、日记代替家训。因而,笔者也以此作为解读曾国藩家训的主要依据,这大概符合曾国藩的原意。
本书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出版的原稿基础上,进行大幅度全面修改。谨此对岳麓书社崔灿社长、马美著总编辑,本书责任编辑刘文主任表达诚挚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