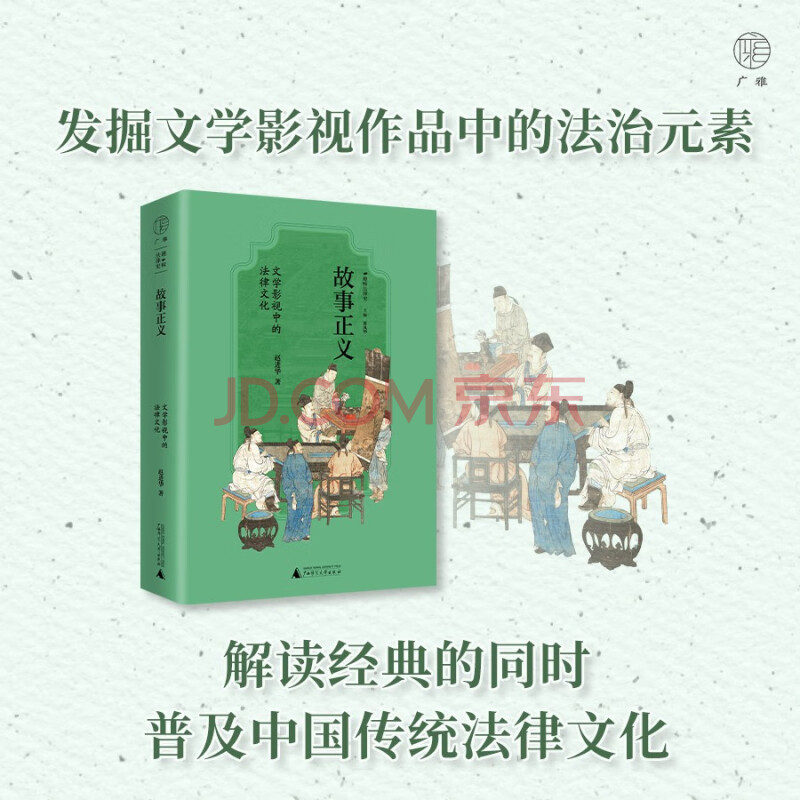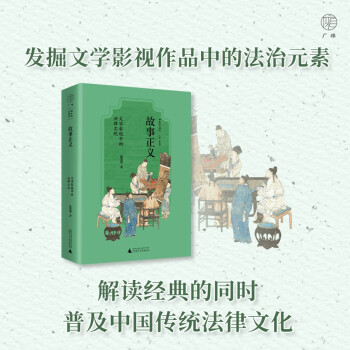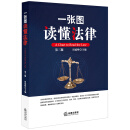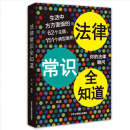内容简介
本书以经典文学作品和热门影视剧为研究素材,以法律史和法律文化为学术底色,发掘经典文学影视作品中的法治元素,解开其中不为人知的法律文化谜题。如通过《聊斋志异》《醒世姻缘传》《红楼梦》等探讨中国古代与身份、婚姻、家庭有关的法律建制和法律实践;借助影视剧《清平乐》《鹤唳华亭》《长安十二时辰》等探讨中国古代与政治、行政有关的法治安排和法律实践。本书在解读文学经典的同时普及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让读者可以具象化地走近古人的法律世界,体会古人的法律情感和法治理想,从而更准确地把握作品的文化内涵,也更深入地理解传统法律文化。
丛书介绍
“趣味法律史”系列(4种)
本丛书旨在从历史上的法律故事与话题出发,以深入浅出和通俗的语言,将故事中的法律史与法律史中的故事呈现给读者。
张田田《木兰无名,缇萦无踪:法律史视野下的女性悲喜剧》;夏婷婷《表象背后:文艺作品中的法律小史》;赵进华《故事正义:文艺影视中的法律文化》;景风华《意义之网:中国法律史的文化之旅》。
精彩书评
在这套丛书的写作过程中,我们的语言文字是轻松随性的,但态度是严谨认真的。面对很多人对中国古代法律抱有的猎奇心态和网络上真假参半的各类传言,我们也希望通过“趣味法律史”丛书,澄清部分对中国传统法的误解,让读者看到法律史的真实面貌。
——景风华(四川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目录
导言 1
壹
在古代,表兄妹到底能不能结婚? 11
十三妹的身份是妾吗? 22
姻缘如何能醒世? 37
严法能奈悍妻何? 53
宋朝男人为何钟情娶小姨子? 66
公主为什么不幸福? 85
裘千尺为什么想不通? 101
贾宝玉挨打反映了什么? 112
贰
为什么说宋朝是中国古代法治的顶峰? 125
范仲淹的好友尹洙因何而死? 139
君主该不该使诈术? 149
太子为什么多不得善终? 156
林九郎是法治派吗? 163
古人为什么喜欢敲登闻鼓? 170
匿丧为什么行不得? 182
夏竦为何没能获谥“文正”? 194
叁
中国古代的理想法官是什么样子的? 203
包公是靠什么断案的? 211
宋江浔阳楼题诗被定谋反冤枉吗? 221
为亲复仇难题如何解? 234
大宋提刑官为何那么牛? 245
宋慈的父亲为何自杀? 256
中国古代的“宰白鸭”是怎么一回事? 265
提利昂的审判为何能打动人心? 276
肆
在古代,庸医会是什么下场? 287
“伤人最少”的侠义之道有什么问题? 294
冤案的逻辑是什么? 305
反杀凶徒何罪之有? 317
世间有天生犯罪人吗? 324
分歧终端机具有何种隐喻? 332
古墓派为何如此另类? 341
正义为何令人困惑? 356
后记 362
试读
反杀凶徒何罪之有?
高分古装剧《大宋提刑官》讲述了南宋著名刑官宋慈屡破疑案、惩恶扬善的传奇故事。当然,史传中宋慈的事迹记载不详,所以剧中的一系列疑案奇案都是参考宋慈的著作《洗冤集录》和其他的古代案例,再融入创作者的文学想象、艺术加工得来。正由于电视剧“非实录”的性质,因此剧中案件的不少情节存在明显的漏洞和瑕疵,若结合相关历史背景,更显出其荒诞不经,毛竹坞无名案即为一例。
恶迹斑斑的匪首王鹏侥幸逃过官府的抓捕,趁着夜色窜入毛竹坞村大善人何老二家中,欲行盗抢,却不料被何老二用一把篾刀完美反杀,结束了其卑鄙而罪恶的一生。何老二一贯本分,杀人凭的是自卫的本能和一腔血勇,移尸村外竹林后,何老二却患上了杀人后恐惧症:“我杀了人了,犯了王法了,这可怎么办?”(此处模拟何老二心理活动)
寝食难安的何老二解不开思想上的疙瘩,在散尽家财之后,打算上吊自杀,总算天不绝人,宋提刑如神兵天降,将其解救下来。此时的宋慈,虽有几分怀疑,但尚不能确定何老二就是杀人凶手,何况他需要说服的不仅是自己,还有众多村民。
于是第二天,宋提刑将村民们召集于一处,当众演示了令人拍案叫绝的办案手法—苍蝇辨刀(此方法并非凭空杜撰,而有其文献依据,有兴趣的读者可查阅《洗冤集录》),从而将何老二的“凶手”身份锁定。(宋慈对案件事实的证明、推测和还原入情入理,颇具说服力,但还没有达到现代刑事诉讼法所要求的“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这就是所谓“历史局限性”吧。)接下来,当何老二像一个溺水之人即将溺毙之际,宋提刑又抛出了他的救命绳索,并顺带宣讲了大宋律法的精义:
你是在王鹏入室行盗、本能自卫的情况下,意外将王鹏砍死的,若不是床沿挡住了刀锋,被砍死的就不是匪首王鹏,而是你善人何老二。大宋律法,惩的是恶,扬的是善。你不但杀人无罪,而且杀贼有功!
宋提刑此言一出,在场村民无不拍手称快,作为嫌疑人的何老二也是如释重负、如获新生。在这一刻,司法逻辑和民众心理实现了高度的契合。宋提刑坦言,这是他办案多年办得最痛快的一件案子,相信观众看得也一定很过瘾。
不过,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本案其实有一个很大的败笔,笔者不能不予指出。宋提刑的当众释法,依据的主要是现代刑法上正当防卫的法理,却忽略了古代社会的法律常识。实际上,何老二也好,其他关切的村民也好,根本无须宋提刑的慷慨陈词,也能确定无疑地知道何老二是否有罪,因为宋朝的法律对类似本案这种情况有白纸黑字的规定。《宋刑统·贼盗律》规定:
诸夜无故入人家者,笞四十。主人登时杀者,勿论。若知非侵犯而杀伤者,减斗杀伤二等。其已就拘执而杀伤者,各以斗杀伤论,至死者加役流。
这一条款实际上包含了对两种行为的法律定性。其一,深更半夜,无缘无故,闯入别人家中,构成轻罪(今可定名为“非法侵入住宅罪”),对应的刑罚是笞四十;其二,被闯入一方当场杀死闯入者的,不须承担刑事责任(不过有两种例外情形)。中国古人虽无“私宅神圣”的观念,但本条保护私人住宅安宁的立法用意一目了然,同时也可视为对特定时空条件下正当防卫权的具体确认。以何老二反杀王鹏案的情形来看,完全符合《宋刑统》“夜无故入人家”条的规定,何老二于法自然是应当“勿论”的。
有人可能会说,法律虽是明文,但是何老二等人均为乡野草民,对大宋律法知之甚少,不清楚其行为的性质也在情理之中。这说法貌似有理,实则不然。须知,宋律中的“夜无故入人家”条远绍秦汉旧律,近承隋唐新统,后来又为元明清诸代法律所因袭,是中国古代知名度非常高的法律条款和法律制度之一,说其家喻户晓恐怕也不为过。
北宋的华镇,一位学者型官员,曾在一篇讨论复仇的文章中提到“夜无故入人家”律,并阐明了自己的理解:
若律曰:“夜无故入人家,主人登时杀者,勿论。”是杀人者,法不必皆死也。夫夜无故入人家者,未必皆侵害于人;主人可以登时杀之者,有侵害于人之理也。有侵害于人之理者,杀之无罪。(《云溪居士集》卷二〇)
另外一个宋朝官员叫张湍(一作张端)的,曾任河南府司录。府里为了祭祀典礼专门买了一只猪,谁料中途猪挣脱控制,窜入张湍家中,张湍毫不含糊,三下五除二就把猪宰杀了。知府管张湍要猪,张湍答道:“律云:‘猪无故夜入人家,主人登时杀之,勿论。’”事情的结局是“尹大笑,为别市猪”。(《宋稗类钞》卷六)故事里,张湍借谐音抖了个机灵,当然,这一定是建立在对“夜无故入人家”律熟稔无比的基础上的。
宋代法治文明的发达不仅体现在少数封建士大夫和政府官员的法律素养上,更体现在社会一般民众的法律素养上。北宋前期知袁州(巧的是,历史上的宋慈曾任江西提点刑狱,袁州正属其管辖,而该地多竹,如毛竹坞村那般的山村
前言/序言
导?言
除了存在于人类共同的想象之外,这个宇宙中根本没有神、没有国家、没有钱、没有人权、没有法律,也没有正义。
——《人类简史》
法律与文学研究属于法理学的一个分支,在法理学研究的大家庭中,法律与文学研究即便算不上一枝独秀,至少也是独树一帜、楚楚动人了。
法律与文学研究的繁荣兴盛来自于作为异质学科的法学和文学的交互滋养和彼此启发,反映出法律与文学之间天然的紧密联系。
一方面,文学是法律得以表达自身的基本工具。现实世界中,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都离不开文学的加持。最能说明这一事实的证据是,举凡伟大的法典无不代表着当时文学的最高水准,所以司汤达在小说创作过程中,才要每天读上几页《法国民法典》,以寻找语言的灵感。而曾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卡多佐也坦承:“在司法判决的荒野上,文学风格不仅不是一种罪恶,只要运用得当,它甚至具有积极的益处。”
另一方面,法律(尤其是司法)是文学叙事的重要对象。文学以揭示人性、映射现实为使命,而法律不仅是现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约束人性的重要制度性力量。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古往今来那些伟大的诗人、剧作家、小说家都如此地偏爱法律题材。不少经典的文学作品触及法律命题,或者本身就是纯粹的法律故事,例证不胜枚举,西方的有《安提戈涅》、《威尼斯商人》、《悲惨世界》(又名《法律的命运》)、《审判》等戏剧小说,中国的则以流行于明清之际的一系列公案文学如《包公案》《施公案》《狄公案》为代表。
法律与文学研究将文学的视角引入法理学的思考,从文学作品中汲取营养,以感性调和理性,从而拓宽了法理学研究的视野,也丰富了法理学研究的内容。罗宾·维斯特曾提示我们:“文学包含有关法律的真相,而这种真相并不易于在非叙事的法理学中被发现。”到了冯象笔下,这层意思揭示得更为显豁:“要弄懂中国老底子的政法手段,光读《唐律疏议》《资治通鉴》《名公书判清明集》是不够的,搞不好还被蒙了;不如听那门子讲一遍‘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的‘护官符’来得切中肯綮,纲举目张。”
诚如冯象所言,想要对中国传统法制和古典法理有更真切的了解,学者实在有必要好好读一读《红楼梦》《水浒传》《儒林外史》《金瓶梅》等古典文学名著。在这些久负盛名的现实主义作品中,读者不仅可以发现大量鲜活的古代法制史料,其中有不少甚至可以补典籍记载之不足,而且可以具象化地走近古人的法律世界,体会古人的法律情感和法治理想。
能够为法律教学和法学研究提供营养的其实不限于现实主义文学作品,《西游记》《聊斋志异》《封神榜》《镜花缘》何尝没有价值?有读者就从《西游记》的字里行间读出了猪八戒的法律意识和权利观念,而描写唐僧身世的一节文字《陈光蕊赴任逢灾 江流僧复仇报本》则反映出中国古代为亲复仇传统的强大,再看唐僧师徒投身艰苦卓绝的取经事业以赎前衍的故事逻辑,其“将功折罪”的法律寓意再明显不过。至于《聊斋志异》,其中描写司法或法律的篇章真正不少,如《席方平》《胭脂》《太原狱》《诗谳》《考城隍》皆是,其间既有对政治黑暗、司法腐败的揭露和鞭挞,也借由幽冥审判和因果报应表达了作者对公道正义的向往和呼唤。
再把眼界拓宽,除了小说这种文学体裁,戏曲、杂文、诗词歌赋乃至民间文学,无不可以成为法学研究取资利用的素材。清人赵翼有《题白香山集后》诗云:“风流太守爱魂消,到处春游有翠翘。想见当时疏禁网,尚无官吏宿娼条。”提示我们,白居易的诗作是考证中国古代官吏宿娼禁令制度的绝佳证据,而后来学者以文证史的研究路数或者正取资于此。
读诗的这层好处折射出文学作品的法律教益价值。借由那些优秀的文学作品的帮助,读者不仅可以把握法律的当下,而且得以窥探法律的前身,甚至能够预见法律的未来。科幻文学的法律预测功能最为突出,不少优秀的科幻小说不乏对未来人类社会法治状况的设想。如《三体》中“青铜时代”号审判记录显示,为当代人所珍视的无罪推定原则在危机纪元被部分推翻了。日本科幻小说《百年法》则大胆地设想了人类实现“永生”后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引导读者思考代际义务的正义性以及“由法律来规定人何时死亡”的正当性问题。
将文学资源引入法律教学和法学研究不仅有理论上的必要,而且从一开始就充满了乐趣。喜欢听故事、讲故事似乎是人类的天性,文学作品(包括影视作品)总是可以轻松地调动人们的情绪,乃至触及人们的灵魂深处。经验告诉我们,大多数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形成可能都要归因于童年时代童话故事的熏陶。
若是按照《人类简史》的作者尤瓦尔·赫拉利的说法,故事的发明或讲故事的能力的形成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正是通过讲故事,人类建立起共同的想象,从而可以实现复杂的社会分工和协作。在这个意义上,几乎全套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