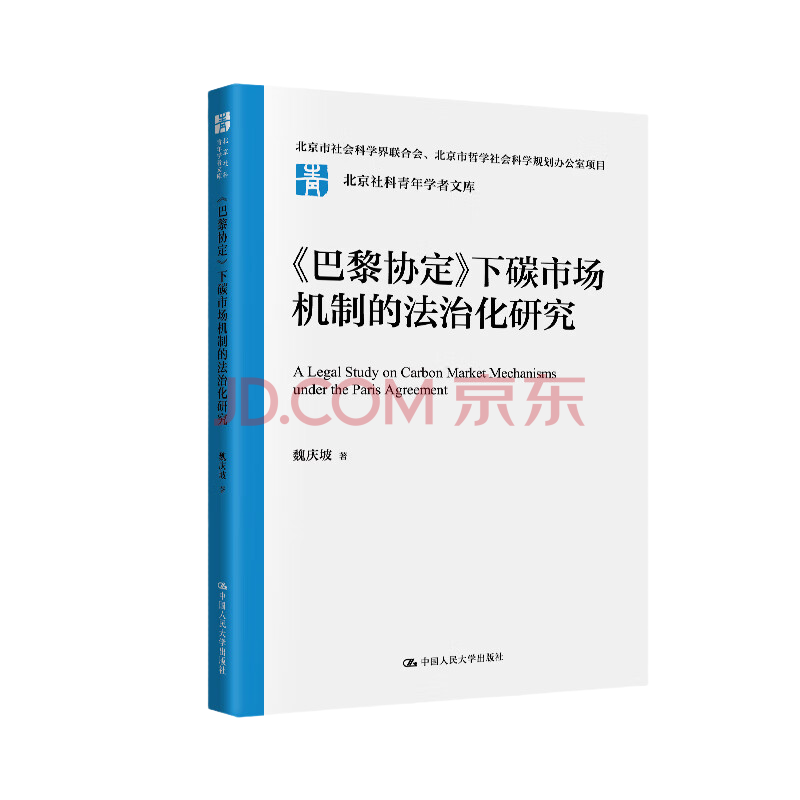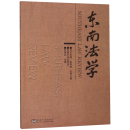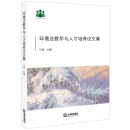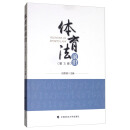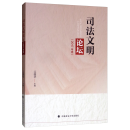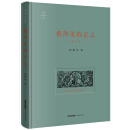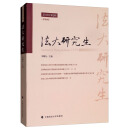内容简介
在《巴黎协定》“自下而上”减排模式框架下,第6条碳市场机制的构建和运行面临着诸多挑战。本研究强调法治在推进碳市场机制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首先系统回顾碳市场机制国际法缘起与演进,对《巴黎协定》第6条的法律规范进行分析,归纳总结法律困境。接着,基于产权理论和碳交易市场实践,重点探讨碳市场机制在交易标的法律属性、缔约国授权机制的法律构造和WTO视域下交易规则的适法性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破解之道。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双碳”目标和减排实际,提出国内碳排放权属性界定、批准和授权制度构建以及利用多边主义应对碳市场机制下单边主义举措等方面建议,为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提供法治保障。
目录
第一章 绪言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二、研究现状
三、研究方法与主要内容
四、研究创新与研究不足
第二章 碳市场机制国际法的缘起、演进与面临的挑战
一、《公约》为碳市场机制肇启奠定基础
二、《京都议定书》引入碳市场机制
三、《巴黎协定》开启碳市场机制新模式
四、《巴黎协定》碳市场机制面临的法律挑战
第三章 《巴黎协定》下碳市场机制的理论因应
一、碳市场机制及其法律监管
二、自由主义国际法下碳市场机制
三、跨国法律秩序理论
第四章 碳市场机制镜鉴与法律制度分析
一、《京都议定书》下碳市场机制
二、国家层面第6条碳市场机制实践
三、欧盟排放交易体系实践分析
第五章 碳市场机制交易标的法律属性分析
一、碳排放权的功能与权利属性
二、碳排放权益保护:一个纯粹的配额问题
三、碳排放权益的法律形态:有限的配额自我控制
四、从概念主义到工具主义的法律路径
第六章 碳市场交易授权机制的法律构造
一、第6条下授权机制的法律规范及挑战
二、东道国授权机制的法律基础
三、第6条下授权机制的法律分析
四、授权机制的完善路径
第七章 国际贸易法视域下碳市场交易规则分析
一、第6条下ITMOs交易规则分析
二、ITMOs交易适用WTO规则分析
三、欧盟CBAM在WTO框架下的法律分析
第八章 《巴黎协定》碳市场机制下的中国法律因应
一、《巴黎协定》碳市场机制给中国带来的主要法律挑战
二、碳排放权法律属性反思与制度完善
三、健全完善国内授权法律安排
四、碳市场机制交易规则层面的法律因应
……
第九章 结论
参考文献
附录:《巴黎协定》
试读
《<巴黎协定>下碳市场机制的法治化研究(北京社科青年学者文库)》:
2.对体系合作缺位的反思完善
自由主义国际法学强调对国际法的“自下而上”解释,即关注国家偏好在全球化和跨国相互依存下对国际社会关系变化的影响,这种方法聚焦于单位层次的合作,拓展了国际法研究的方法论,但也存在一些弊端。首先,导致研究者忽视行为的背景问题。虽然关注国家内部因素对国际法的影响很重要,但过于聚焦于单位层次的合作可能会忽视国际法形成和实践中其他因素的影响,如国际制度、权力关系、国际经济和地缘政治因素等②。其次,在实践中,国家参与国际合作确实是一种“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不仅需要与其他国家进行谈判和协商,还需要与国内的各种利益相关者和政治行为者进行协调和讨价还价,这意味着国际合作不仅受到国际因素的影响,还受到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因素可能比国际因素更加复杂和多样化。因此,尽管自由主义国际法学的“自下而上”解释提供了一种重要的视角,但在研究国际法和国际合作时,仍需要综合考虑单位层次和系统层次的因素,以及国内和国际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以更全面、准确地理解国际法的形成和实践。
本质上,国际法律制度的建立旨在规范和约束当前国际社会的行为和互动,在塑造国际关系、应对不确定性和降低交易成本方面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制定法律、条约和准则为国际社会建立一种共同的框架,以规范国家之间的行为和相互关系。这些规则和准则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于合理行为的共识,并提供了一种共同的框架和机制,有助于促进合作、解决争端,并提高国际关系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在分析或评估国际法律制度的过程中,需要考虑到多个因素,而不仅仅是国家间政治的层面①。第一,需要考虑社会群体当前和未来的需求,包括了解不同社会群体的需求方向、强度、风险和不确定性等因素,这些需求会影响到国家对国际法的态度和行为,因此在制定和评估国际法律制度时,需要充分考虑这些因素。第二,充分了解代表性机构性质的信息,包括了解这些机构如何代表和反映社会群体的需求和利益,以及它们在制定和执行国际法律制度方面的作用和影响,这些机构的性质将直接影响到国际法律制度的设计和遵约性。第三,注重在未来改变和引导社会偏好,这意味着国际法律制度的设计应该能够适应未来社会群体的需求变化,并且能够引导这些偏好朝着符合决策者的偏好方向发展。
在国际法律协议的制定中,特别是在设计遵约机制时,必须考虑到未来偏好的变化,并在体制设计中保持刚性和灵活性的平衡,因为过度刚性可能导致制度无法适应变化,而过度灵活性可能导致滥用。在此过程中,需要关注当前的不确定性水平和对未来外部冲击的担忧②,因为这些因素可能影响国家对机制的偏好。社会偏好模式的变化被认为是定义国家间互动形式的关键因素,并对制度形式产生影响。同时,体制设计需要综合考虑刚性、灵活性、不确定性、外部冲击和社会偏好变化等因素③,以建立更具适应性和有效性的国际法律体系。在考虑未来外部冲击的担忧和社会偏好的变化时,需要特别关注如何处理潜在的争议,以及如何吸引各国继续参与体系,以确保其持续性和吸引力。
基于对个体的重视和尊重,《巴黎协定》第6条第2款赋予了缔约方在履行国家自主贡献方面的自主性,允许它们自愿参与“合作方法”。该方法允许缔约方进口在另一个国家领土上产生的减缓成果,并将这些国际转让的减缓成果用于自身的减排履约目的。然而这种自主性的增加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破坏了合作的体系性①,并可能对全球减排目标的实现产生负面影响,因为国家更倾向于追求自身独立的减排目标或“搭便车”,而不是通过国际合作共同努力。同时,如果缺乏必要的保障措施,“合作方法”的使用可能会破坏而不是加强整体减缓努力②。理论和经验都强调了治理框架的重要性,只有确保环境政策的市场工具发挥应有的作用,才能维护市场参与者和利益相关者的权利,确保市场透明度并防止滥用行为,从而实现气候治理目标。
……
前言/序言
为了弥合缔约方自主减排目标与全球实际减排目标之间的差距,考虑到联合国主导机制的官僚化和僵硬化,尤其无法承认各个缔约方的需求,《巴黎协定》开启了“自下而上+国家自主贡献”的国际气候治理模式,并在第2条明确提出将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2℃以内的目标,这需要国际社会集体行动。后巴黎时代全球气候治理开始转向“国内驱动型”模式,呈现出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博弈、经济发展与减排降碳碰撞、去中心化与中心化并驱的严峻态势。中国作为《巴黎协定》缔约方积极提高国家自主贡献(NDCs)力度,并提出2030年“碳达峰”与2060年“碳中和”目标(“双碳”目标),这不仅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而且是负责任大国应尽的国际义务,同时也有利于中国有效应对国际气候谈判的种种挑战,进一步提升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为帮助缔约方实现国家自主贡献,《巴黎协定》第6条依据“自愿”原则构建了新的市场合作机制,旨在帮助缔约方以更灵活的合作方式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激励缔约方提升减排雄心,进而实现全球总体减排。其中第6条第2款规定了“合作方法”(cooperative approaches)框架,旨在为缔约方之间关于国际转让的减缓成果(ITMOs)提供框架机制。第6条第4款碳信用机制(也被称为“6.4机制”或“可持续发展机制”)与清洁发展机制(CDM)具有许多共同特征,在《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决议的指导和授权下开展,并受到监督机构的管理。参与者提议的减缓活动必须得到东道国的批准,并由指定经营实体(DOE)进行验证,随后将批准的可交易的碳信用发放至实施者的账户。
过去20多年,碳市场在促进国际减排合作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例如,根据《京都议定书》第12条创建的CDM,自2001年以来,已有8000多个CDM项目和计划在111个发展中国家注册,减少了2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温室气体排放,并带动了3000多亿美元的气候和可持续发展项目投资。我国作为CDM项目最大供应国,截至2016年8月已经批准CDM项目5000余个,已经获得CDM执行理事注册的项目近4000个。积极参与CDM为中国带来减排的资金和技术,有效推动了中国绿色低碳发展转型。
国际排放贸易协会(IETA) 2019年经过评估认为,以市场形式进行跨国减排合作可以在2030年之前将实现国家自主贡献的成本降低一半,即在无须增加额外费用的情形下削减50%的温室气体排放。《巴黎协定》消除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静态区别,要求所有缔约方都要根据各自国情和能力制定国家自主贡献目标,这与《京都议定书》“二分法”形成了鲜明对比。未来,随着所有缔约方都按照《巴黎协定》要求制定和实现国家自主贡献,这将使碳市场主体范围更为广泛和多样化。为确保环境完整性,明确禁止重复计算减缓成果,即如果转让的减缓成果用于实现另一国的国家自主贡献,则该减缓成果不得用于转让国的减排承诺,为此,对两国的任何减缓成果转移都要求进行相应调整。可见,基于产权制度设计的碳市场机制牵涉因素错综复杂,缔约方之间为了自身目标和利益,在具体方案选择上存在较大分歧,如果设计和实施不当,国际碳市场机制不仅会增加减缓气候变化的成本,而且可能导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
2021年11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26次缔约方会议(COP26)在英国格拉斯哥闭幕,在经历了一天的加时谈判后,近200个缔约方通过了《格拉斯哥气候公约》,最终敲定了《巴黎协定》第6条的实施规则。至此,这一本应在2018年波兰卡托维兹完成的事项在延期三年后最终落定。COP26就实施第6条碳市场机制的框架达成一致,其中包括关于第6条第2款“合作方法”的指南以及第6条第4款碳信用机制的规则、模式和程序(RMP)。但是,这种概念和程序上的界定并未限定参与方对第6条碳市场机制的实施方式,亦未明确合作的具体条件和标准。因此,第6条碳市场机制实质上并未构建市场机制本身,而仅仅是为缔约方提供了由其自身决定与哪一方跨境转让减缓成果的一个宽泛合作程序框架。
考虑到缔约方在《巴黎协定》下作出自主减排承诺,以及半数缔约方在自主贡献中支持建立国际碳市场,未来会有更多国家参与第6条的减排合作。比如瑞士已同多个国家缔结了双边协定以推进减排合作,并与合作伙伴确定了认可ITMOs的要求,为合作双方建立了法律框架。这种法律框架具有明显的单边性限制属性,尤其在标准不清晰的情况下可能具有明显的歧视性,势必会引发一些争议,进而可能与《巴黎协定》第6条“合作”的初衷相悖。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全球气候治理以联合国为主导,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形成了《公约》、《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等国际条约,这些重要阶段性成果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其中,1992年《公约》开启了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制度化轨道,明确提出了风险预防原则、“共区原则”和可持续发展原则等国际气候合作的基本原则。1997年《京都议定书》进一步将“共区原则”推进到落实层面,以“自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