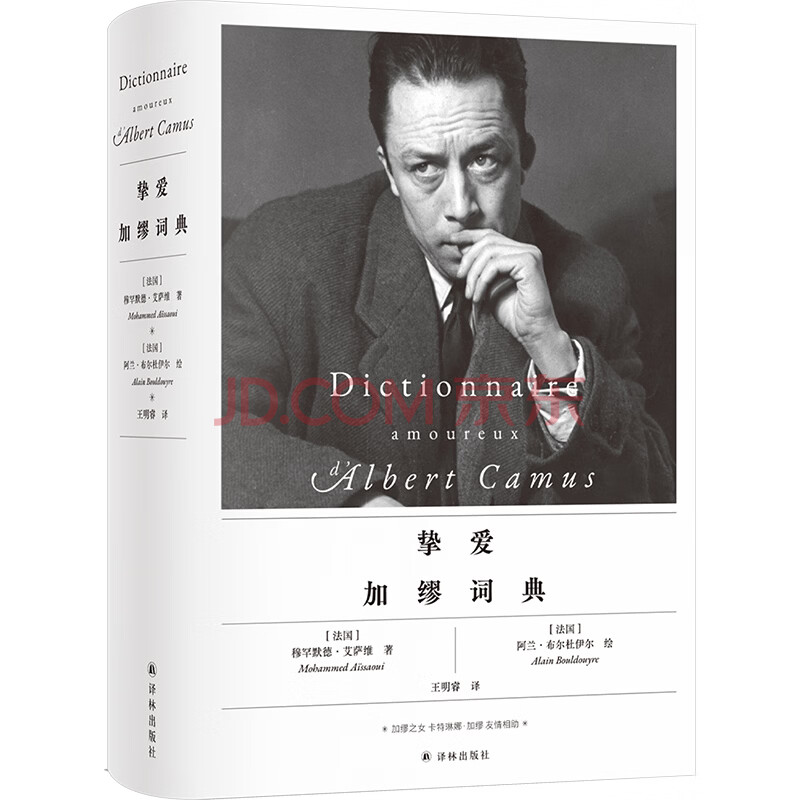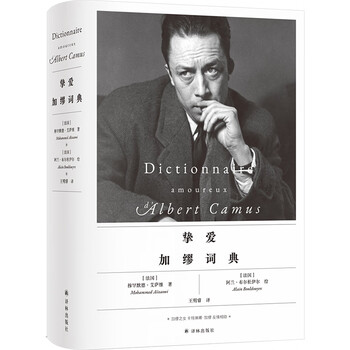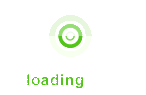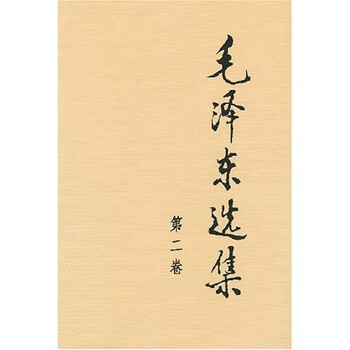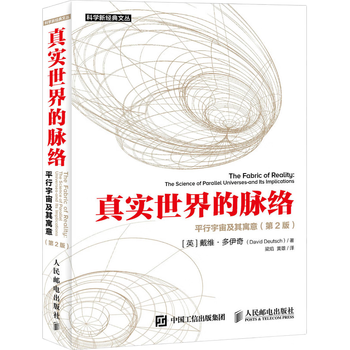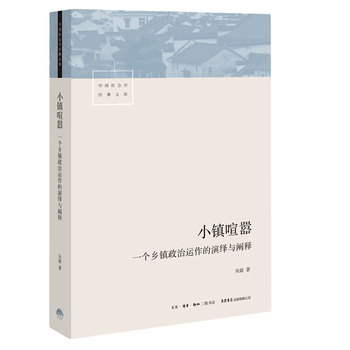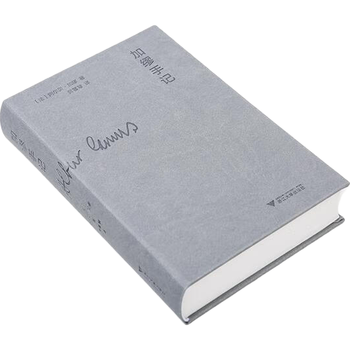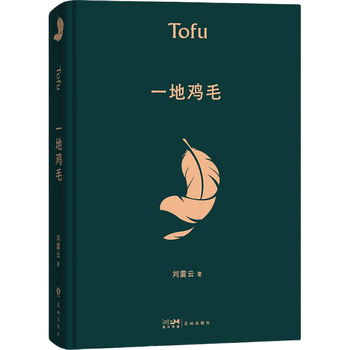内容简介
与加缪同样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作家、记者穆罕默德·艾萨维,在加缪女儿卡特琳娜的协助下,与我们分享这位他深爱的作家生命中珍贵的片段:
18岁的加缪最心仪的同时代作家是谁?
与加缪展开激烈论战的对手,向他掷去了怎样锋利的箭矢?
在加缪长眠的墓园里,是哪些花儿在静静绽放?
为了守护父亲留下的文学遗产,卡特琳娜·加缪放弃了怎样一段属于自己的职业生涯?
为什么说《阿尔贝·加缪与玛丽亚·卡萨雷斯通信集(1944—1959)》的编辑完成了“修女般的工作”?
加缪在伽利玛出版社主持的“希望”丛书收录了哪些作品?
目录
前言Avant-propos
A
阿卜杜勒·麦利克Abd Al Malik
荒诞,荒诞性Absurde, absurdité
古斯塔夫·阿库:屠夫姨夫Acault, Gustave:l’oncle boucher
阿尔及尔,《阿尔及尔的夏天》Alger, L’Été à Alger
《阿尔及尔共和报》(反对加缪的会议纪要)Alger républicain(procès-verbal contre Camus)
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利亚人Algérie, Algérien
友情Amitié
爱情Amour
“加缪去死吧!”« À mort Camus ! »
无名年鉴Anonymes, Chroniques
阿拉伯人,“那个阿拉伯人”Arabe ou « l’Arabe »
艺术家,《约拿或工作中的艺术家》Artiste,Jonas ou l’artiste au travail
B
美Beauté
贝尔库Belcourt
乔治—马克·本纳穆Benamou, Georges-Marc
路易·贝尼斯蒂Bénisti, Louis
埃马纽埃尔·贝尔Berl, Emmanuel
幸福Bonheur
奖学金Bourse d’études
C
咖啡馆Cafés
《卡利古拉》Caligula
卡特琳娜·加缪Camus, Catherine
吕西安·奥古斯特·加缪Camus, Lucien Auguste
玛丽·卡多娜(《局外人》人物)Cardona, Marie (dans L’Étranger )
《笔记》,过程中的作品Carnets (ou Cahiers),l’oeuvre en formation
《医院风波》Cas intéressant, Un
玛丽亚·卡萨雷斯Casarès, Maria
歌曲(歌手加缪!)Chanson (Camus chanteur!)
勒内·夏尔Char, René
魅力Charisme
埃德蒙·夏尔洛Charlot, Edmond
尼古拉·奇洛蒙蒂Chiaromonte, Nicola
《堕落》Chute, La
引文制造机加缪Citations, Camus, homme de
让—巴蒂斯特·克拉芒斯(《堕落》人物)Clamence, Jean-Baptiste(dans La Chute)
《战斗报》Combat
阿尔贝·柯赛里Cossery, Albert
D
让·达尼埃尔Daniel, Jean
卡迈勒·达乌德Daoud, Kamel
荒漠Désert
《荒漠》Désert, Le
《抓住欲望的尾巴》Désir attrapé par la queue, Le
堂吉诃德Don Quichotte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ïevski, Fiodor
痛苦Douleur
《痛苦》Douleur, La
大仲马Dumas, Alexandre
E
学校Écoles
作家职业Écrivain, Le métier d’
出版人Éditeur
阿尔及利亚的孩子们Enfants d’Algérie
拉斐尔·昂多凡Enthoven, Raphaël
“在母亲和正义之间……”« Entre ma mère et la justice… »
《反与正》Envers et l’Endroit, L’
团队,集体,组织Équipe, collectif, groupe
西班牙Espagne
“希望”« Espoir »
《戒严》État de siège, L’
夏天Été
《夏天集》Été, L’
《局外人》Étranger, L’
局外,一种存在感受Étranger, Sentiment d’être
题铭,题词Exergue, épigraphe
《流放与王国》Exil et le Royaume, L’
……
附录Annexes
加缪大事记Quelques repères biographiques
加缪代表作简介Quelques mots sur les principaux textes de Camus
部分参考文献Bibliographie sélective
阿尔贝·加缪通信集La correspondance d’Albert Camus
关于阿尔贝·加缪的专著Les livres sur Albert Camus
关于加缪的短篇小说一则Une nouvelle sur Camus
试读
阿卜杜勒·麦利克
Abd Al Malik
我想在这部词典的开篇向所有喜爱加缪的人致以问候,而我们人数众多。在我们当中,有一些和我一样已经发现了《局外人》的作者;我们拥有在一座城市度过的同样童年,由一个尽职尽责的母亲抚养,她竭尽所能地照料着一个大家庭,始终想把价值观传给后代。无论怎样,她始终都挺直了腰板。
阿卜杜勒·麦利克在一本书中表达了自己对这位阿尔及利亚作家的喜爱,他将其视为自己的兄弟、自己的英雄。在《加缪:反抗的艺术》中,他写道:“我在《局外人》的书页里遇见了阿尔贝·加缪。这是一场文学的相遇,是将我塑造成艺术家、音乐家和作家的相遇之一,是决定了我创作之路的相遇之一。我相信,我不是唯一一个感觉到这层关系的人:来自各个阶层的所有法国人,无论是否依然年轻,只要相信文化和教育依然是用来对抗社会决定新形式的主要武器,就都会感到这层关系。”
我有幸见过阿卜杜勒·麦利克,甚至和他共同完成了一项计划。我见过他在艾克斯—普罗旺斯登台饰演加缪,我在巴黎看过他对《正义者》的改编;我在卢尔马兰见过他,在一些会议上也见过,那些会议讨论的是我们忙了两年的计划,我们打算拍摄一部关于福尔西这位人物的电影,这个奴隶抗争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为的是让司法机构承认自己自由人的身份。我发现阿卜杜勒·麦利克是个少有的人、少有的艺术家,他信念坚定,心胸开阔。我们经常有机会交流对加缪的看法。我们两个都是从初中时期开始接触加缪的。感谢学校。他跟我讲了他第一次阅读加缪时感受到的震撼。“我在学校里读了《局外人》,感到一种冲击,而这种冲击始终在发出回响。后来发生了其他事。我也如愿读了加缪年轻时写的第一部随笔集《反与正》,深受震撼。从这本年轻时期的作品算起,他在20 年后写下一篇序言证明了自己的艺术家地位,但实际上,他说的最多的是他自己的源头:他说人应该回到本质上的东西。这本书加深了我对加缪的理解。”
在和阿卜杜勒·麦利克交流的过程中,我特别发现我们对加缪的感情都像是兄弟——一个精神上的兄弟,但不仅如此。他的经历、他的家庭、由单亲母亲抚养、在“文化”一词意味着浪费时间的环境里成长,还有将我们拯救的学校……所有这些,我们都在骨子里明白它们意味着什么。这拉近了我们的距离,像一个微笑。
加缪将阿卜杜勒·麦利克拉出了莫大的困境,后来他成了我们熟悉的艺术家,而他小时候生活在做大麻生意的纽霍夫城。我们知道这种“生意”会把人带到哪里:直接送进牢房,之后就再也出不来了。通过阅读加缪,这个年轻人不再贩卖这种会毁了别人、毁了自己的毒品。“对,真的,这不是神话。我们不能通过犯下其他不公来抵抗不公,这是加缪告诉我的主要内容,我深受触动。所以,我不能再对别人不公,也不能再对自己不公。这是这本书轻声告诉我的。要竭尽所能地投身到作为一个人的事业当中。也就是说,即便世界是荒诞的,即便最终这一切都没有意义,我们依然要竭尽所能地投身到生而为人的事业当中。阅读《反与正》的时候,我就是在为自己重建一条脊柱。”
后来阿卜杜勒·麦利克说了一句感人的话:“加缪对我来说是一位导师,是一个帮助你挺直腰杆的人……”今天,这位艺术家成了杰出的加缪代言人——甚至是他的旗帜。我很少听到有人评价加缪时能说得这么好。麦利克在戏剧中扮演他,特别是出演了《正义者》,不过在所有演出中都让人想起加缪。他排演了一出关于《反与正》的戏,所到之处吸引着年轻人纷纷前来观看。而这场巡演持续了整整五年。
前言/序言
前言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觉得自己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认识加缪、了解加缪的人,觉得他只是在为我书写:他是我的父亲、我的兄长、我的老师、我的朋友。他安慰我无须为世事烦忧,给我带来欢乐,他遭遇不幸的时候我悲痛万分。因为有了他,我从未觉得孤独。我比任何人都要了解他,觉得其他人无法真正了解他,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我和他的生活……贫穷、有个永远不会给你读书的文盲母亲、趾高气昂的目光,这种陌异的感觉无处不在,我们在出身环境和日后“进入”的环境之间无所适从——社会差异令人眩晕。也是在两个国家、两个世界之间痛苦得无所适从:在法国和阿尔及利亚之间。我觉得加缪拿起笔是为了告诉我:“看啊,你不是一个人。”在我家里,处处都摆着他的书、放着他的书,好像它们在保护我—防止什么?我不是很清楚。我只是需要他时时刻刻在我身边。我的书橱里有他同一本小说的若干版本,也有同一个版本的若干册。而且我的包里永远都有一本加缪的书。
后来,我明白了加缪不属于我——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不是只属于我!喜欢他的人上千、上百万。如果某个人喜欢加缪,那么我也会喜欢他:我们是一家人。我发现这个家庭人口众多。所以我学会了分享。而且现在支持者众多,这是好事,我很开心。虽然他并不知道,但自从读了《局外人》而发现他的那天起——当时我并不理解,却很是震撼—直到今天,他一直都是个能给我启迪的伙伴。在我看来,他是一个开启心智的人,是一个永远的朋友,总是对我轻声念叨着“希望”,至少我愿意相信他,当然我也了解他阴郁的一面、他的孤独,还有他深深的失望。他发表的第一部作品(《反与正》)中有一句话已经说出了一切,或者是几乎一切:“如果对生活不曾失望,就不会热爱生活。”我不是研究他作品的专家,而我钦佩那些耗费多年生命去研究加缪、解读加缪的人。加缪让我想起了自己曾经的孩童模样,而这个孩子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是贫穷的;这位作家用自己的词语和回响不绝的优美精准文字帮助了这个孩子,而在今天,这些文字或许回响得更为强烈。在这部“挚爱词典”里,我只是想表达自己作为读者的仰慕之情。我以前觉得自己非常了解这位心爱的作家,可还是会发现一些亮点、闪光和快乐,发现一颗为了一个句子而激动不已的心。当然有《局外人》《鼠疫》《误会》《堕落》《卡利古拉》;还有《笔记》和众多信件的片段;也有合在一起的“小”文章,它们散落在《婚礼集》《夏天集》《流放与王国》《反与正》中,最后这本是一个得了肺结核的22 岁年轻人创作的第一本书……我不是在向专家们传授任何东西,而是面向不了解这部文集的人,或者很久以前读过这部文集的人:请拿起这本年轻人写的书,它在阿尔及利亚由书籍出版销售商埃德蒙·夏尔洛出版,印刷了几百册,打开它吧。比如,可以读读《是与否之间》这个标题有趣的短篇小说,这也许是加缪最具自传性质的文本,回忆了他在贝尔库度过的童年、他的母亲、寂静、贫穷,还有死于战争的父亲,那时他才11 个月……但是从来都不悲伤。从来都不。《笔记》的第一句话便是:“我想说:愿我们能够不带浪漫色彩地怀念一种已经失去的贫穷。”后文中又说:“于是,每当我似乎感到了世界的深意,让我为之震撼的都是它的‘仅此而已’。”那么,这个文集中的最后一则短篇小说又怎么样呢?整个文集就是以它命名的——《反与正》:短短七页,内容却很是丰富,像一首特别的交响曲,讲述了一个老妇人的故事,她继承了一小笔钱财后给自己买了座墓穴,每天都要去看一看。七页!怎么能够只用七页就如此准确而强烈地呈现出人与世界?
可以大胆地说:他虽然没有生在优越的文学环境中,却具有文学天赋。的确,每个人对文学都有自己的定义,而即便在一定程度上都会牵涉诺贝尔奖,这些定义也很少有重合的地方,但是必须承认,在简单的表象后面,在作为强烈风格标志的流畅文笔后面,是出类拔萃的才华。从一开始,作者就给自己规定了一条行为准则,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两条。第一条:“人们只会通过图像来思考。如果想成为哲学家,那就写小说吧”(《笔记I》,1936 年1 月,他当时22 岁)。第二条:根据实实在在、真真切切的世界来改编神话—这就是《鼠疫》的计划,它模仿了《白鲸》,从中获得灵感,因为这位伟大的作家博览群书,读过麦尔维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福克纳、普鲁斯特……他借鉴了最杰出的作家,有时会把他们的作品改编成戏剧。
所有喜欢加缪的人都知道这个该死的日子:1960年1月4日。我查过了,那是个星期一。那天,在约讷的一条公路上,一辆汽车撞上了一棵树,在一个叫作“小维勒布勒万”的地方,离桑斯不远。当时是下午一点五十五分,这是停在汽车仪表盘上的时间。在这辆法赛维嘉里,有米歇尔·伽利玛、他的妻子和继女,还有当场死亡的阿尔贝·加缪——出版商米歇尔·伽利玛伤势过重,几天后也去世了。当时加缪才46岁。现在的我比他老多了。
从1960 年到2023 年,他去世已经63 年,但我明白他一直活着。很少有作家在身后依然拥有如此绚丽而丰盈的生命。他在继续和我们对话,我们当中有老人也有最年幼的人。一个被阅读的作者、一个经常被引用的作者是不会死的——天知道人们有多喜欢引用加缪。看到人们比以往还要喜欢阅读他,我很开心。他的作品始终销量可观。我曾在自己供职的报纸上做了一个调查,看看人们最喜欢哪些经典作品,结果加缪位列第四,紧跟莫泊桑、莫里哀和左拉!而在这个只有20 本书的排名中,他就占有3 部(《鼠疫》《局外人》《第一个人》)。他的名字受众多学校钟爱,被刻在了门楣上。
然而,加缪去世后,人们对他的评价远远算不上友好。让—保罗·萨特主宰着当时的思想界。大学教授们看不起《反抗者》作者的作品,鄙视他。人们认为他只不过是一个“出现在高考试卷上的哲学家”,这是萨特的枪架子、记者让—雅克·伯劳希耶于1970 年在一篇抨击文章中的公开评价……竟然侮辱死者,可真是胆大!但是对于他的女儿卡特琳娜·加缪来说,“出现在高考试卷上的哲学家”更是一种赞扬;而伯劳希耶用来侮辱加缪的这句话只是在评价他自己。
20世纪90年代,形势扭转了。首先是他的作品一如既往地受读者欢迎——不仅仅是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指路灯般的《鼠疫》——每一部都大量陈列在书店里。人们阅读他笔触光彩夺目的杰出文字,去发现他或者重新发现他。因为以前,人们提起这个人时,并没有充分讨论他的写作,而这种风格能够历经岁月而不衰,每天都令他的作品更有力量。雅克·费朗代的绘画改编借鉴了阿尔及利亚的气味和颜色。在卡特琳娜·加缪的推动下,未竟之作《第一个人》于1994 年出版,这在当时是一件大事,更是一个真正的转折点,可有些人还批评这部遗著,其手稿是在那辆法赛维嘉的后备箱发现的。只要读一读这段家庭往事,加缪的人道主义精神就会跃入眼帘。
一个看待《反抗者》作者的新眼光出现了,它和柏林墙的倒塌、极权思想的垮台一样是确凿的事实。他的敏锐、克制和对表现细微之处的勇气(终于)得到了认可。对比之下,他盲目自大的对手们变得让人难以忍受,也就是萨特、梅洛—庞蒂、让松之流。
今天,我们在阅读或者观看《正义者》的任何一个版本时都会想到当代恐怖主义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四开经典”丛书中有一卷别出心裁地收录了加缪的17 部作品。关于与这位作家相伴时感受如何,拉斐尔·昂多凡说得很清楚:“对于寻找生命意义的人,加缪回答说我们并不是来自笼罩我们的天空。对于因荒诞而忧伤的人,加缪说世界是美丽的,这已足够满足一个人的内心。[……]阿尔贝·加缪让人觉得治疗失望的方式在于做事的时候不必怀着希望[……]。”这些评价和让·格勒尼耶的话异曲同工。格勒尼耶是加缪的哲学老师,后来两人成了朋友。他说加缪不仅与智力的懒惰斗争,更是与心灵的懒惰抗衡。他从未厌倦战斗,因为他从未厌倦热爱。
有件事我必须承认:在我的整个记者生涯中,最难忘的时刻是见到卡特琳娜·加缪,那是在吕贝隆地区的卢尔马兰……在阿尔贝—加缪街……我把她当成自己的姐妹,甚至是我的妹妹,虽然她比我大几岁,我总是有保护她的冲动,保护她免于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
如果没有她、没有她的帮助,我完成不了这部《挚爱加缪词典》。在此,我要感谢她的慷慨和热情——在她那里,这两种美德高于一切。这个把自己描述为父亲“小作品”的人是研究加缪最杰出的专家。
一次见面时,我问了她一个问题,正是关于《挚爱加缪词典》的。我并没有抱什么希望,问她是否想在这本书中放进什么词,一些意料之外的词,甚至是她觉得对于父亲来说不可回避的词。她回答我说:“有十个词是爸爸最喜欢的!”他笔记众多,在其中一本里写下了十个可以说是永远没有离开他的词语,列表如下。本书给它们做了特殊安排:它们会被“画出来”,还会配上一句加缪写的话,因为还有谁能比他更好地定义这些词呢?
荒漠
痛苦
夏天
人
荣誉
大海
母亲
苦难
世界
大地
最后,我想说撰写本书成了我每日莫大的幸福。这是一件幸福得令人眩晕的事,我会为此奉献一生,或者说:我们会不断地去了解身为人和身为作家的加缪,而我无法将这两种身份分开。《笔记》(这部精彩的作品记录了他的创作过程和想法)中的某个部分、《鼠疫》中的一句话、《堕落》中的一个表达方式、通信中的一封信、《婚礼集》的优雅、《战斗报》中的一课……很少有作者能给读者带来这么丰富的文字。
这部完全主观的《挚爱加缪词典》不会给出每一个众所期待的词条:我不得已做出了选择,而且,无论如何,尝试处理整个“主体”都是痴心妄想,因为它无边无际,讨论不尽。我也不会去探讨哲学方面的内容,很遗憾,我没有足够的学识去谈论或者分析让加缪着迷的哲学思想,比如尼采的主张,也没有能力去探讨为什么他摒弃了尼采的告诫——我只不过为了高考才上过哲学课。
《挚爱加缪词典》这本书是用来认可、分享和感谢的:出自一个阿尔及利亚之子的手,献给一位伟大的阿尔及利亚作家。我要感谢所有解读加缪作品的专家,他们做了大量工作,让我得以看到自己以前没有看到、没有明白的东西——我会逐一提到他们的名字,因为他们贡献卓越。读他们的成果,就是在继续发现加缪、走近加缪。我会想起那些在加缪彷徨、失望之时支持他的作家,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在各个方面为他发声(阿卜杜勒·麦利克、拉斐尔·昂多凡、卡迈勒·达乌德、弗朗西斯·乌斯特……)。我还会提及一些不是很出名的人,当然喜欢加缪的人应该对他们有所了解,我知道这些人对《婚礼集》的作者来说很重要,比如古斯塔夫·阿库,他是加缪家族里的肉店老板。我也会理所当然地提到他的小学老师路易 · 热尔曼,还有他的哲学老师让·格勒尼耶。虽然人们很少提到他的屠夫姨夫,但他热爱文学,照顾了痛苦的小阿尔贝,用红肉调养他的身体,还慷慨地向他敞开自己的大书房:加缪的志向诞生于此,这可不是件小事。
有时候,我不得不暂停一遍又一遍地挖掘每一本加缪的书、每一本涉及加缪的书。这项“工作”给我带来了激动的美好时刻;我其实可以为此再花上十年,可这依然不够。无论如何,我都会继续下去,因为我不愿意没有他的陪伴。
穆罕默德·艾萨维
前言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觉得自己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认识加缪、了解加缪的人,觉得他只是在为我书写:他是我的父亲、我的兄长、我的老师、我的朋友。他安慰我无须为世事烦忧,给我带来欢乐,他遭遇不幸的时候我悲痛万分。因为有了他,我从未觉得孤独。我比任何人都要了解他,觉得其他人无法真正了解他,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我和他的生活……贫穷、有个永远不会给你读书的文盲母亲、趾高气昂的目光,这种陌异的感觉无处不在,我们在出身环境和日后“进入”的环境之间无所适从——社会差异令人眩晕。也是在两个国家、两个世界之间痛苦得无所适从:在法国和阿尔及利亚之间。我觉得加缪拿起笔是为了告诉我:“看啊,你不是一个人。”在我家里,处处都摆着他的书、放着他的书,好像它们在保护我—防止什么?我不是很清楚。我只是需要他时时刻刻在我身边。我的书橱里有他同一本小说的若干版本,也有同一个版本的若干册。而且我的包里永远都有一本加缪的书。
后来,我明白了加缪不属于我——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不是只属于我!喜欢他的人上千、上百万。如果某个人喜欢加缪,那么我也会喜欢他:我们是一家人。我发现这个家庭人口众多。所以我学会了分享。而且现在支持者众多,这是好事,我很开心。虽然他并不知道,但自从读了《局外人》而发现他的那天起——当时我并不理解,却很是震撼—直到今天,他一直都是个能给我启迪的伙伴。在我看来,他是一个开启心智的人,是一个永远的朋友,总是对我轻声念叨着“希望”,至少我愿意相信他,当然我也了解他阴郁的一面、他的孤独,还有他深深的失望。他发表的第一部作品(《反与正》)中有一句话已经说出了一切,或者是几乎一切:“如果对生活不曾失望,就不会热爱生活。”我不是研究他作品的专家,而我钦佩那些耗费多年生命去研究加缪、解读加缪的人。加缪让我想起了自己曾经的孩童模样,而这个孩子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是贫穷的;这位作家用自己的词语和回响不绝的优美精准文字帮助了这个孩子,而在今天,这些文字或许回响得更为强烈。在这部“挚爱词典”里,我只是想表达自己作为读者的仰慕之情。我以前觉得自己非常了解这位心爱的作家,可还是会发现一些亮点、闪光和快乐,发现一颗为了一个句子而激动不已的心。当然有《局外人》《鼠疫》《误会》《堕落》《卡利古拉》;还有《笔记》和众多信件的片段;也有合在一起的“小”文章,它们散落在《婚礼集》《夏天集》《流放与王国》《反与正》中,最后这本是一个得了肺结核的22 岁年轻人创作的第一本书……我不是在向专家们传授任何东西,而是面向不了解这部文集的人,或者很久以前读过这部文集的人:请拿起这本年轻人写的书,它在阿尔及利亚由书籍出版销售商埃德蒙·夏尔洛出版,印刷了几百册,打开它吧。比如,可以读读《是与否之间》这个标题有趣的短篇小说,这也许是加缪最具自传性质的文本,回忆了他在贝尔库度过的童年、他的母亲、寂静、贫穷,还有死于战争的父亲,那时他才11 个月……但是从来都不悲伤。从来都不。《笔记》的第一句话便是:“我想说:愿我们能够不带浪漫色彩地怀念一种已经失去的贫穷。”后文中又说:“于是,每当我似乎感到了世界的深意,让我为之震撼的都是它的‘仅此而已’。”那么,这个文集中的最后一则短篇小说又怎么样呢?整个文集就是以它命名的——《反与正》:短短七页,内容却很是丰富,像一首特别的交响曲,讲述了一个老妇人的故事,她继承了一小笔钱财后给自己买了座墓穴,每天都要去看一看。七页!怎么能够只用七页就如此准确而强烈地呈现出人与世界?
可以大胆地说:他虽然没有生在优越的文学环境中,却具有文学天赋。的确,每个人对文学都有自己的定义,而即便在一定程度上都会牵涉诺贝尔奖,这些定义也很少有重合的地方,但是必须承认,在简单的表象后面,在作为强烈风格标志的流畅文笔后面,是出类拔萃的才华。从一开始,作者就给自己规定了一条行为准则,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两条。第一条:“人们只会通过图像来思考。如果想成为哲学家,那就写小说吧”(《笔记I》,1936 年1 月,他当时22 岁)。第二条:根据实实在在、真真切切的世界来改编神话—这就是《鼠疫》的计划,它模仿了《白鲸》,从中获得灵感,因为这位伟大的作家博览群书,读过麦尔维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福克纳、普鲁斯特……他借鉴了最杰出的作家,有时会把他们的作品改编成戏剧。
所有喜欢加缪的人都知道这个该死的日子:1960年1月4日。我查过了,那是个星期一。那天,在约讷的一条公路上,一辆汽车撞上了一棵树,在一个叫作“小维勒布勒万”的地方,离桑斯不远。当时是下午一点五十五分,这是停在汽车仪表盘上的时间。在这辆法赛维嘉里,有米歇尔·伽利玛、他的妻子和继女,还有当场死亡的阿尔贝·加缪——出版商米歇尔·伽利玛伤势过重,几天后也去世了。当时加缪才46岁。现在的我比他老多了。
从1960 年到2023 年,他去世已经63 年,但我明白他一直活着。很少有作家在身后依然拥有如此绚丽而丰盈的生命。他在继续和我们对话,我们当中有老人也有最年幼的人。一个被阅读的作者、一个经常被引用的作者是不会死的——天知道人们有多喜欢引用加缪。看到人们比以往还要喜欢阅读他,我很开心。他的作品始终销量可观。我曾在自己供职的报纸上做了一个调查,看看人们最喜欢哪些经典作品,结果加缪位列第四,紧跟莫泊桑、莫里哀和左拉!而在这个只有20 本书的排名中,他就占有3 部(《鼠疫》《局外人》《第一个人》)。他的名字受众多学校钟爱,被刻在了门楣上。
然而,加缪去世后,人们对他的评价远远算不上友好。让—保罗·萨特主宰着当时的思想界。大学教授们看不起《反抗者》作者的作品,鄙视他。人们认为他只不过是一个“出现在高考试卷上的哲学家”,这是萨特的枪架子、记者让—雅克·伯劳希耶于1970 年在一篇抨击文章中的公开评价……竟然侮辱死者,可真是胆大!但是对于他的女儿卡特琳娜·加缪来说,“出现在高考试卷上的哲学家”更是一种赞扬;而伯劳希耶用来侮辱加缪的这句话只是在评价他自己。
20世纪90年代,形势扭转了。首先是他的作品一如既往地受读者欢迎——不仅仅是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指路灯般的《鼠疫》——每一部都大量陈列在书店里。人们阅读他笔触光彩夺目的杰出文字,去发现他或者重新发现他。因为以前,人们提起这个人时,并没有充分讨论他的写作,而这种风格能够历经岁月而不衰,每天都令他的作品更有力量。雅克·费朗代的绘画改编借鉴了阿尔及利亚的气味和颜色。在卡特琳娜·加缪的推动下,未竟之作《第一个人》于1994 年出版,这在当时是一件大事,更是一个真正的转折点,可有些人还批评这部遗著,其手稿是在那辆法赛维嘉的后备箱发现的。只要读一读这段家庭往事,加缪的人道主义精神就会跃入眼帘。
一个看待《反抗者》作者的新眼光出现了,它和柏林墙的倒塌、极权思想的垮台一样是确凿的事实。他的敏锐、克制和对表现细微之处的勇气(终于)得到了认可。对比之下,他盲目自大的对手们变得让人难以忍受,也就是萨特、梅洛—庞蒂、让松之流。
今天,我们在阅读或者观看《正义者》的任何一个版本时都会想到当代恐怖主义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四开经典”丛书中有一卷别出心裁地收录了加缪的17 部作品。关于与这位作家相伴时感受如何,拉斐尔·昂多凡说得很清楚:“对于寻找生命意义的人,加缪回答说我们并不是来自笼罩我们的天空。对于因荒诞而忧伤的人,加缪说世界是美丽的,这已足够满足一个人的内心。[……]阿尔贝·加缪让人觉得治疗失望的方式在于做事的时候不必怀着希望[……]。”这些评价和让·格勒尼耶的话异曲同工。格勒尼耶是加缪的哲学老师,后来两人成了朋友。他说加缪不仅与智力的懒惰斗争,更是与心灵的懒惰抗衡。他从未厌倦战斗,因为他从未厌倦热爱。
有件事我必须承认:在我的整个记者生涯中,最难忘的时刻是见到卡特琳娜·加缪,那是在吕贝隆地区的卢尔马兰……在阿尔贝—加缪街……我把她当成自己的姐妹,甚至是我的妹妹,虽然她比我大几岁,我总是有保护她的冲动,保护她免于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
如果没有她、没有她的帮助,我完成不了这部《挚爱加缪词典》。在此,我要感谢她的慷慨和热情——在她那里,这两种美德高于一切。这个把自己描述为父亲“小作品”的人是研究加缪最杰出的专家。
一次见面时,我问了她一个问题,正是关于《挚爱加缪词典》的。我并没有抱什么希望,问她是否想在这本书中放进什么词,一些意料之外的词,甚至是她觉得对于父亲来说不可回避的词。她回答我说:“有十个词是爸爸最喜欢的!”他笔记众多,在其中一本里写下了十个可以说是永远没有离开他的词语,列表如下。本书给它们做了特殊安排:它们会被“画出来”,还会配上一句加缪写的话,因为还有谁能比他更好地定义这些词呢?
荒漠
痛苦
夏天
人
荣誉
大海
母亲
苦难
世界
大地
最后,我想说撰写本书成了我每日莫大的幸福。这是一件幸福得令人眩晕的事,我会为此奉献一生,或者说:我们会不断地去了解身为人和身为作家的加缪,而我无法将这两种身份分开。《笔记》(这部精彩的作品记录了他的创作过程和想法)中的某个部分、《鼠疫》中的一句话、《堕落》中的一个表达方式、通信中的一封信、《婚礼集》的优雅、《战斗报》中的一课……很少有作者能给读者带来这么丰富的文字。
这部完全主观的《挚爱加缪词典》不会给出每一个众所期待的词条:我不得已做出了选择,而且,无论如何,尝试处理整个“主体”都是痴心妄想,因为它无边无际,讨论不尽。我也不会去探讨哲学方面的内容,很遗憾,我没有足够的学识去谈论或者分析让加缪着迷的哲学思想,比如尼采的主张,也没有能力去探讨为什么他摒弃了尼采的告诫——我只不过为了高考才上过哲学课。
《挚爱加缪词典》这本书是用来认可、分享和感谢的:出自一个阿尔及利亚之子的手,献给一位伟大的阿尔及利亚作家。我要感谢所有解读加缪作品的专家,他们做了大量工作,让我得以看到自己以前没有看到、没有明白的东西——我会逐一提到他们的名字,因为他们贡献卓越。读他们的成果,就是在继续发现加缪、走近加缪。我会想起那些在加缪彷徨、失望之时支持他的作家,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在各个方面为他发声(阿卜杜勒·麦利克、拉斐尔·昂多凡、卡迈勒·达乌德、弗朗西斯·乌斯特……)。我还会提及一些不是很出名的人,当然喜欢加缪的人应该对他们有所了解,我知道这些人对《婚礼集》的作者来说很重要,比如古斯塔夫·阿库,他是加缪家族里的肉店老板。我也会理所当然地提到他的小学老师路易 · 热尔曼,还有他的哲学老师让·格勒尼耶。虽然人们很少提到他的屠夫姨夫,但他热爱文学,照顾了痛苦的小阿尔贝,用红肉调养他的身体,还慷慨地向他敞开自己的大书房:加缪的志向诞生于此,这可不是件小事。
有时候,我不得不暂停一遍又一遍地挖掘每一本加缪的书、每一本涉及加缪的书。这项“工作”给我带来了激动的美好时刻;我其实可以为此再花上十年,可这依然不够。无论如何,我都会继续下去,因为我不愿意没有他的陪伴。
穆罕默德·艾萨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