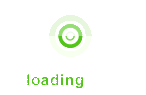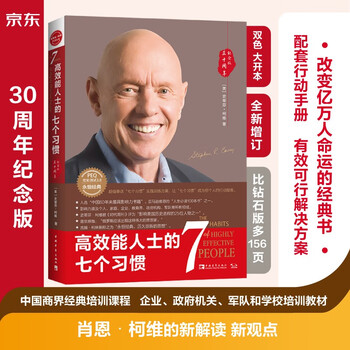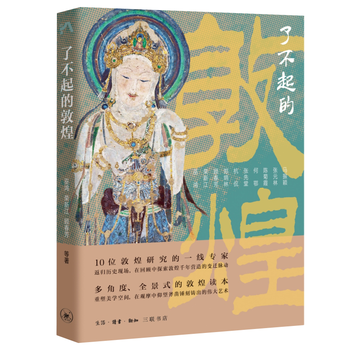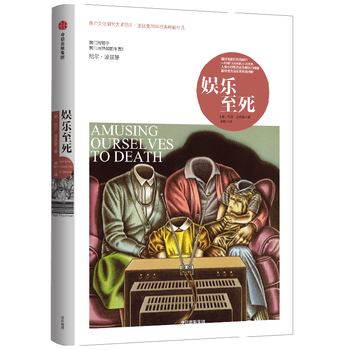内容简介
《黑暗之刺》写于《父之罪》完成后五年,马修?斯卡德此时还是个酒鬼,尚未加入匿名戒酒会。九年前,一个疯狂的冰锥杀手连续刺杀好几位女性后逃逸失踪;九年后,纽约警方在偶然的机遇下逮到此人,其他的案件他都承认,唯独对芭芭拉的死坚决否认。芭芭拉的父亲找到斯卡德,希望能找出是谁杀了他女儿。
“回忆是一种合作的动物,很愿意讨好你,供应不及时,它常常可以就地发明一个,再小心翼翼地去填满空白。”
本书获夏姆斯奖1982年度长篇小说奖。
精彩书评
媒体推荐
当今的犯罪小说作家中,若要找一名堪称雷蒙德·钱德勒与达谢尔·哈梅特的传人,则非劳伦斯·布洛克莫属。
——《旧金山纪事报》
当然,这些情节都不是真实的,可除了布洛克,还有谁能驾驭这样的故事呢?引人入胜的悬念,滑稽搞笑的场景,大胆成功的尝试……总之,这是布洛克的杰作。
——《圣路易斯邮报》
布洛克书中大的主角不是杀手凯勒、不是谭纳、也不是马修,而是一个城市——纽约。
——《人物》杂志
读者始终一路追随马修从年轻气盛直到老而弥坚,从酗酒到滴酒不沾,以他特有的步调踽踽独行于兼具犯罪诡谲与人文艺术氛围的纽约。
——《诚品好读》
名人推荐
在阅读马修·斯卡德的过程中,感觉像小时候看武侠小说那样非要一口气看完不可。我年少混街头但没有混到顶的“遗憾”,或朋友们笑我有黑道情结,在读马修时皆获得满足。马修跟米克·巴卢,男人对男人之间的关系,很过瘾。他们爱看拳击,我也很爱。马修像牛头犬般一旦咬住就不松口的脾气,有时还违反法律,同时又充任法官和陪审团执行法律,甚至像在代替上帝执行正义,都让我记起少年情怀。
拍《悲情城市》时,我常让梁朝伟看些书。空闲时,他就在旁边看书。拍完后,我习惯了看到好看的书就寄给他,或者去香港时顺道带给他。他可能也介绍给王家卫看,后来他们拍《蓝莓之夜》,找的编剧就是布洛克。
——侯孝贤
美国有个作家叫布洛克的,写的关于探案的书很棒。或许有机会我会跟他合作。
——梁朝伟
作者聪明到既放了大量好莱坞元素,又以他对元素步步为营的反讽,既满足了读者的需求,又反讽了自己的俗又有力。
——张大春
劳伦斯?布洛克小说里有很多细节,这些细节不是福尔摩斯式的推理细节,它或许是散乱无用的,但就像一堆拼图,到了正确的时候轻轻摇一下,就会拼出来。
——朱天文
作为一个类型作家,同时又作为一个不愿驯服、抗拒的越界者,劳伦斯·布洛克皆做了精彩、高难度的表演和贡献。
——朱天心
获奖记录
劳伦斯?布洛克获奖记录:
世界推理迷大会的安东尼奖(Anthony Awards):1987、1991年度长篇小说,1994、2001年度短篇小说集;
美国推理作家协会的埃德加·爱伦·坡奖(Edgar Awards):1978年度平装本初版,1983、1992、1995年度长篇小说,1985、1991、1992、1994、1998、1999、2017年度短篇小说,1994大师奖(The Grand Master Award);
美国私人侦探作家协会的夏姆斯奖(Shamus Awards):1982、1983、1987、1990、1991、1992、1994、1995年度长篇小说奖;1985、1994年度短篇小说奖,2002年获颁终生成就奖,2009年“马修?斯卡德”获年度角色奖。
英国推理作家协会的钻石匕首奖(Cartier Diamond Dagger Award,被誉为英国侦探推理小说的诺贝尔奖):2004年度;
日本的马耳他之鹰奖:1987、1992年度。
试读
1
我没有看见他走进来。我坐在阿姆斯特朗后排那个我一向坐的位置上。午餐的人潮已经散去,吵闹的声音也降了下来。收音机里播放的古典音乐,现在你毫不费力就可以听得很清楚。外面一片灰蒙蒙的,吹着可怕的风,空气中含着雨意。不过,这种天气真适合待在这家位于第九大道的酒吧里,一边喝掺有波本威士忌的咖啡,一边读《邮报》上有关第一大道砍人的报道。
“斯卡德先生吗?”他大概六十岁左右,高额头,淡蓝色的眼睛上面架着一副没有镜框的眼镜,变灰的金发服服帖帖地伏在头皮上。他大约五英尺九英寸或十英寸高,重一百七十磅上下,肤色白皙,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瘦削的鼻子,嘴小唇薄,穿着灰色的西装、白色的衬衫,戴着红黑金三色条纹领带。他一手提着公文包,一手拿着雨伞。
“我可以坐下吗?”
我朝我对面的那张椅子点点头。他坐下来,从胸前的口袋里拿出钱包,递给我一张名片。他的手小小的,上头戴着共济会的戒指。
我看了名片一眼,还给他。“抱歉。”我说。
“但是……”
“我不需要任何保险,而且你也不会想要卖给我的。我的风险很高。”我说。
他发出一种类似紧张的笑声。“老天啊,”他说,“你当然会这么想,不是吗?我不是来向你推销东西的。我都不记得有多久没写个人保单了。我专门负责公司团体保险。”他将名片放在我们中间的蓝格子桌布上。“拜托你。”他说。
从名片上看来,他的名字是查尔斯·伦敦,共同人寿新罕布什尔总代理。地址在松树街四十二号,位于市中心金融区内。上面有两个电话号码,一个在市区,另外一个的区域号码是914。应该在北边郊区,也许在韦斯特切斯特。
当特里纳过来为我们点饮料时,我手中还拿着他的名片。他点了帝王牌苏格兰威士忌和苏打水,我则还有半杯咖啡没喝完,等特里纳走开听不见我们的谈话声时,他说:“弗朗西斯·菲茨罗伊向我推荐你。”
“弗朗西斯·菲茨罗伊?”
“菲茨罗伊警探。第十八分局。”
“哦,弗兰克,我有好一阵子没见到他了。我甚至不知道他现在在第十八分局。”我说。
“我昨天下午和他碰的面。”他把眼镜拿下来,用餐巾擦亮镜片。“他向我推荐你,我刚刚说过了,当时我决定考虑一个晚上再说。我没怎么睡。今天早上我有约会,然后我到你住的旅馆,他们告诉我在这里可能找到你。”
我等他继续说。
“斯卡德先生,你知道我是谁吗?”
“不知道。”
“我是芭芭拉·埃廷格的父亲。”
“芭芭拉·埃廷格。我不……等一下。”
特里纳端着他的饮料过来,放在桌上,一言不发地走开。他弯着手指握住杯子,但是没有将杯子拿起来。
我说:“冰锥大盗是我知道这个名字的原因吗?”
“没错。”
“应该是十年以前的事了。”
“九年。”
“她是受害人之一。我那时候在布鲁克林工作。柏根街和弗拉特布什区的第七十八分局。芭芭拉·埃廷格,是我们分局的案子,对吗?”
“是的。”
我闭上眼睛,让记忆浮到脑海中。“她是后面几个受害人之一。应该是第五或第六个。”
“第六个。”
“在她后面还有两个,然后他就洗手不干了。芭芭拉·埃廷格。她是个教师。不对,不是教师,但类似这样的工作。一家日间托儿所。她在一家托儿所工作。”
“你的记忆力不错。”
“应该可以更好的。但是我只处理到判定又是冰锥大盗后,就把案子转给专案承办人。我想起来了,是中城北区。事实上,弗兰克·菲茨罗伊那时候就在中城北区。”
“完全正确。”
我突然记起那时候的感觉。我记得在布鲁克林的一间厨房里,死亡不久的腥臭味压过烹煮食物的味道。一个年轻的女人躺在油毡上,衣衫零乱,身体上有数不清的伤口。我记不得她的长相,只知道她死了。
我喝完我的咖啡,真希望我喝的是纯波本威士忌。坐在我对面的查尔斯·伦敦啜了一小口他的苏格兰威士忌。我看着他金戒指上的共济会标志。我觉得很奇怪,那些标志代表什么意义,还有这些标志对他个人而言又代表什么。
我说:“几个月的时间内,他杀了八个女人。从头到尾都使用相同的犯案手法,大白天里在被害人的家中展开攻击,用冰锥戳得伤痕累累,攻击了八次以后销声匿迹。”
他什么都没说。
“九年后他们逮到他。什么时候的事?两个礼拜以前吗?”
“快三个礼拜了。”
我没有特别用心读那则新闻报道。两个上西城的巡逻警察在街上拦住一个形迹可疑的人,搜身时翻出一把冰锥。他们把他带回警察局,清查他的档案,发现他刚服完在曼哈顿州立医院的延长拘禁。有人多事问他干吗带把冰锥在身上,他们还真是走运。
在大家都还没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前,他就全盘招认了那一长串还未破案的谋杀案。
“他们登出了他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