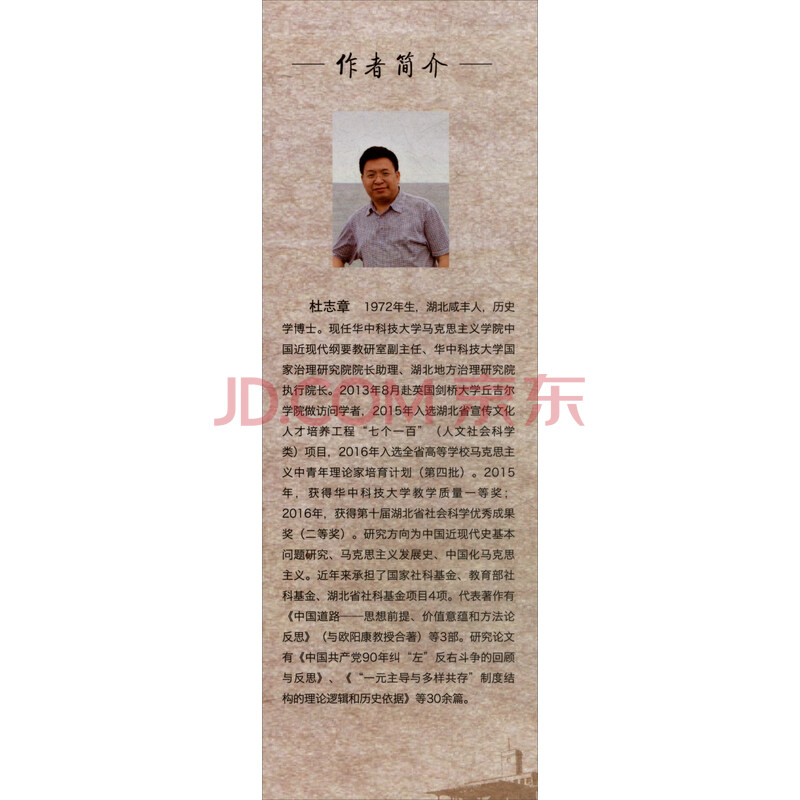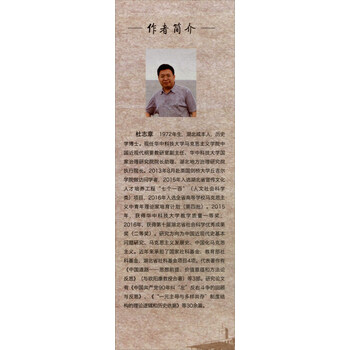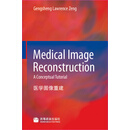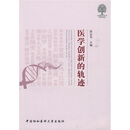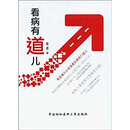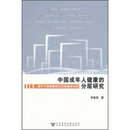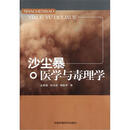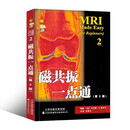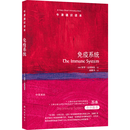内容简介
教会医学对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影响,可概括为“西教”→“西学”→“近代化”的历史与逻辑:由于传教士充当了西方文明载体的角色,在传教过程中,把包括医学在内的许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传到了中国,引起了中国科学的发展和中国社会的变迁。许多中国人是通过认识西方医学,才认识西方文明的;也是通过接受西方医学,才接受西方文明的。因此可以说,近代教会医学催生了中国医学现代化,中国医学现代化又推动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
《近代中国社会变迁:教会医学与中国医学早期现代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论丛》研究的对象为“教会医学”、“中国社会变迁”。研究内容是在对近代“教会医学的发展演变”、“教会医学与中国医学早期现代化”等问题的研究基础上,重点探讨“教会医学对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影响”。
目录
导论
一、研究缘起
二、学术回顾
三、研究思路
四、基本慨念
第一章 医务传教的渊源
一、宗教与医学
二、基督教与医学
三、基督教与在华医学事业
第二章 明末清初教会医学
一、明末清初基督教传教士在华医药活动概述
二、明末清初基督教传教士译著西医书籍概览
三、明末清初教会医学对中国医学的影响
第三章 近代教会医掌迅速发展的背景
一、16一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对外扩张
二、鸦片战争及系列中外条约的签订
三、16-19世纪中西方医学不同轨迹的发展
四、非传教士在中国早期医药活动的影响
第四章 近代教会医学的发展历程
一、教会医学的奠基(1835-1860年)
二、教会医学的拓展(1860-1900年)
三、教会医学的繁荣(1900-1937年)
四、教会医学的消退(1937-1951年)
第五章 教会医学与中国医学早期现代化
一、西方医学日益为中国人所认同
二、中国传统医学遭到质疑和批判
三、现代医学体系在中国的确立
附录A 关于医学社会史的理论思考
一、医学社会史的定义
二、医学社会史的学科定位
三、医学社会史的研究对象
四、医学社会史的研究方法
五、医学社会史的价值判断
附录B 医学社会史研究案例——“卫生”含义的现代转型
一、中国传统的“卫生”含义
二、清末“卫生”含义的现代转型
三、民国时期“卫生”含义的进一步演变
参考文献
后记
试读
《近代中国社会变迁:教会医学与中国医学早期现代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论丛》:
三、基督教与在华医学事业
(一)在华医药事业被认为是基督教传教的重要手段
基督教在唐代、元代、明清及近代多次传人中国,几乎每个时期的传教士都以医药事业作为传播福音的重要手段。明代,在葡萄牙人取得在澳门的居住权后不久,担任日本和中国教区代牧主教的贾尼劳(Carneiro)便在澳门开办了仁慈堂和两所医院,这是中国领土上最早出现的西医医院。此后,又有一些传教士及传教机构在澳门及东南沿海地区开展医疗活动。这些医疗活动有利于澳门社会的稳定,有利于维护葡萄牙富商的利益,也有利于扩大天主教在澳门的影响。明代耶稣会士还以“天算舆地医学等结人心,颇得华人所重”。例如,天主教医学传教士邓玉函(Jean Terrenz)就将瑞士巴塞尔大学包因教授(Gaspard Bauhin)的《解剖学论》译成《泰西人身说概》,并与罗雅谷(Giacomo Rho)、龙华民(Nicolas Longobardi)合作译述了《人身图说》等。清代前期,也有许多医学传教士在中国广泛开展医疗活动。如1693年,法国传教士洪若翰(P.Joames Fontaney)和葡萄牙传教士刘应(Mgr Claudusde Visdelou)向康熙帝敬献金鸡纳霜(奎宁),治愈了康熙的疟疾。此后,又有医学传教士张诚(P.Joan Franciscus Cerbillon)、徐日升(P.Thomas Pereyra)、罗德先(Bernard Rhodes)、罗怀忠(Jean-Josephda Costa)等也因身怀高超医术或进献特效药物而深得朝廷赏识。即使在康熙晚年宣布禁教以后,他们仍能获准在北京或全国其他地区居住,开设药房、诊所,建立教堂等。这些医学传教士的医药活动使他们获得了接触朝廷上层且留居中国的机会,从而为进一步传教创造了条件。
基督新教早在1807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RobertMorrison)来华后就在中国开始传播。然而,由于中国社会各阶层对中国原有文化普遍怀有优越感,再加上长期接受儒道“现世关怀”文化传统的影响,对基督教缺乏兴趣;同时,清廷的闭关政策和禁教政策也阻碍了传教事业的发展。因此,在头20年,传教活动收效甚微。为了打开局面,传教士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些有效经验——医务传教。1820年,马礼逊与东印度公司医生李文斯顿(Dr.J.Livingstone)在澳门开办诊所;1827年,东印度公司医生郭雷枢(Dr.Thomas R.Colledge)在广州创办医院,从而为传教士与中国人接触提供了极好的机会。普鲁士自由传教士郭实腊(Karl Friedich August Gutzlaff)于1831-1833年内多次潜入中国沿海地区活动,曾为沿海居民施医送药。他发现中国人对免费的医药服务十分欢迎,于是产生了“医务传教”的念头,并建议英美传教差会对将要派往中国的传教士进行正规的医学训练。他说:“我们需要在中国的腹地有一所医院,而且我们需要有人为了此项事业在那里独自生活。”这是最早关于派遣医学传教士到中国来的建议。美部会采纳了郭实腊等人的建议,于1934年派遣医学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来到中国。1835年11月4日,伯驾在广州开办“普爱医院”,开始了“医务传教”的历史。1835年,郭雷枢也在《中国丛报》上撰文呼吁英美教会派医生传教士来华,他说“现在正在派遣传教士的差会应该向这个蒙昧的各族派遣医生”,他们“将会通过获取中国人的信任而为传播基督教铺平道路”。在郭雷枢等人的推动下,中国医务传教会(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于1838年4月成立。虽然“中国医务传教会”的宗旨已远远超出了宗教目的而带有强烈的世俗意义,在一定程度上为政治和贸易服务,但是医务仍然被视为传教的重要手段。正如在中国医务传教会成立不久,郭雷枢、伯驾和美部会最早来华的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共同署名发表的一封公开信所言,“通过为人们治病送药,解除病痛,可以消除中国人的排外心理和蔑视态度,赢得理解和尊重”,“从而可以顺利地传播基督教”。
……
前言/序言
近代中国教会医学(missionary medicine)是指近代基督教各差会及传教士在中国开办医院、诊所施医送药以及创办医护学校培养医学人才等事业的泛称。教会医药活动的目的在于传教,但其客观上将西方近代医学传人中国,促使了中国医学的现代转化,最终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近代著名医学家严福庆指出:“西医发达日见成效,使我国多数人得西医之真传,知博爱之感化,如吾人有独办之能力,即脱离(教会)关系,任我国人独办之。”曾选择医学救国的鲁迅也指出,“日本维新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与之相仿,中国的早期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也与教会医学有关。
教会医学对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影响,可概括为“西教一西学一近代化”的历史与逻辑:由于传教士充当了西方文明载体的角色,在传教过程中,把包括医学在内的许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传到了中国,引起了中国科学的发展和中国社会的变迁。许多中国人是通过认识西方医学,才认识西方文明的;也是通过接受西方医学,才接受西方文明的。因此可以说,近代教会医学催生了中国医学现代化,中国医学现代化又推动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
虽然中国的现代化并不等同于“西化”,但西方文明对中国现代化的启迪和推动作用却无可否认。近代中国人对待西学,经历了怀疑(抵制)一接受(中体西用)一崇拜(全盘西化)一理性选择(中西会通)的艰难历程,这与中国人对待西医的态度惊人地相似,即排斥西医一中西医并行一要求废除中医一中西医会通。这种一致性表明,中国医学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缩影,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教会医学不仅促使了中国医学现代化,而且引起了近代中国社会在许多方面的重大变迁。一是世界观的变迁:从“华夷之辨”到“师夷制夷”。教会医学凭其“仁慈而有效”的印象改变了中国人传统的“华夷”观念,“师夷”成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基本取向。二是科学技术的变迁:从“实用经验”到“科学理性”。医学传教士在传播医学和宗教的同时,还把近代西方的生物、化学、天文、地理、矿物等自然科学知识以及国际法、经济学、政治学等方面的社会科学知识传人中国。这些科学传播活动,对中国早期现代化起到了思想启蒙作用,奠定了中国现代化的科学基础。三是价值观的变迁:从“尊崇传统”到“反思、批判与建构”。伴随着西医的优势日渐显露,传统中医开始遭遇怀疑和批判,甚至出现了几次“废止中医”的政府决策,这也引起了人们对包括传统中医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批判。“西医”以科学的面貌在近代中国新文化运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四是社会风貌的变迁:从“封建礼教”到“人性复归”。医学传教士广泛参与革除中国传统陋习的活动,如戒除吸食鸦片、赌博、缠足、卖淫,印发预防疾病的宣传资料,大力宣传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健康观念等,对于近代中国道德革命以及社会风貌的改变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五是社会结构的变迁:从“士农工商”到“多元分层”。伴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又出现了许多新的职业,除西医的医生和护士之外,还有教师、律师、银行家、科学家、革命者等,使中国的社会结构由单一而稳定的“士农工商”向“多元分层”转化。
概括而言,近代教会医学是导致中国社会近代变迁的重要因素。梳理近代教会医药事业及其对中国医学现代化的影响,可以再现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一个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