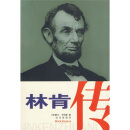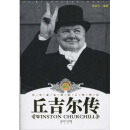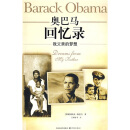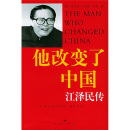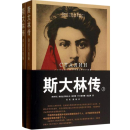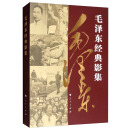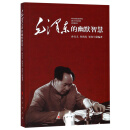内容简介
《奥巴马回忆录:我父亲的梦想》作者巴拉克·奥巴马,主要讲述的是奥巴马的故事。奥巴马出生于夏威夷,父亲是肯尼亚一名黑人经济学家,母亲是美国一名白人女教师。父母在奥巴马两岁的时候分手,在听说父亲1982年在肯尼亚死于车祸前,奥巴马只见过父亲一次,奥巴马跟着母亲和姥姥姥爷长大。
父亲离开了,奥巴马跟着母亲长大。邓纳姆后来嫁给了一名印尼石油公司的经理罗罗·素托罗,素托罗由于工作的关系需要去雅加达,于是,邓纳姆带着6岁的奥巴马去了印尼。奥巴马在印尼度过了四年的童年时光。
10岁时,母亲与继父离婚,奥巴马回到了夏威夷,大部分的时间他和外祖父外祖母生活在一起。
在2004年7月,民主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奥巴马被指定在第二天做“基调演讲”。所谓“基调演讲”,就是民主党人阐述本党的纲领和政策宣言,通常由本党极有前途的政治新星来发表,1988年做“基调演讲”的人就是时任阿肯色州州长的克林顿。奥巴马不负众望,他亲自撰写演讲稿,并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在演说中他提出消除党派分歧和种族分歧、实现“一个美国”的梦想。
45岁的奥巴马演说极具魅力,灿烂的笑容更虏获许多民众的心。与过去有意竞选总统的黑人前辈相比,奥巴马是首位在初选前民调获得全国性支持的明日之星,打败2008年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黑人总统。
精彩书评
当母亲告诉我那些南部学校的防除产只能读从富有白人学校里传出来的书,却仍然能成为医生、律师和科学家时,我为自己早上不愿起床学习而感到羞愧。
——选自《一部 我的身世》
组织者是赚不到钱的,他们的贫穷正是为人正直的证据。
——选自《第二部 芝加哥起飞》
那推倒任何使人弯腰而不是直立之力量的决心,能在从前没有音乐的地方谱出乐章。
——奥巴马人生感悟
美国政坛有史以来很好看的回忆录。
——《时代》周刊
奥巴马是个有故事的人。
——吴念真
目录
第一部 我的身世
第二部 芝加哥起飞
第三部 梦回肯尼亚
试读
第一部 我的身世
那是在我二十一岁生日刚过几个月之后的一天,一个陌生人打电话告诉了我这个消息。当时我住在纽约哈莱姆以东和曼啥顿区交界处的一个不知名的地方,位于第一大道和第二大道之间的第九十四街,那里的环境并不怡人,草木贫瘠,一排排灰黑色的临街公寓遮住了一天当中的大部分阳光。我住的那个公寓楼很小,地板已经倾斜,供暖断断续续,楼下的门铃也坏了,前来造访的客人必须事先在街角的加油站打一个付费电话才能上来。那儿还有条像狼一样大小的黑色杜宾犬,嘴巴里总是叼着一个空啤酒瓶子,夜幕降临的时候,它就会机警地走来走去。
其实这些都跟我没多大关系,因为我根本就没有什么客人。那些日子,我总在焦躁不安地忙碌于自己的事情,忙碌于那些没有实现的计划,当时的我总是把其他人看作是多余的干扰,不过我倒也并不是不喜欢和人交往。我还是乐于与那些波多黎各裔的邻居们用西班牙式的客套语寒暄上几句的。在下课回来的路上,我还会经常停下来与一群男孩子们攀谈一会儿,他们整个夏天都待在门廊上谈论尼克斯队,谈论他们在前一天晚上听到的枪声。要是赶上好天气,我和室友就会围坐在炉火旁抽上几根烟,欣赏暮色渐渐淹没了城市上空的蔚蓝。要不然我们就会看着那些住在旁边高档社区的白人到我们街区来遛狗,让狗在路边拉屎。这时,我的室友就会怒气冲冲地朝他们大骂:“把狗屎弄干净,你这杂种!”在他们弯下腰去铲狗粪便的时候,我们就会面无愧色地嘲笑主人和狗。
每当那样的时候我也会感觉到快乐,但那快乐只是暂时的。一旦谈论的话题偏离了主题,或者转向了加深彼此之间的了解,我就会找个理由起身告辞。我已经习惯了一个人享受孤独的世界,因为我知道只有那里是最安全的。
我还记得当时有一位就住在隔壁的老人,和我有着相似的性情。他一个人孤苦伶仃地生活,偶尔外出时,人们就会看见一个苍老佝偻的身影,穿着一件厚重的黑色外套,戴着一顶怪模怪样的软呢帽独自蹒跚而行。有时候,我在楼下碰巧看到他刚从商店买东西回来,就会主动上前帮他把东西提上楼去,他会看看我,然后耸了耸肩。于是我们就一起上楼了,在每一层的楼梯拐角处他都要停下来歇一歇。终于到了他家门口,我小心翼翼地把袋子放在地上,他礼节性地点点头表示谢意,然后就走进房间关上了门。我们甚至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他也不曾向我表示过一次感谢。
老人的沉默寡言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心
前言/序言
离这本书第一次出版已将近十年了。我在初版的介绍中提到过,写作这本书的机缘来自我还就读于法学院的时候,因为当时我成功地当选了《哈佛法律评论》的首位非裔美国人社长。经过几次务实的公开洽谈后,我收到了一位出版商的预付款,于是开始写作,相信自己的家族故事以及我为理解这些家族故事而作出的努力,可能会在某些方面涉及到美国历史上无法抹灭的种族隔阂问题,以及地位身份变动的状态(一直以来,这都是一个飞跃,一种文化冲突的状态),那是我们现代生活中的烙印。
与大多数第一次写作的作者一样,我对于这本书的出版寄予了厚望,同时又感到遗憾。我希望这本书可以超越我年轻的梦想而大获成功,而遗憾的则是我并没有写下什么值得讲述的事情。事实刚好是处于两者之间。这本书得到了还算不错的评论,事实上评论的人只是在出版商安排的刊物上发表意见。书的销量平平。于是,几个月后,我仍继续我原来的生活,并且确信,我的职业写作生涯是短暂的,但还是很高兴自己能没有损失一丝一毫的尊严便走过这段路程。
在出版后的十年里,我少有时间来反思这本书。在1992年的大选中,我负责一个选举人的登记方案,开始从事民权工作,并且开始在芝加哥大学教授宪法。我和妻子买了一处房子,幸运地拥有了两个漂亮、健康、淘气的女儿,为还清账单上的债务而努力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