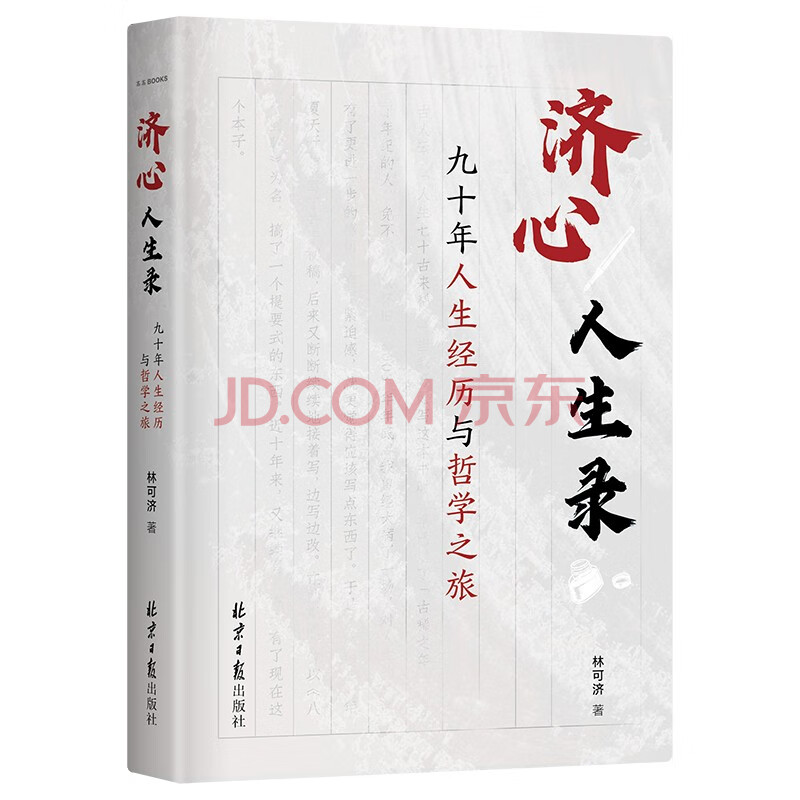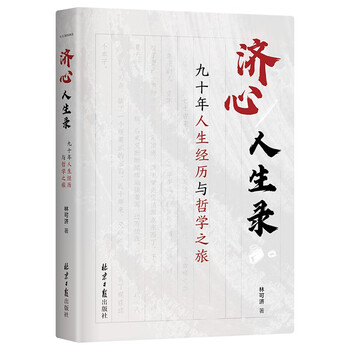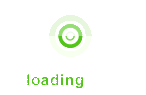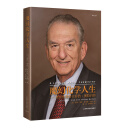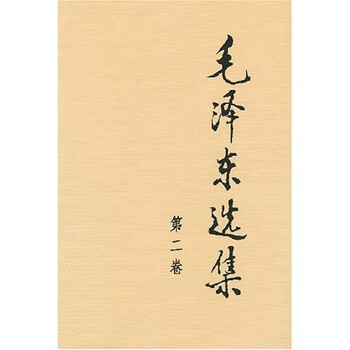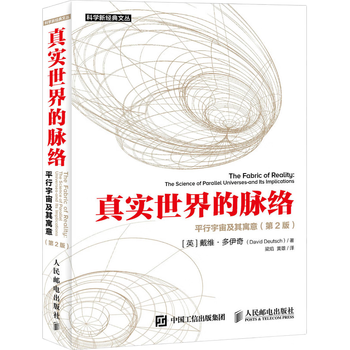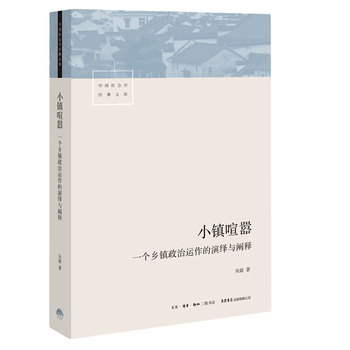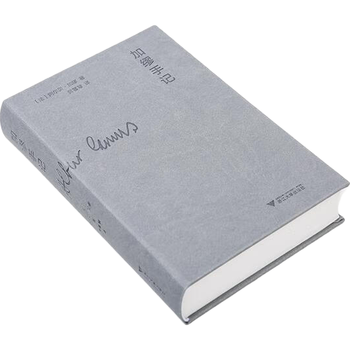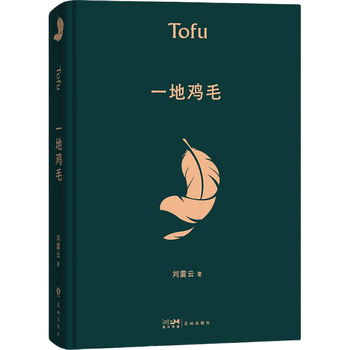内容简介
这是一位九十岁学者的人生回望,也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记录时代与自我成长的真诚自述。他出生于福州郊区的一户农民家庭,少年从军,曾参加抗美援朝;1954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曾受教于包括金岳霖、冯友兰、张岱年、张世英等在内的诸多当代哲学大师。大学毕业后,他主动回到家乡福建教书育人,毕生从事哲学教学与研究。九十年光阴,他以平实的笔触叩问历史、思考人生、回忆往事、怀念故人,也汇聚了大量对人生、教育、爱情、家庭与死亡的沉静思考。这不仅是一部自传,更是一部具有珍贵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的哲学研究史、地区教育史、私人口述史,同时,也是一堂讲给普通人该如何过好平凡却不平庸一生的人生感悟课。
试读
第一章?
童年、小学、初中、高中
(1950年以前)
在这一章里,简要记述我的童年和读小学、初中、高中的若干情况。其中,福州的两次沦陷,至今不忘。
我的故乡和我的长辈
我的故乡在福州的西郊靠近凤凰池的一个小村落。那个村落的后山上,有一座庙,名叫“将军庙”,里面供奉着“西山协惠将军”,因而这个后山就被称为“将军山”。
我的家乡,谈不上风景优美,但有山有水,一派田园风光。全村有近百户人家,以务农为主,绝大多数姓林。彼此之间,都有亲疏程度不同的亲戚关系。
我的祖父林作庵,是乡间的中医。他和祖母周氏结婚后,生下我的父亲和两位叔叔、一位姑姑。祖父在世时,我并未见过他的面。我所看到的,只有挂在客厅墙上、出自民间画家之手的画像,以及写着“妙手回春”“功同良相”之类赞词的横匾。它们都挂在老宅门框上面的显著位置。祖母长寿,享年九十有七,如果把所经过的闰月算上,可说是过了百岁的长寿老人了。
父亲林仰霄(1897—1939年),曾经读过一些书,母亲马淑芝(1897—1973年)的娘家在北门的农村白水塘,她识不了多少字。
听我母亲说,我的出生地是在上海。时间是农历癸酉年十一月十三日(对应于当年的阳历是1933年12月29日)。当时,我父亲在上海的海关做事。后来,全国抗战爆发,政府内迁,父亲的工作也随着变动,我们全家都搬到四川省的万县。
我依稀记得:站在万县家里的阳台上,可以看到大钟,它静静地矗立在附近的一所公园里。大人带着我去公园玩,最吸引我注意的是爬行的蜗牛。平时印象最深的是,每当警报响起,许多人都跑到离家稍远的巨大岩石的下面,去躲避日本飞机的空袭。
我的不大记事的童年,是在这样的战争环境中度过的。
母亲还告诉我,小的时候,我曾经患疝气,多方治疗而无效。后来因吃了许多当地盛产的龙眼,想不到竟不知不觉地痊愈了。
1939年12月8日,我父亲病逝,家里失去经济来源。没有工作的母亲,带着我们四个兄弟,辗转绕道,经过柳州、长沙等地,历时两个多月,终于回到了我在前面说的、那个位于福州西郊的农村老家。
我有三个哥哥,没有姐妹。三哥林柱生大我两岁,二哥林耀星又比三哥大一岁,他们的年纪与我相去无几;好在大哥林松年的年纪大出了许多,在从四川返回福州漫长而又艰险的旅途中,他出了不少力。在从四川返回福州的路途中,我还生了一次病,发高烧,险些丧命,细节记不住了。
回到故乡以后,对我来说,一切都是陌生的。祖母主持着大家庭,那时二叔已去世,三叔在外地工作,偶尔回家,我对他印象不深。我母亲同两位婶婶一起,参加中断多年的田间农业劳动,并以此为生。
父亲生前曾买过人寿保险,他去世时才42岁。因此,我母亲领到一笔保险赔偿金,并把它分为三份:一份给我大哥,用于去上海的私立大厦大学读书;一份给祖母买“寿板”(木头棺材板),以备她“百岁”时使用;一份用于购买土地。这时,我母亲已和婶婶们一起在我祖父遗留下来的土地上劳动,无力在买来的土地耕作,于是,就把它出租给一位远房的舅舅。当时,农村的人都认为,购买土地是最保险的产业,但以后的事实却证明:这种谁都无法预料的做法,竟然铸成大错,它为后来我母亲被误评为“富农”留下了隐患,在“左”的政策下,长期以来,它给我们全家带来了数不清的伤害。
小学阶段的三所学校
我家附近一个名叫“祭酒岭”的地方,那里有一所教会办的“私立协和小学”。1940年9月,我到那里读一年级。在这短暂的时间,我第一次接触了基督教。做礼拜、过圣诞节,对于一个生活在农村的小孩来说,新鲜而又有趣。而且,它那异国的风俗,多多少少带着神秘的色彩。
1941年4月21日,福州第一次沦陷,被日本侵略军占领。当时,我刚刚在念一年级的第二学期。
学校停课了,但村里的私塾仍旧在教书。家里为了不让我荒废学业,也让我去念了一阵子私塾。年纪小的读的是《三字经》《千字文》《幼学琼林》等。年纪稍大的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左传》等古籍。不同年龄的儿童,都坐在一间很大的农家房屋的大厅里,朗读之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我一边读自己的书,一边又忍不住听到他人读的书。我当时是从《三字经》和《千字文》开始读的,但同时又可以听到其他年纪大的小孩所读的书。老师要求当天的功课当天就要能够背诵,否则就要挨打手心,或者留下来继续读,直到老师认可才能回家。另外,还要练毛笔字。
说起村里的私塾,虽然许多人看不起它,但却给我很深刻的印象。尽管时间不足半年,很难说读了多少书,即使读过了,也未必理解其中的道理。若干年后,当我阅读到上述相关的古典著作时,耳边仿佛又响起了当年在私塾时同窗好友的朗读声,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1941年9月3日,福州光复。过了一段时间,我转学到位于福州西湖附近的“私立榕西小学”,插班读二年级。又过了一年,转学到公立的“福州西峰小学”。1945年7月小学毕业。那是我所读的第三所小学。
读福州西峰小学期间,福州第二次沦陷。我再一次进入私塾,这时,年龄稍大,对所读的内容,也未必都能理解。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地懂得了其中的意思。后来我对中国古典文学、书法会感兴趣,实与此有关。
当然,我读小学还是以“洋学堂”为主。那时,学校的功课压力,似乎不如现在的小学生们这么大,课余闲暇的时间还不少。生长在农村的自然环境中,好玩的地方很多。池塘可以戏水,后山林密草深之处,是捉迷藏的好去处。农忙割稻子时,跟着大人,在稻田里可以轻而易举地捉到泥鳅和小青蛙。我母亲的娘家在福州市的北郊,有时去那里的亲戚家做客,是最开心的了。不仅有好吃的,一路上过溪涉水,跨石墩,边走边玩。
前言/序言
自?序
古人云:“人生七十古来稀。”当我开始写这本书时,早已过了“古稀之年”。上了年纪的人,免不了喜欢怀旧。2003年年底,我大病了一场,对人生的真谛有了更进一步的感悟,有了紧迫感,就更觉得应该写点东西了。于是,从2004年夏天开始,写了若干初稿,后来又断断续续地接着写,边写边改。在此期间,曾以《八十回眸》为名,搞了一个提要式的东西。近十年来,又继续写,方才有了现在这个本子。
记得胡适先生曾经在他的著作《四十自述》中大致说过这样的意思:“四十岁写儿童时代,五十岁写留学时代到壮年时代,六十岁写中年时代。”按照这个时间表,我已迈入耄耋之年,才写这些文字,显然已经太迟了。但迟有迟的好处。我生性愚钝,几近后知后觉,以现在的眼光,对许多往事,也许会比我在年轻时,看得更清楚一些,体验得也更深刻一些。
我很喜欢诸葛孔明的“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也很欣赏陶渊明的“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还有苏东坡的“一蓑烟雨任平生”等。它们的精神实质是相通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物欲横流,要真正做到淡泊、宁静,几乎是难乎其难,至于像陶诗所描写的那样“采菊东篱”,恐怕是连想都不要去想了。但“自静其心,无求于物”,则是可以,而且应当努力做到的。陶诗中的最后两句:“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其中所蕴含的深意,更是特别值得人们反复地领悟与体会。
今年我八十有九,已过“米寿”,按民间说法,正跨入九十。回首往事,不胜唏嘘。我年轻的时候,应该说是个有理想、有抱负、追求进步,对未来有着美好憧憬的热血青年。投身革命,以身报国,在当时是顺理成章、自然而然的事情。其中虽然包含年轻人的稚嫩与冲动,但对民主、自由的向往,是毋庸置疑的。然而,现实的社会是复杂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知识的积累,我慢慢地发现,太多、太多的事情,常常是“事与愿违”的。
知识分子就其承担的社会责任来说,不应当仅仅理解为“有知识的人”(lntellectual),更重要、应当的是“有思想的人”(lnstructor)。换言之,真正的知识分子,应保持自己独立的见解,而不应人云亦云,随波逐流,也更不能同流合污。五四时期的仁人志士所倡导的“科学”“民主”,应该不断地在后来者那里得以传承,并发扬光大。每当我认真沉思自己将近九十年来已经走过的人生之路时,总是不禁心潮起伏,感慨万千!
本书共有十一章,讲的大都是一些虽已过去、但又不应忘却之事。其中有苦、有乐,有喜、有悲,我的人生并没有大起大落,就总体而言,是平淡无奇的。即便是这样,若要系统、全面地回顾,也非易事。现在,仅能选择其中印象较深、记得起来的人生经历和哲学生涯中的若干片段,简略地记述下来。就此而言,这些文字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自传。
叩问历史,思考人生,回忆往事,怀念故人,仅此而已。
全书大体上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来写的,所分的阶段虽然是根据历史事件而定,但并不十分严格。其中大的阶段包括:从小学到高中的读书时期,参加部队(抗美援朝)时期,北大求学时期,最长的时间是在福建师范学院和福建师范大学,执教六十多年的时期。中间还包括下放到农村两年多时期。
对于不同时期或同一时期、不同情况出现的同类事情,有时出于行文的方便,也把它们集中起来,作概括性的叙述。每一阶段总有一些值得特别关注、反思的事情,在集中叙述时,不免多说了几句。对不同时期的历史事件,着墨的详略程度,也必然各异,只能是“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有的事情在正文中不宜展开阐述,就在注释中说,或者把过去已经写成的文字拿来作为“附录”,以为补充。正文、注释、附录三者之间,阅读时可以相互参照。这样,从文体来说,显得很不统一,也不匀称,难免有些“不伦不类”,贻笑大方了。
六十多年哲学之旅的征途中,由于教学内容改变而引起的学术研究领域的变化,先后把重点放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辩证法(科学技术哲学)”“中西哲学比较研究”这三个方面。
在这六十多年,特别是退休以后所写的学术专著、论文集的陆续出版,也算是我在哲学之旅中的一种收获。这些著作虽然水平不高,但敝帚自珍,不妨略作介绍,聊以备忘。
在各个相关的部分中,除了概括性的叙述之外,还收入了已有的专题性的文字以作为附录。这些附录,有个别的已经在相关的报纸或刊物上发表过,但绝大多数都是在不同时期写的、未曾发表过的文稿。为节省篇幅,或减少重复,收入本书时,对于原文稍长的,做了不同程度的技术性处理。
在这些章节中,免不了要涉及学术观点,不得不进入理论思维的领域。其中的专业名词、抽象概念固然枯燥,却又是无法省略的。
既然是回忆性质的文字,除了老年人难以避免的记忆失误以外,力求做到真实,实话实说。本来这是首要的,又是最基本的。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一度出现讲假话不仅不会受到惩罚,甚至还得到好处,而讲真话倒需要有很大的勇气,还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北京大学已故的著名教授季羡林先生在生前曾经提倡:“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这句话看来似乎简单,但做起来却非常不易。
这本书力求做到“假话全不说”。对于经历过的诸多事情,不能不做些筛选,可说者则说之,不宜说,或不许说者,则只好不说。这也许就是“真话不全说”的意思吧!这应该是被允许的。当然,我不说的,自有他人说之;我辈今生无法说明白的,或者说不得的,只能留待后人评说了。
此书写作,从开始酝酿到现在搁笔,前后跨越20余年。静观平生,虽未尽如人意,却也无愧吾心。如能真正做到“直道而行,俯仰无愧”,那就心安理得,不虚此生了!
是为序。
林可济?2022年4月
于福州仓前山福建师大之华庐住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