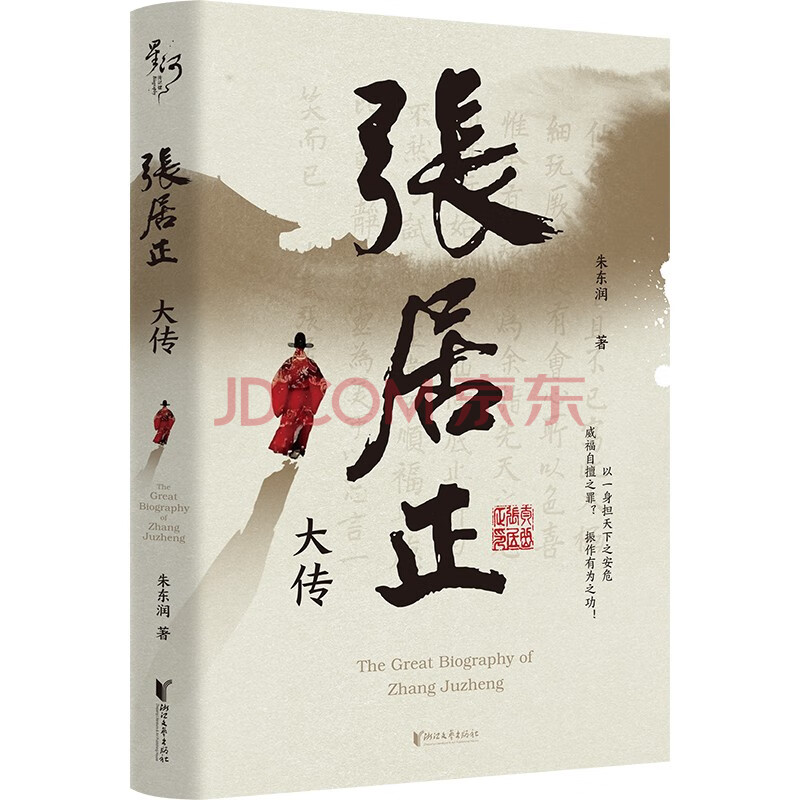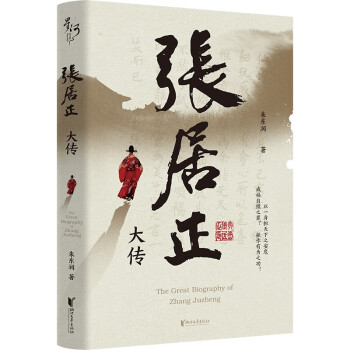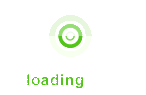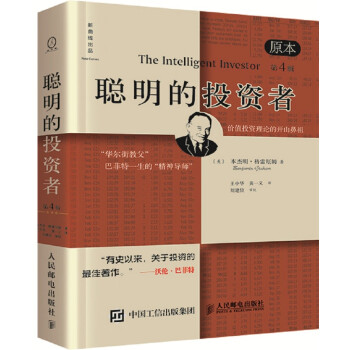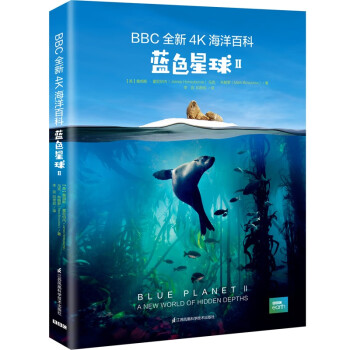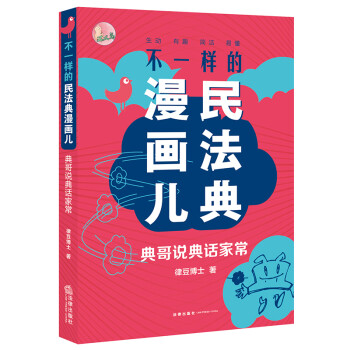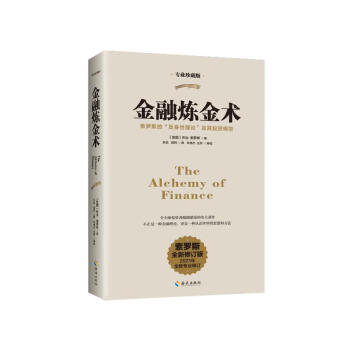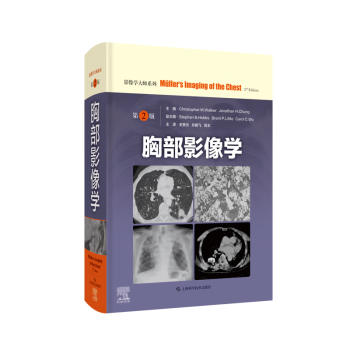内容简介
这是一本长篇人物传记。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幼名张白圭,生于湖广江陵(今湖北荆州市荆州区),故又称之“张江陵”。明朝政治家、改革家、内阁首辅,辅佐明神宗朱翊钧进行“万历新政”,史称“张居正改革”。他从荆州的一个普通家庭起步,经过不懈努力,成为万历首辅、神宗皇帝老师,以及明朝中兴的奠基人。本书是朱东润先生由传记理论研究转入传记文学创作的开端,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被誉为“二十世纪四大传记”之一。阅读本书,读者会对张居正这位专制王朝的著名改革家有更深刻的理解与同情,对传主所置身的那个时代有更清醒的认识与反思。本书不仅有突出的学术成就与研究价值,也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与实用价值。
目录
第一章“荆州张秀才”
第二章政治生活的开始
第三章休假三年
第四章再投入政治旋涡
第五章内阁中的混斗(上)
第六章内阁中的混斗(下)
第七章大政变
第八章初步的建设(上)
第九章初步的建设(下)
第十章第一次打击以后
第十一章从夺情到归葬
第十二章元老的成功
第十三章鞠躬尽瘁
第十四章尾声
试读
居正和高拱的私交本来不错,但是现在他们的地位太逼近了。逼近便是一种威胁,高拱当然不会愉快,而且高拱有他的一群人,他们要立功,便要先替高拱制造敌人,然后再把敌人打倒。政治的主张是由黑暗走向光明,但是政客的阴谋是由光明走向黑暗。高拱死后,居正和高拱的亲戚说:“不穀与玄老为生死交,所以疏附后先,虽子弟父兄,未能过也。叵奈中遭人交构其间,使之致疑于我,又波及于丈,悠悠之谈,诚难户晓。”黑暗中的动物,永远在黑暗中蠢动。
高拱对于居正,固然感到威胁,但是居正对于高拱,也时时感到危险。“尔诈我虞”,成为高、张联立内阁的标语。最容易引起误会的,还是徐阶的家事。居正已经是一路提心吊胆,“畏行多露”了,但是,“不行,为什么他要帮助徐阶说话呢?”黑暗中的声音要问。黑暗中的动物没有道义,没有感情,他们也不相信人类还有道义和感情。“势利呀!”他们要说,“一切都是势利,在朝的首辅便捧他一把,在野的首辅便踢他一脚:这是人情。再不然,便有另外的动机!”黑暗中的动物又被动员了,他们要报效高阁老,便得搜求居正帮助徐阶的动机。他们把发明当作发现,终于认定已经发现了居正的动机。
这个消息很顺利地传达到高拱那里。事情是这样的:徐阶的儿子送三万两银子给居正,于是居正承认替他们维持。在大学士的朝房里,高拱看见居正,便半真半假地讽刺了一顿。这一个刺激太大了,居正变了色,指天誓日地否认这件事。经过这样的剖白以后,高拱承认这是误会,事情勉强结束。
内阁的政潮正在准备着新的发展。隆庆六年三月尚宝卿刘奋庸上疏条陈五事:(一) 保圣躬,(二) 总大权,(三) 慎俭德,(四)览章奏,(五)用忠直。第二条和第四条都很活跃。奋庸说:“今政府所拟议,百司所承行,非不奉诏旨,而其间从违之故,陛下曾独断否乎?国事之更张,人才之用舍,未必尽出忠谋,协公论。臣愿陛下躬揽大权,凡庶府建白,阁臣拟旨,特留清览,时出独断,则臣下莫能测其机,而政柄不致旁落矣。”他又说:“人臣进言,岂能皆当,陛下一切置不览,非惟虚忠良献纳之诚,抑恐权奸蔽壅,势自此成。望陛下留神章奏,曲垂容纳;言及君德则反己自修,言及政则更化善治。听言者既见之行事,而进言者益乐于效忠矣。”奋庸请穆宗总大权,大权旁落,必有所在;又说权奸蔽壅,“权奸”二字必有所指。同时给事中曹大埜上疏劾高拱不忠十事,据说这是居正主使。政治的斗争从言官发动了。高拱的部下立刻应战,给事中涂梦桂劾刘奋庸动摇国是;给事中程文再劾奋庸、大埜“渐构奸谋,倾陷元辅,罪不可胜诛”。结果奋庸谪兴国知州,大埜谪乾州判官,高拱又得到小小的胜利。
在不断的政治战争中,端拱无为的穆宗皇帝终于感觉厌倦,在隆庆六年五月逝世了,是年三十六岁。
书摘二
居正对神宗正和一位尊严的小学教师一样,利用一切的机会,要把自己的学生领上理想的境界。他看到小学生正在一步步地跟着自己迈进,心里感觉到无限的喜悦。然而,他忘去学生只是一个人,是人便有人的无限的光景,同样也有人的必然的缺陷。何况神宗是世宗的孙子,是穆宗和李太后的儿子,在他的血管里,正动荡着倨傲、颓废和那委屈迁就、伺机图逞的血液!
神宗在讲官们的教导中逐日成长了,但是小学教师只看到一个驯服听话的学生。一次神宗朗诵《论语》的时候,失于检点地竟把“色勃如也”读作“色背如也”。在旁站着的居正厉声说:“应当读作‘勃’字。”这一下神宗真有些“勃如”,但是居正没有看到。
性质倔强的人遇到压迫的时候常会感到非常的烦闷,成人如此,小孩子也如此。有时小孩子受到父母和师长的压迫以后,便对弟妹发作一番;再不然,看到小狗、小猫,也得踢一脚,这是方向的移转,发作还是发作。神宗对居正真是恭敬万分,慈圣太后要他这样,他能不恭敬吗?还有司礼监冯保呢!这是管理宫内一切事务的人,慈圣太后都听他的话,自己更得听话了。神宗称他“大伴”,连名字都不便提,正和只称居正为“先生”一样。小小的心灵对于“大伴”已是非常的悚敬,何况在文华殿的时候,连“大伴”也肃然地站在那里,自己能不用心听话吗?居正讲到国家大事,“大伴”又那样耳
提面命地道:“‘先生’是先帝托孤的忠臣,‘先生’说的话,皇上要得仔细听啊!”于是居正面上又蒙上一重特有的庄严,神宗被驯服得和小羊一样。
但是,神宗时常感到异常的烦闷。十岁的时候,慈庆宫后房被毁了,御史胡涍疏请放归后宫宫人,内称“唐高不君,则天为虐”。神宗大怒,要他明白回奏,经过居正再三解释,胡涍还是得到斥逐为民、永不叙用的处分。十二岁的时候,内监张进醉酒放肆,言官交章弹劾,神宗勃然大怒,认为言臣干涉宫内琐事,完全是欺蔑皇上。十四岁的时候,看到奏疏中提到江洋大盗“缚王劫印”一句,神宗震怒非常,认为抚按处罚太轻。居正说:“盖主上恒以冲年,恶人之欺己,故以失事为可逭,而以隐匿为深罪也。”居正看到神宗因为自己年幼时常痛恨诸人之相欺,但是居正没有预料到这和万历十年以后,神宗痛恨居正是有同样的心理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