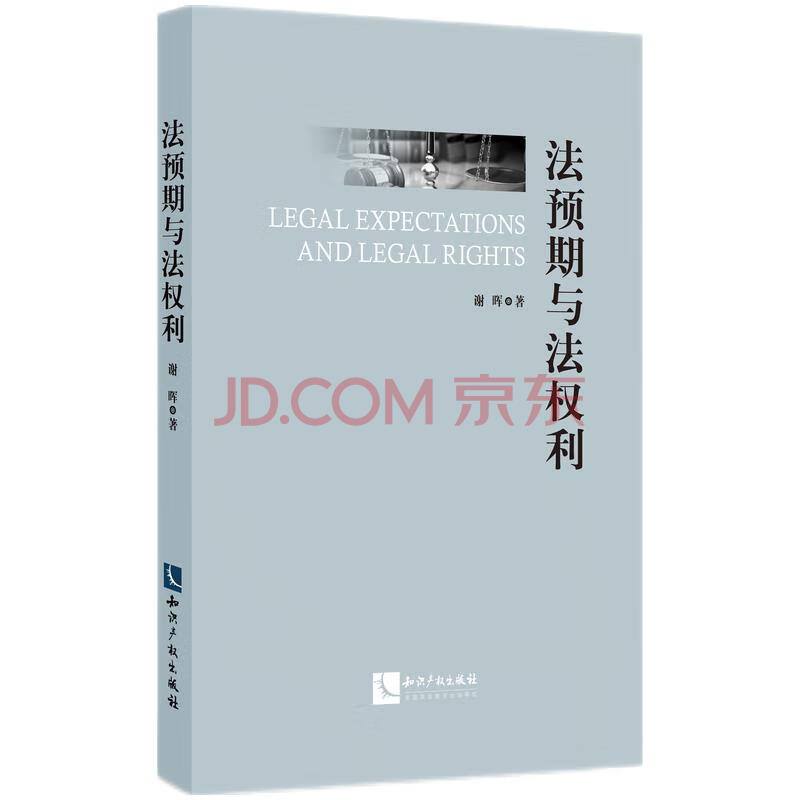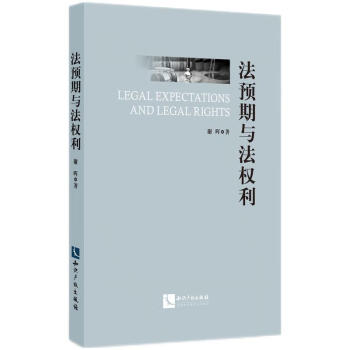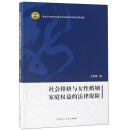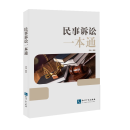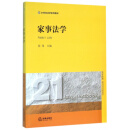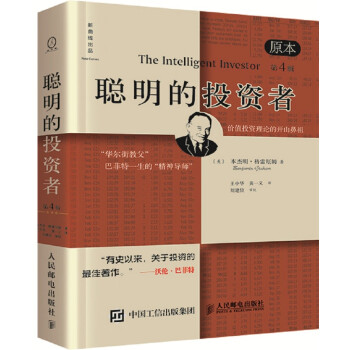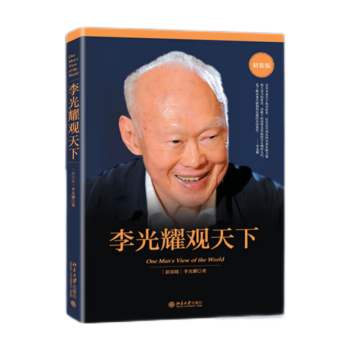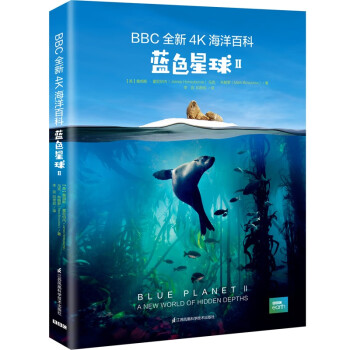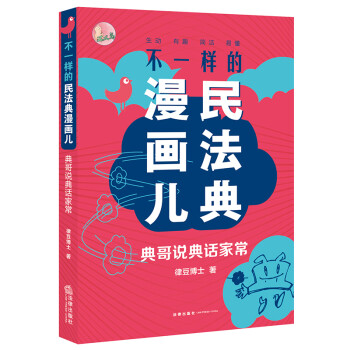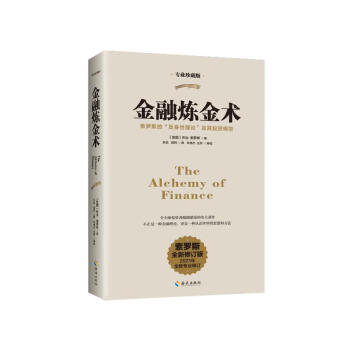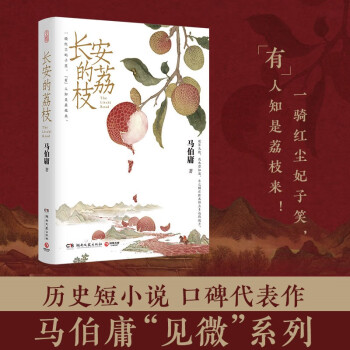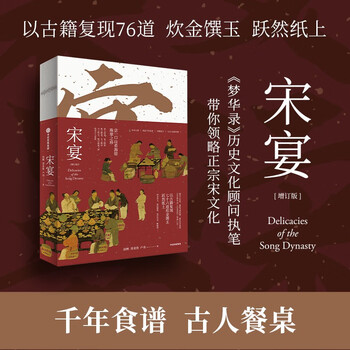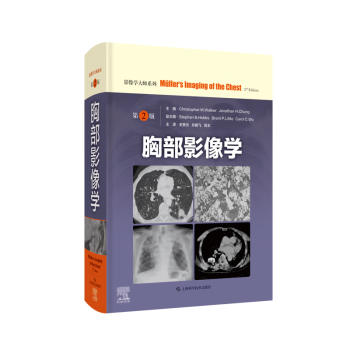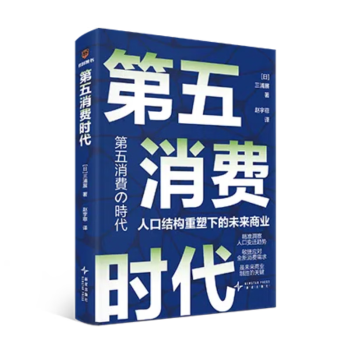内容简介
预期成就权利,法预期与法权利之间具有紧密的、内在的逻辑关联。本书是笔者近些年来就相关问题探讨成果的结集,全书客观上呈现的样貌,突出了人们对两者关联关系的印象。 本书是作者本人文集,集合了多年研究成果。
目录
目录
论法律预期性
一、法律预期性的概念
(一)法律预期性的一般概念
(二)法律预期性的相邻概念
二、法律普遍调整的预期要求
(一)普遍调整时间指向的时间预期性
(二)普遍调整空间指向的空间预期性
(三)普遍调整关系指向的关系预期性
三、法律预期的拟制设置
(一)类型化的规范,拟制预期的内容
(二)类型化的调整,拟制预期的技术
(三)类型化的归责,拟制预期的结果
四、运行中的法律预期:经验预期和逻辑预期
(一)法律经验预期
(二)法律逻辑预期
论法律预期能力的立法预设
一、何谓法律预期能力
二、通过一阶立法方法赋予法律预期能力
(一)立法中的间接经验与直接经验
(二)一阶立法方法及其任务
三、通过二阶立法方法设计法律预期能力
(一)二阶立法方法及其任务
(二)宽容原则与价值(事实)兼顾
(三)优先原则与价值(事实)识别
(四)排除原则与价值(事实)否定
四、通过三阶立法方法补强法律预期能力
(一)立法后法律预期冲突与三阶立法方法
(二)立法(前)后法律预期冲突的救济
五、通过立法的法律预期真、善、美
论法律预期目的及其规范预设
一、法律预期目的
二、免于恐惧的人类秩序预期及其规范预设
(一)人类秩序预期的基本要求
(二)秩序预期的义务规范预设
三、向往自主的人类自由预期及其规范预设
(一)自由预期的基本追求
(二)自由预期的权利规范预设
四、寻求公道的人类正义预期及其规范预设
(一)正义预期的基本追求
(二)正义预期的权力及责任(消极义务)预设
五、结论
论法律预期目的冲突司法救济的默会维度——一个默会正义的思考
一、明述的法律和默会的法律
(一)逻辑系统架构的法律明述之维
(二)修辞预设架构的法律默会之维
(三)法律预期目的之明述与默会
二、法律预期目的冲突及其司法救济中的默会知识
(一)法律预期目的冲突的强默会性质
(二)法律预期目的冲突中司法的两种面向:法律的和事实的
(三)司法救济法律预期目的冲突的方法默会
三、再申法律预期目的冲突下经由默会通向司法正义
(一)运送正义的方式:司法的基本宗旨
(二)司法的正义——“一张普罗透斯似的脸”
(三)司法正义是明述的,还是默会的
四、正视司法救济法律预期目的冲突的默会正义
论新型权利的基础理念
一、新兴权利和新型权利
(一)自发的和自觉的
(二)自然的和法定的
(三)流变(多元)的和成型(统一)的
二、新型权利概念的内在视角——教义学基础
(一)内在视角与法律教义学
(二)内在视角1:法律——立法吸纳
(三)内在视角2:裁判基础——司法吸纳
三、新型权利概念的外在视角——社会学基础
(一)新型权利创生的事实根据
(二)新型权利的可接受性
(三)规范(新型权利)的普遍化与再社会化
四、新型权利与司法关怀
论新兴权利的一般理论
一、新兴权利是“权利”吗
(一)权利研究的法律藩篱
(二)如何界定新兴权利
(三)新兴权利的“权利”属性
二、新兴权利是何种意义的“权利”
(一)新兴权利是与法律相关的概念
(二)新兴权利是法律未规定的概念
(三)新兴权利是可普遍化的概念
三、新兴权利的生成根据是什么
(一)法律遗漏与新兴权利之生成
(二)法律排斥与新兴权利之生成
(三)社会变迁与新兴权利之生成
四、新兴权利如何得以保障
(一)新兴权利的法律保障——权利推定
(二)新兴权利的社会保障——民间规范
(三)新兴权利的运行保障——纠纷解决
数字社会的“人权例外”及法律决断
一、主体性、现代社会与人权的法理
二、数字(机器)宰制、主体离场与传统人权法理之殇
(一)数字宰制、精神离场与人类思想之稀释
(二)数字宰制、行动离场与人类自由的失落
(三)数字宰制、身体离场与人类尊严的沦丧
三、数字奴役、主体性危机与“人权例外”
(一)主体之争
(二)主体竞争与人类主体性之黄昏
(三)数字奴役与“人权例外”
四、智能社会中“人权例外”的法律决断
(一)智能社会中人权的双重倾向
(二)“人权例外”:法律保护人权的难题
(三)“人权例外”:法律救济人权的限度
(四)“人权例外”:保护和救济之外的法律决断
论紧急状态中的权利扩展
一、紧急状态之类型与权利之克减和扩展
(一)外力救济的紧急状态及权利克减
(二)自力救济的紧急状态及权利扩展
(三)混合救济的紧急状态及权力和权利的平衡
二、紧急状态中权利扩展的场域
(一)因紧急状态中的政府失灵——救济不能
(二)因紧急状态中的权力失当——救济不当
(三)因紧急状态中的权力不及——救助无力
三、紧急状态中权利扩展的内容
(一)紧急自救权——积极自救与消极自救
(二)紧急避难权——个体避难与集体避难
(三)紧急救助权——紧急助他与紧急互助
(四)紧急抗辩权——紧急请求与紧急抗拒
四、紧急状态中权利扩展的方式
(一)依法扩展——法律授权
(二)推定扩展——法律默许
(三)责任扩展——道义迫使
论权利推定的类型和方法
一、“剩余事实”与权利推定的方法之维
二、权利推定:不仅是理念
(一)面对事实的行动
(二)义务推定的不能
(三)推定道德义务:自设义务即权利
(四)“剩余事实”的权利推定
三、权利推定的两大类型
(一)日常生活中的权利推定
(二)纠纷解决中的权利推定
四、权利推定的逻辑方法
(一)通过演绎的权利推定
(二)通过归纳的权利推定
五、权利推定对法治之法的补救
前言/序言
代序:预期成就权利
众所周知,对未知事物的恐惧,是经常导致人类神魂不定、忐忑不安(心理),进而引发人类畏首畏尾、裹足不前(行为)的主要原因。而所谓未知,一言以蔽之,就是人们在交往行为时,对未来的事物缺乏基本预期。古人云:“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言前定则不跲,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疚,道前定则不穷。”这说明了预期在人类交往行为中的极端重要性。当预期与否直接决定人们交往行为成功与否时,预期本身的价值无论怎么评价都不为过。
那么,什么是预期?要言之,预期就是人们对其行为必然导向其所希望看到或得到的结果的事先判断和把握。有了这种判断和把握,人们才能做好行为或不行为,以及倘若行为则如何行为的物质、精神和行动准备。所谓“不打无把握之仗,不打无准备之仗”,说的正是这个道理。可见,有无预期,是有无把握、有无准备的基本前提。
如果把预期置诸人们交往行为的一般规范——法律领域,则可以认为,人类史上的所有法律,都肩负着给法律调整下的人们的交往行为,甚至思想言论创造预期的职能。换言之,法律调整的特点,就是给人们以一般、普遍、统一和平等的预期,这是其作为一般调整区别于个别调整的基本特点。说到个别调整,人们不禁会想到春秋战国之际,叔向和子产的一场争论:
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犹不可禁御,是故闲之以义,纠之以政,行之以礼,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为禄位以劝其从,严断刑罚以威其淫。惧其未也,故诲之以忠,耸之以行,教之以务,使之以和,临之以敬,莅之以强,断之以刚。犹求圣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长,慈惠之师,民于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祸乱。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而侥幸以成之,弗可为矣。
叔向在致子产信中的上述观点,人们尽管可能在多个视角加以阐述,如有人说叔向所追求的是实质正义(公正),从而不同于成文法对形式正义的特别追求。不过在笔者看来,叔向的上述观点,与实质正义之追求,毫无关联。他不过是在主张更有利于主事者的前提下,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让普罗大众不要因为成文法统一标准的公布而获得预期,并根据这种预期给主事者“找麻烦”而已。再如,有人认为叔向的观点,有点类似于判例法。诚然,叔向的时代,我国尚处在“判例法时代”,且叔向在信中也确实描述了这种“类案异判”、议事以制的情形。可这种类似的、一以贯之的实践机制,至今在我国仍未引导出一种判例法来,因此毋宁说他所奉行的,是赤裸裸的权力至上、方便权力、个别调整,进而允许当权者随心所欲罢了。叔向的观点,与实质理性,与判例法,都毫无关系。还有人认为,叔向在此明显倾向于秘密刑法(罚)观,反对刑法(罚)的统一公开,以免为人们据理力争留下口实。这一观点,笔者是赞同的,但学者们所关注的,是叔向观点的实践功能,并未引出一个学理性的结论。因此,笔者愿在此适度展开对叔向观点的看法。
笔者认为,叔向所陈述的情形,在法学理论上观察,可谓典型的个别调整。个别调整就是一事一议,“议事以制,不为刑辟”。一切统一的、公开的成文法,都必然倡导普遍调整、一般调整、统一调整。在实践中,这种调整虽有利于公平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但对当权者“任使”民众而言,显然添加了负担。只有在人们普遍地“法律蒙昧”的状态下,一事一议地解决问题,才能方便地落实、实践当权者所倡导的那种“案结事了”,避免人们“刀锥之末,尽将争之”。因为,这不但会导致高昂的成本支出,而且一旦裁判不符合成文法的规定,引致上诉,势必会给有司增加物质上和名誉上的负担——把其所负责的案件,没有一锤定音般地裁判、执行下去,对有司而言,总不是一件光荣的事。
然而,这种个别调整无论在公权(特别是司法权)还是私权行使上的代价都是巨大的。具体表现为:
第一,预期不能,意味着秘密用权(公权)。从而所有公务行为,尤其司法裁判行为都是秘密的,因此,对当下进入司法的纠纷,究竟如何裁处,当事人一片混沌,即使主事者,也没有十足的把握,很难做到胸有成竹。
第二,预期不能,意味着只会有司法专横。司法者没有可坚守的法律一般标准,因此,裁判只能跟着感觉走。表面看来,它赋予司法以主动性、能动性和积极性,实际上,却让双方当事人成为法(判)官任意吆三喝四的对象。
第三,预期不能,意味法官的“类案异判”。法官不可能采取类案类判,更不可能实现类案同判的司法正义。其裁判只能根据权力之间的角力、博弈行事,从而权力的“脸色”,往往就是法官裁判的最高“法律”。
第四,预期不能,更意味着人们交往行为的混乱。因为缺乏标准,交往行为也就无所适从。其进一步的结果,自然是社会的失序。社会一旦失序,无论于公于私,都面临着社会风险陡增的结果。
因此,个别调整的成本是事倍功半的,代价是劳而无功的,结果也是扑朔迷离的,原因就在于它不能给人们创造预期,除了行为选择的左右为难、无所适从外,更有内心判断的狐疑不定、忐忑不安。试想,当人们在心理和行为两方面都受困于不确定的干扰时,如何能放松身心、一往无前地追求其理想的事情——无论生活,还是工作?所以,只有确定,才能让主体获得权利感,让主体能够心无旁骛、专心致志、胜任愉快地投入其想做的事,追求其想过的生活。
这样看来,预期性必然意味着与个别调整相对的普遍调整。法律就是一种普遍调整机制,也是最有代表性的普遍调整机制,从而也是最有效的预期机制。诚如马克思所言:
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在这些规范中自由获得了一种与个人无关的、理论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存在。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
法律的如上属性,正是确保其预期性的内在决定因素。在一定意义上,法律的普遍调整机制和其预期性之间,是前提预设与运行—后果归结的关系,从而是调整规范与调整过程及其结果之间的关系。只要具有普遍调整功能的法律得以运行、贯彻和落实,就必然意味着其预期性如影随形般地展开。不但如此,法律预期还成就着法治,特别是它成就着人们的法权利。何以法预期成就法权利?对此,笔者将从如下五方面稍加展开:
第一,法预期决定主体权利选择的能力。权利的本质是选择,从而其价值必然通向自由。选择的空间有多大,自由的空间也就有多大。但选择本身,却并非一蹴而就的,反而越是自由选择,越考验着选择者的选择能力。没有预期的选择,更是劳神劳心的事。法律作为人类交往行为的规范,作为人类最重要的预期方案,对包括权利和义务、权力和责任在内的所有人类行为的选择,都通过规范方式明确了预期机制,但由于义务、权力以及责任在法律上选择的空间很小,甚至大体上是严格法定的(所以才有“权力不得推定”“义务应当履行”“责任必须落实”的禁止或强制要求),因此,人们面对这些规范,要依法选择,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可权利即便是法定的,它的规范性质也决定了其只能在选择中予以行使。可见,法定权利的背后,必然是事实权利的意定。法律能够更加精准地赋予人们以预期,且人们能够娴熟地掌握法律的预期,意味着其权利选择能力因为“预期准据”的明确而增强和提升。这无论对作为权利运用者的公民、法人而言,还是对作为社会管理者的政府、非政府组织而言,都意味着行为选择能力,特别是权利选择能力的提升;意味着法律的普遍调整和普遍预期,对主体选择行动能力的加持。
第二,法预期保障主体权利选择的正确。这一点,应是前一点的实践性展开,即人们权利选择的正确程度,与其权利选择能力的高度成正比。就一般情形而言,权利选择的能力越高,则其选择的正确程度越大;权利选择的能力越低,则其选择的正确程度越小。虽然法律预期绝不意味着人们的权利选择就一定准确无误,也不排除即便在有法律预期的情形下,人们在权利选择上的重大失误。但即使如此,法律预期的存在,可保障人们在权利选择时不至于太过离谱,避免或者把本不属于权利的事项,当作权利来行使,例如,父母在子女婚姻缔结中所行使的“父母之命”的“权利”;或者把本来属于权利的事项,当作义务来履行。由此可见,法律预期保障了人们权利选择的正确。古人云:“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倘若套用这一结论,则对人们权利选择的正确程度而言,完全可以说:“天不生法律,选择即迷宫。”法律预期的基本作用,就是指示人们行为的选择方向,无论是行使权利的选择还是履行义务的选择,尽量保障人们行为选择的正确性。如前所述,其中对保障主体行使权利的选择的正确性而言,其尤为重要且必要的。
第三,法预期提升主体权利运用的效率。这一点是上述第二点的逻辑延伸。法律预期是通过法律的规范性以及规范的普遍性来实现的。在技术理性视角,法律就是一种逻辑化、一般化,进而具有可普遍化的规范(操作)体系。在实质上,它是因应人的规范性而制定的一种制度事实。人的本质问题,是一切社会学科逻辑展开的前提,与规范性相关的人的本质论,就有符号本质论、文化本质论等。在笔者看来,上述人的本质理论,在实质上可以归结为人的规范本质论,因为无论文化,还是符号,都是规范性的载体。人类因为循守文化—符号这样的规范,进而创造了文明,并使自身成为能够经由文化—符号而思考和行动的文明主体。站在效率的视角,依循文化—符号的结果,使人类行为能够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倘若说文化—符号本来就具有规范性,甚至它就是人们交往行为的规范的话,那么,建立在文化—符号基础上的法律,就是对规范的进一步提纯,可谓是规范的规范。这种规范,和文化—符号相比,给人们以更高、更准确和更稳定的预期。因此,人们按照法律预期的权利选择,在其按照文化—符号行为时事半功倍的基础上,可进一步强化权利选择的效率,节约权利行使的成本。
第四,法预期强化主体权利行使的边界。尽管权利意味着人们的自由选择,但正像自由是有边界的一样,作为自由的规范设置,权利也是有边界的。在一定意义上,权利就是自由的规范边界。或以为,义务是权利的边界,决定了义务才是自由的边界。因此,权利只是自由的规范内容,而不是其规范边界。初看之,确实如此,但作为自由的内容,权利范围内的自由,都是合法且受法律保护的,跨越权利边界的“自由”,是非法且逻辑上必将被法律所取缔的。因此,这并不意味着权利不能充当自由的边界——尽管义务是权利、自由的最终的和不可逾越的边界。可以说,权利既是自由的规范内容,但同时作为一种规范事实,它本身就意味着边界,因为规范就是边界。法定的权利规范,不但确定了主体交往行为的自由内容,也因此使得自由“固定化”。所谓“固定化”,就是边界的意思。正是权利本身之于自由的边界规定性,决定了人们根据法律预期行使权利时,就必然意味着对自由,也是对权利边界的循守,只有在法律预期内的权利行使,才符合法定的权利边界,并受法律保护,从而是利益的取得方式。超越法律预期的“权利”行使,不但跨越权利和自由的边界,而且是其利益被剥夺的法定事由。不难得见,预期是如何强化主体权利行使的边界的。
第五,法预期促进国家对权利的公共保障。任何法律预期,不仅是规定给普罗大众的,而且照例是规定给公权主体的。所有公权的产生及存在的合理性,取决于具体的个人总是难以愉快地解决人们所面对的复杂社会事实,从而需要强有力的第三方出面予以解决。例如,调解的出现,就是纠纷主体之间不能自我解决纠纷,人们希望由第三方出面帮助解决纠纷的需求结果。司法的出现,就是即便有普通的第三方出面,仍然不能解决主体间的纠纷,从而人们希望国家公权主体出面予以解决的需求结果。行政的出现,则是当主体面对自然灾害、国家战争等不可抗力以及诸多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的难题,不能自主地解决时,希望更权威的公共主体出面予以解决这一需求结果。所以,国家权力来到世间,服务于普罗大众的权利需要,满足对公共利益和秩序的强有力的保护,是其天经地义的使命。而在对法律预期的把握上,一方面,公权主体比私权主体更具有信息、知识、智慧以及公共设施方面的优先性。另一方面,公权主体的法律预期获知,其目的在于对私权主体提供权利选择和行使的公共保障——当私主体的权利行使溢出法律边界时,及时提供提醒义务(职责),并对那些业已给他人、社会和国家带来损失的权利行使行为,予以处置并提供公共救济。这样一来,法律预期被国家公权主体所掌握,其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对权利行使提供公共保障——无论是公权根据法预期对其提醒、警告还是制裁。
综上所述,预期成就权利,进而法预期与法权利之间具有紧密的、内在的逻辑关联。本书内容,是笔者近些年来就相关问题探讨成果的结集。尽管其内容不是专门探究法预期与法权利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但全书结集后客观上呈现的样貌,突出了人们对两者关联关系的印象。因此,特作此序,就是为了方便读者们对法预期与法权利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有一个大概的、框架性的认识。
是为序。
谢 晖
作于清远小居
2024年12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