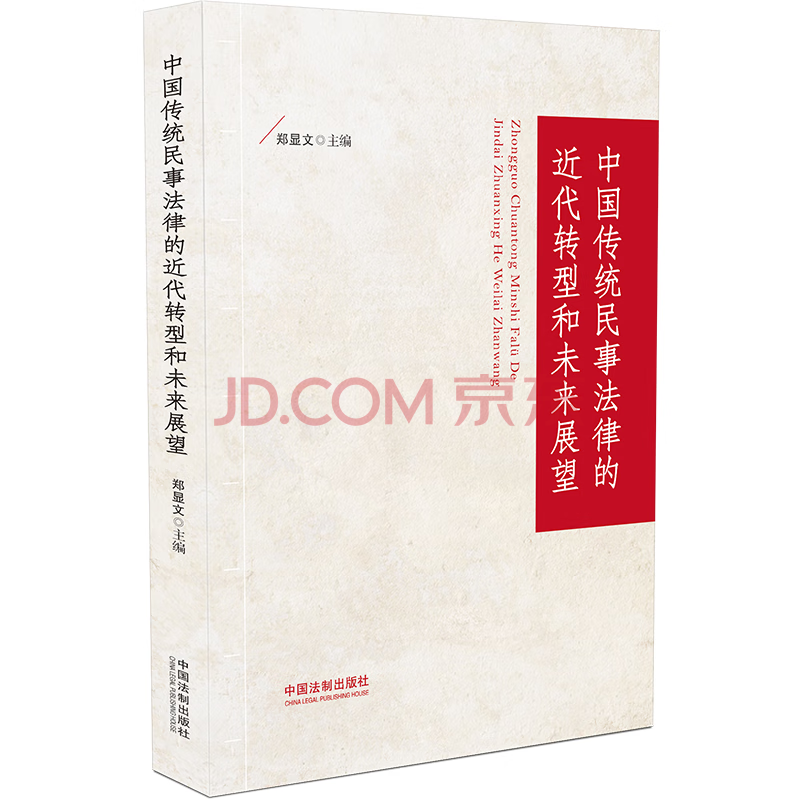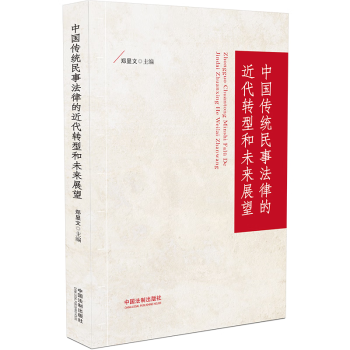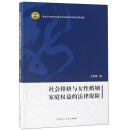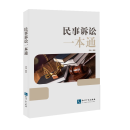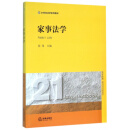内容简介
《民法总则》公布后,为了深入探究中国民法发展演变的历史,更好地了解新颁布的《民法总则》的立法精神和法律内容,2017年11月4日,在上海师范大学成功举办了“中国传统民事法律的近代转型及未来展望”学术研讨会。此次学术研讨会汇聚了中国法律史学界和民法学界众多的专家学者,大家围绕着中国传统的民事法律制度、中国近代民法的转型和当代中国民法的发展这三个主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终形成了这部学术成果。本书主要围绕着三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论述,一是关于中国传统民事法律的探讨;二是关于中国近代民法转型的研究;三是关于现代民法未来展望的探讨。以期为将来法律史学和民法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目录
上篇 中国传统的民事法律探源
古今民法观念批判
论中国历史上的“并嫡”与“兼祧”现象
汉代继承问题刍议
再论东汉正卫弹的性质
宋代《理欠令》的成立及债法的变化
元代官田侵害与民田交易纠纷的法律规制
中篇 中国近代民法的转型
中国传统契约文本形式中的守信及其近代转型
从大理院审理的祭田案件看民事权利在近代中国的生成
从湖北汉阳《罗氏宗谱》看清末民初中国乡绅的法律近代化
民初大理院援用习惯所考量因素初探
“《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寻踪:无法可守的守法主义?
传统民事习惯对《中华民国民法·物权编》的影响
民国时期江西地区的民间谱牒纠纷及其解决机制
民国时期民间借贷的利率习惯与司法适用
从女子财产继承权的确立看民国时期民法近代化
下篇 中国现代民法的未来展望
法典理性与民法总则:以中国大陆民法典编纂为思考对象
“以法治孝”的传统承继与现代转型
生活之法:村规民约规定的民事习惯
国外习惯进入国家法之情况考察
认真地对待《民法总则》第一章“基本规定”
《民法总则》第九章“诉讼时效”评析
民法典中立法目的条款的表达与设计
从民办学校法人归类看《民法总则》的创新与不足
论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在我国民法中的形成与确立
后记
试读
古今民法观念批判
赵晓耕
一、中国传统“义利观”“公私观”与西方的“私权”观与近代民法 的形成
中国古代历来重公轻私,不言私权,“权利”一词在中国古代很少使用,即便有,也常受到鄙视与不屑。不言私权并非私权不存在,只是它长期处于被忽视的地位,我国古代家族制度发达,因而“家族”代替了“个人”,“宗族或家”的共有财产代替了个人财产,私人权利和私人财产淹没和束缚在国家和宗族的阴影下。因此,虽然律令中自古就有婚姻、户役、田宅、继承、钱债、市厘等项目,但始终处于附属和次要地位,附属于刑事法规和行政法规中。民间这些大量存在和发生的民事法律关系,其实就是私权在中国古代得以存在的证明,也是中国人私权观念的体现。
西方的“私权”观在法律中体现较为明显,罗马法中的市民法便是一个以权利为本位的私人权利体系。但后人据此妄议传统社会不注重“私权”,不无可议之处。古语有“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等,该做何解?
(一)中国传统义利观与近代“私法”观念的形成
1.传统中国的义利观
民法同“利”最为相关,因此,考察中国古代的民法根本无法绕开古人对“利”的理解。而“利”在中国古代高扬道德大旗的意识形态控制下,“耻于言利”成为基本的道德戒律。因此,“利”往往和“义”结合在一起成为中国古代士大夫的主流意识、人生观或者说正统知识学中的基本问题。
“义利观”是古人对“义”与“利”(道德与利益)的基本看法,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儒家学说占主导地位的传统中国,人们的义利观是主张以“义”制“利”,以“义”节“利”。
孔子讲: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孟子说:
“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荀子也认为:
“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桀纣也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故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
儒家义利观的主要内容就是始终将宗法伦理的等级秩序置于物质利益之上,要求重义轻利、先义后利、以义生利、以道取利,见利思义。用最简短的语言来概括先秦儒家义利观的内容,应该是“重义兼利”“重义尚利”。
“义利观”在国家治理中的最大体现则是强有力地推行“重农抑商”的国策。商鞅变法特别是秦汉之后,重农抑商成为古代中国的一项根本经济政策。在中国古代社会,农为国家之大利,为国家之最适宜者,故亦为国家之大义。重农,即国家“重义”也。商为私人之利,为国家之害。抑商乃国家之“轻利”也。与之相适应,中国的传统法律在重农抑商方面也作出了许多规定。基于义利观的影响,在古人的观念中,法律只需要规定一些重大的关涉社会统治秩序,体现“义”的内容,而一向被古人看作是“细故”的民事关系则无须出现在官方制定的法律典籍之中。法律既然作为最不坏的规则,只能是“教民尚义”而非“导民逐利”。正如荀子说言:
“上重义则义克利,上重利则利克义。故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丧,士不通货财。”
古人强调天子、诸侯、大夫等要作人民表率,“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因此,在国家正统的法律典籍中不屑于提及“利”。这种“不言利”也正是古代政府所倡导的思想意识和制度设计原则:官府不言利,“官不与民争利”,希望以此达到的效果则是民不相争利,从而稳固统治秩序,实现社会无讼和谐。即便是民众为了“田宅细故”的事情而对簿公堂,也并非仅仅是主张民事权利,依然是在“义利观”的指导下约束自己的行为。往往是以“要个说法”而展开的。在正常的传统社会结构中,人们的权利是依据礼义的秩序获得的。所以,“田宅钱债细故”之争,就不仅仅是在“争利”,也是在“争义”。这就如同现实社会中的许多百姓也常忿忿地说“打官司,争的就是这个理”是一样的道理。
不仅如此,“义利观”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影响还表现为:其一,崇公抑私的法律观念;其二,平衡的权利义务关系;其三,以忠孝为核心的社会等级关系。这种道德上的义务又在法律上得到确认和强化,在很大程度上约束着人们对自身权利的认识、追求和维护。近现代民法上的交易、侵权等关系难以孕育、建立和发展,与此不无关联。因此,有学者认为“义利”关系实际上是物质利益与社会制度、规范之间的关系。但从历史经验与社会发展的要求来说,“义利”关系总是辩证的:一方面,“义”的产生源起于制“利”的需要,不具备调整利益关系功能的社会规范是不可能存在或是无意义的;另一方面,“利”的实现又必须在“义”的指导下进行,那种不能实现物质利益功能的社会规范同样是不可能存在或是可接受的。可以说“义利观”成为指导中国古代立法和
前言/序言
中国传统的民事法律制度不太发达,各个时期的民事法律规范大多散见于汉、晋、唐、宋、明、清时代的律、令、科、品、格、式、会典、则例等法律形式之中。中国古代从未制定过单独的民法典,中国古代是一个有民事法律规范而没有单独民法典的民事法律体系的时代。
从清朝末年起,中国开始借鉴西方大陆法系的民法体例,先后制定了《大清民律草案》、“民律二草”和《中华民国民法》等法典,初步构建了近代的民法体系,开启了中国法律近代化的先河。
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仿照苏联的民法体系编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民法典。虽然中国于1955年、1963年、1980年等先后起草和制定过民法典,但迄今为止仍没有颁布过一部完整的民法典。2017年3月15日颁布、同年10月1日开始实施的《民法总则》,标志中国民法典的立法逐渐走上了正轨。
为了深入探究中国传统的民事法律制度,对中国民法近代化的进程进行反思,为了对《民法总则》进行全面解读,为了对正在编纂的民法典中的债法、物权、婚姻、继承等法律篇目提供有益的借鉴经验,2017年11月,在上海师范大学召开了“中国传统民事法律的近代转型及未来展望”学术研讨会,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三十余篇,这本学术文集就是在上述成果的基础上编纂而成的。
“中国传统民事法律的近代转型及未来展望”学术研讨会主要围绕着三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其一,关于中国传统民事法律的探讨。主要成果有赵晓耕的《古今民法观念批判》,闫晓君的《汉代继承问题刍议》,郑显文的《宋代〈理欠令〉的成立及债法的变化》,吴海航的《元代官田侵害与民田交易纠纷的法律规制》等论文;其二,关于中国近代民法转型的研究。主要成果有李启成的《从大理院审理的祭田案件看民事权利在近代中国的生成》,春杨的《中国传统契约文本形式中的守信及其近代转型》,张小也的《从湖北汉阳〈罗氏宗谱〉看清末民初中国乡绅的法律近代化》,龚汝富的《民国时期江西地区的民间谱牒纠纷及其解决机制》等论文;其三,关于现代民法未来展望的探讨。主要成果有朱庆育的《法典理性与民法总则:以中国大陆民法典编纂为思考对象》,高其才的《生活之法:村规民约规定的民事习惯》,于飞的《认真地对待〈民法总则〉第一章“基本规定”》,刘颖的《民法典中立法目的条款的表达与设计》,石文龙的《论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在我国民法中的形成与确立》等论文。通过会议期间的学术交流,各位学者充分认识到不同专业、不同学科之间学术交流的重要性,大家一致认为这次会议的成功举办开拓了学术研究的视野,为将来法律史学和民法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法律史学是一门交叉性的学科。我们殷切希望法律史学界能够与法理学、民法学、刑法学、诉讼法学等不同法学学科之间展开密切的交流,能够与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展开更广泛的对话,从而提高法律史学研究的学术质量,为当前我国的法制现代化建设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