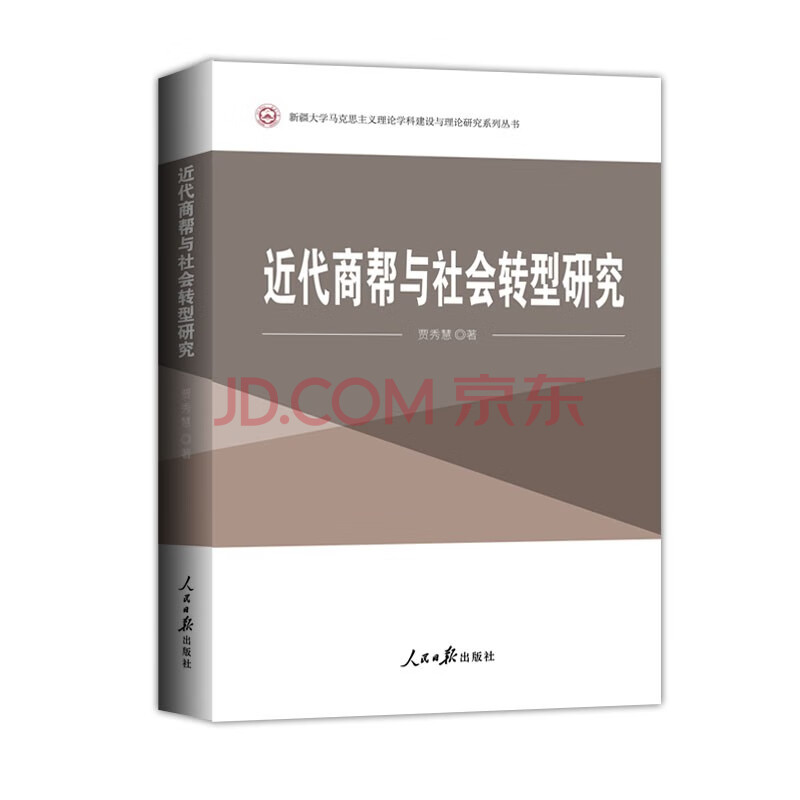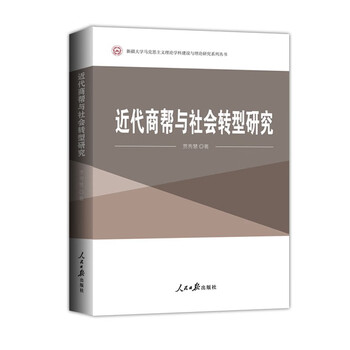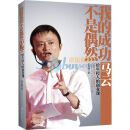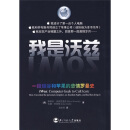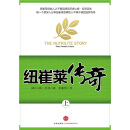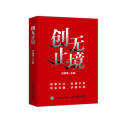内容简介
《近代商帮与社会转型研究》是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2BZS089)的结项成果,同时也是 “天山英才” 培养计划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和新疆文化名家项目(2023WHMJ012)的阶段性成果。
《近代商帮与社会转型研究》是探讨近代商帮群体影响并推动社会转型的学术著作,兼顾社会史与经济史视角,剖析其在近代社会变革中的角色和作用。该书先梳理全国近代商帮的崛起与演进,再聚焦 19 世纪 80 年代左右从天津、晋陕、甘川、湘鄂、河南等地到新疆的商人形成商帮后,在社会转型中的独特作用与影响,从商业活动、地缘组织(近代会馆)、与近代商会的关系、对中华传统民俗文化的传承及对社会转型的推动等维度展开叙述。
书中通过翔实史料与生动案例,探讨商帮如何以商贸活动跨越地理界限连接内陆与边疆,加速商品和信息流通,揭示其在近代中国社会大变革中的崛起及对地方乃至全国经济结构的重塑力量,为社会转型研究提供宝贵经验样本。
目录
导论/001
第一章 近代商帮的崛起与演进/011
第一节 近代商帮的兴起背景/013
第二节 近代商帮的主要类型与特点/020
第三节 近代商帮的发展历程/030
第二章 近代新疆商帮的产生与发展/033
第一节 商帮在新疆的发端(1759-1875)/035
第二节 商帮在新疆的兴起(1876-1911)/049
第三节 民国时期新疆商帮的发展(1912-1949)/086
第三章 商帮的商业活动/103
第一节 商业活动/105
第二节 商帮的内部社会结构/143
第三节 商帮的商业文化/154
第四章 商帮与少数民族商民的交往/165
第一节 近代新疆的少数民族商业/167
第二节 语言及风俗习惯方面/174
第三节 二者共同抵御外国经济侵略/177
第四节 二者共同合作经商及从事慈善事业/185
第五章 商帮的地缘组织——近代新疆的会馆/193
第一节 各商帮在近代新疆设立的会馆/195
第二节 会馆的内部组织及运行/210
第三节 会馆的功能/214
第六章 商帮与近代新疆商会/227
第一节 商帮与近代新疆商会的成立/230
第二节 商帮与新疆商会的内部组织运作/235
第三节 商帮与新疆商会的经济活动/262
第四节 商帮与新疆商会的社会活动/277
第七章 商帮对中华传统民俗文化的广泛移植与传承/297
第一节 商帮与中华传统节日文化/301
第二节 商帮与中华传统工艺文化/306
第三节 商帮与中华传统饮食文化/311
第四节 商帮与中华传统戏曲文化/318
第五节 商帮与中华传统游艺文化/323
第六节 商帮推动新疆多民族间文化的交流交融/324
第八章 商帮与新疆的近代化/333
第一节 商帮自身的近代化/336
第二节 商帮促进新疆城市建设的近代化/341
第三节 商帮促进新疆文化建设的近代化/354
第四节 商帮促进新疆社会生活的近代化/362
第九章 近代商帮:社会转型的强劲推手/391
第一节 经济层面/393
第二节 社会层面/397
第三节 文化层面/399
参考文献/405
后记/421
试读
商帮,是近代中国经济舞台上最为活跃、最受瞩目也最具实力的商贸活动单位,以其地域性、行业性和组织性的特点,在促进经济发展和推动社会近代化转型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从明清时期的晋商、徽商、陕(秦)商、鲁商,到近代的粤商、浙商等,商帮不仅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区域经济的繁荣,还赋能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对于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转型产生了深刻影响。
第一节 近代商帮的兴起背景
近代商帮的兴起,其背后原因复杂多样,但主要可归结为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增长、交通与通讯条件的显著改善,以及政府政策与制度的积极扶持。
随着国内外市场的逐步开放和扩大,商品流通的需求日益增强,为商帮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交通与通讯条件的改善,使得商品运输和信息传递更为便捷,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商业效率。
同时,清政府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商业的政策和制度,如放宽商业限制、鼓励民间资本投入等,为商帮的兴起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保障。这些因素共同作用,推动了近代商帮的蓬勃兴起,成为中国商业史上的一段辉煌篇章。
一、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增长
近代以来,随着国内外市场的不断扩大,对商品的需求也日益增长。一方面,国内城市化进程加速,人口集中,消费能力增强,为商品经济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国际贸易的拓展,使得中国商品得以走向国际市场,进一步刺激了商品生产。这种市场需求的增长,为商帮的兴起提供了契机。
商帮形成于明清时期,在鸦片战争后发展迅速,其发展变化始终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大变革、大动荡,是在西方势力强行侵入、中国传统的封建集权政治继续起作用的复杂背景下展开的。长期以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社会生产的主要形式。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具体表现为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即耕与织的结合。这种耕织结合的基本经济单位是家庭,主要保障了衣、食这两种人们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的生产结合。人们生产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自给,只是在自用有余的情况下,才拿去交换,由于其数量有限,国内市场也不可能有很大发展。直到鸦片战争以前,这种自给自足的经济形式,仍然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虽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但在社会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商品经济和国内市场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随着商品生产的不断壮大,它有力地推动了交通网络的扩展和商业城市的繁荣。商品流通需求的增加促使交通设施不断完善,道路、水路等交通方式得到了显著的发展,使得商品能够更快速、更广泛地流通到各地。同时,商品生产的繁荣也促进了商业城市的兴起。这些城市成了商品交易的中心,吸引了大量的商人和资本,推动了城市经济的蓬勃发展。可以说,商品生产的发展是交通和商业城市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商品经济的发展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前提。一般认为,从明朝中叶以来,中国在一些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到清代中叶以后,这种资本主义萌芽又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到了19世纪40年代,这种独立发展的进程被打断,资本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西方的一切汹涌而来,中国的社会发生了质的变化,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主权丧失,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凭借强加给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将中国变成他们的商品市场、原料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中国经济被纳入资本主义发展的链条之中,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解体。中国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思想、文化、社会主要矛盾等,都发生了鸦片战争前未曾有过的变化,与此同时,中国自身也开始向近代社会迈进。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手工业特别是手工棉纺织业的没落和改组,自然经济的解体,使中国农民从手工业品的生产者变成了消费者,而城市的手工业者则成了剩余的劳动者和商品生产者。这也为中国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客观条件。近代工业产生并发展起来,随之而来的是农产品商品化的普遍发展,农产品的商品化是整个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农产品原料的掠夺,促进了经济作物商品化的进一步发展,以海关统计的丝、茶、豆类、棉花、油类、烟叶的输出量为例。
同时,粮食商品化也有发展。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说明了生产关系的变化。晚清时期,中国的生产形态从自然经济走向商品经济。
甲午战争以后,中国的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帝国主义列强加紧瓜分中国,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力图独占市场,经济侵略活动已不只是商品输出,资本输出也不断增加。为了扩大商品和资本输出,列强攫取了在华开设工厂、修筑铁路和开采矿藏的权利,帝国主义在华资本迅速扩张。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但并没有改变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因此也不可能改变由外国资本控制的中国对外贸易模式。民国初期的对外贸易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一时期,对外贸易继续增长。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发生了一定变化。由于西方列强忙于战争,无力向中国大量倾销棉纱、棉织品等消费品,进口额有所下降;而出口商品除丝、茶继续停滞外,其余商品大都增加,出口值有较大增长。甲午战争以来持续增长的贸易入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降到了较低的水平。由此可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对外贸易方面,中国的出口增加了,进口则相对减少了。
民国初期,国内市场的扩大也是很明显的。造成国内市场扩大的因素主要有:进出口贸易的增加;城镇和非农业人口进一步增加,由1894年的3300万人增至1920年的4400万人①,商品需求大量增加;农产品进一步商品化;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国内近代工业的兴起和发展;交通运输业和金融信贷的近代化。生产、流通和资本运用,三者互为促进,造成了商品生产的发展和流通的扩大。这为商帮的崛起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交通与通讯的改善
交通与通讯的改善是商帮兴起的重要条件。近代以来,随着公路、水路、铁路等交通网络的逐步完善,商品流通速度加快,物流成本降低,为商帮的跨区域经营提供了便利。同时,电报、电话等通讯工具的出现,使得商帮能够迅速获取市场信息,调整经营策略,提高市场竞争力。
明清时期,随着封建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商业城市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
明代中后期,全国交通条件得到大幅度改善,有利于大规模远距离的商品贩运,从而推动各地商帮的兴起。明代山河一统,幅员广阔,水陆畅达,为大规模的商品流通提供了极为有利的交通条件。为了巩固边防,明代又特别注意北部及边防路线的修建。尤其在永乐时期,为了对付蒙古势力,便利军队的往来与粮饷辎重的输送,修建了许多道路,使北边与内地的交通更加便捷。到明代中后期,全国各地的水陆交通较前大为发展。在这些商道上,商品流通极为频繁。伴随着道路的畅达,商品流通日益兴盛繁荣,商人需要以群体的力量,集中巨额资金,展开经营活动,以获取规模效应,增加实力。因此,交通条件的改观,大规模的商品流通,推动着商人们结成群体。
进入晚清以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初步发展,沿海沿江通商口岸兴起,交通运输获得迅速发展。19世纪70年代后,洋务活动进入办工厂、开矿山、修铁路以及举办轮船航运、电报通讯等民用工业更为广阔的新阶段。洋务派在兴办军事工业的基础上,又进而大力创办民用企业。
前言/序言
《近代商帮与社会转型研究》是一本深入探讨近代商帮群体如何影响并推动社会转型的学术著作。该书以近代商帮为研究对象,兼顾社会史与经济史的研究视角,详细剖析了他们在近代社会变革中的角色和作用。
本书首先梳理了全国范围内近代商帮的崛起与演变,然后聚焦于近代从天津、山西、陕西、甘肃、四川、湖南、湖北、河南等地来到新疆的商人们,约于19世纪80年代形成商帮后在近代社会馆中的独特作用与深刻影响,从商帮的商业活动、商帮的地缘组织——近代转型、商帮与近代社会、商帮对中华传统民俗文化的传承、商帮对近代社会转型的推动作用等维度,为读者展开了一幅细腻入微的历史画卷。
本书通过翔实的史料分析与生动的案例叙述,探讨了近代商帮如何通过商贸流动跨越地理界限,连接内陆与边疆,不但加强了商品流通与信息交流,还在文化观念、城市建设、社会生活、社会结构等方面引发了连锁反应,揭示了商帮在近代中国社会大变革时期的崛起历程及其对地方乃至全国经济结构的重塑力量,为研究社会转型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样本。
一、研究内容
本书所要探讨的对象——商帮,指的是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以会馆为其在异乡联络、计议之所而的一种既“亲带”而又松散的自发形成的商人群体。徽商、晋商、陕、甘、鲁商、商丘、闽商、浙商、粤商、苏商、赣商、宁波帮是中国近代商帮的典型代表,他们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近代化进程,推进了中国封建社会阶层的流动历程,为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注入了新的生命力,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推动力量。
清代,伴随着新疆的统一与开发,天津、山西、陕西、甘肃、四川、湖南、湖北、河南等地的商人们来到新疆,于19世纪70年代形成了群体组织——商帮。新疆的商帮发端于清乾庵年间统一新疆之初,形成于清光绪时期左宗棠军军复收新疆之际,19年代90年代已有相当多年,形成以地域城邦划分的“八大商帮”,即燕(其中京商少,津商多)、晋、秦、陇、蜀、湘、鄂、豫。至20世纪30年代,商帮有了很大的发展。到了到来后,特别是盛世才1942年转制向、实行反共反苏的政策后,新疆商业几乎被破坏殆尽,商帮的经营活动也遭受了重创。
近代 ^{①} ,特别是晚清民同时期,为中国从传统文化向近代社会转型蜕变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个时期,政治风云变幻,思想政治文化激荡,内在忧外患迭起。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新与旧、中与西、自由与专制、激进与保守、发展与停滞、侵略与反侵略,各种社会潮流在此期间汇聚碰撞,形成了变化万千的特殊历史景观。
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这一时期也是新疆社会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剧烈变迁时期。这一时期的新疆,政治腐败,社会动荡,战乱频仍,商业环境恶劣。自祖国被打开后,到19世纪中叶新疆已成为俄、英帝国主义的商品市场和原料掠夺地。他们拥有雄厚的资本和免税的贸易特权,严重阻碍了新疆本地工商业的发展。可以说,受国际、国内大环境的影响,新疆近代的政治、经济小环境,也是变幻莫测,喜忧参半,对商业发展不利的因素多,有利的因素少。
1865年(清同治四年)浩罕军官阿古柏入侵新疆后,在新疆实行残暴统治,各族人民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为清除外患,保卫国土,左宗棠于1876年(清光绪二年)率兵入疆,驱逐阿古柏。因军需供应困难,天津杨柳青一带的200多名货郎携带生活用品和常用中成药,经陕甘随军来援。他们一边路,一边推销,俗货“赶大营”。进“赶大营”的人,则被称为“大营客”。
从1876年7月至1878年(清光绪四年)1月,清军仅用了一年半时间,就消灭了阿古柏政权,收复了除伊犁以外的新疆所有地区。战后,新疆的社会秩序急需恢复。为此,在19世纪末,清政府通过1884年(清光绪十年)新疆建省和以“建省”为中心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以及20世纪初在新疆推行的“新政”(1901—1911),重新规范了新疆的政治、经济秩序,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整合,对新疆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促进了新疆社会的一体化。
在经济领域,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奖励实业、鼓励贸易、复兴商业。它的实施推动了新疆境内民族资本的萌芽,使民族工商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就是在这种社会大背景和经济基础之上,“赶大营”的天津小商贩在战后颇受朝廷照顾,加之经营有方,逐渐形成以迪化为中心,遍及新疆各地的规模庞大、财势雄厚的“天津商帮”,俗称“津帮”,成为新疆近代商业发展的奠基者。津商从津京等地采购货物,并将新疆的土特产羊毛、肠衣、皮革、棉花、中药材等运往关内,沟通了新疆与中原的物资交流,同时也引来了全国各地商贾对新疆的投资,逐步形成了按地域划分的“八大商帮”。
商帮人士不远千里来到新疆,把这里作为自己的第二故乡,不畏艰难,潜心经营。其具有合股经营、重视商铺字号的命名、注意人际关系培养等一些共同的经营特点。商帮中的津商执新疆商业之牛耳,其经营上的独到之处有:(1)十分注意店堂与门脸的布置点缀。(2)重视店员的形象与素质。(3)从商品结构看,他们经营的商品品种繁多、种类齐全,基本满足了社会各阶层、各民族的需要,小到土特产,大到土地、坎儿井。从经营范围看,津帮从事的百货业、食品业、蔬菜业、中药业等,都是与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行业。(4)从商品流通渠道看,津帮一些大商号以“迪化为中心,天津为总汇”,分号不但遍及天山南北,而且上海、北京和全国各大商埠都设有他们的代办机构。(5)较其他各商帮来看,津帮在资金周转方面更为便利。
商帮的内部社会结构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较强的凝聚力。首先,八大商帮在生意经营运作上基本都属于家族式经营,它成为商帮创业初期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选择,也对商铺顺利度过艰难的创业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次,商帮从置货、销售到资金回笼,实行的是一条龙式的区域经营。再次,近代新疆的商帮有自己的商业行规并严格遵守,如账簿记载明晰清楚、恪守信用等。复次,在婚姻关系中,商帮大多是同乡通婚,有共同的文化背景,如生活习惯、习俗、乡音、乡情等,家庭关系较稳定。最后,商帮内部的社会分层中,发生密切社会关系的阶层,特别是处于强势地位的阶层始终持有发展良好关系的心愿,如老板对工人、经理对店员等,使得该群体内部各阶层的相处基本良好。
商业文化是能够体现商业价值观念的文化指导思想和与之相对应的规范化制度的总称。商业经济的发展,推动着商业文化的发展。反过来,商业文化的发展又促进了商业经济的发展。两者紧密相连,互相推进,发挥着商业文化功能的作用。近代新疆的商帮在长期的商业实践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商业文化,吃苦耐劳、诚实守信、富于创新、社会责任感强是其商业文化的精髓。他们信奉的童叟无欺、言无二价、追求品质等经营理念,是克敌制胜的法宝。
新疆属于多民族聚居区,近代商帮在经商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与少数民族商民发生接触、交往、交流。商帮与少数民族商民的交往,主要有:(1)相互学习语言、互相尊重风俗习惯、逢年过节互访祝贺。(2)团结一致,紧密合作,共同投资设厂以挽权利,并肩抵抗外国经济侵略。(3)共同合作经商及从事公益、慈善事业,推动了本地的经济发展,造福了各族人民,加强了新疆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这些友好往来都增进了民族团结,强化了新疆各族人民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的心理认同感。
商帮通过设立同乡组织,也是地缘组织——各省会馆,在扶贫济困、调解纠纷、办理公益事业、传承民族传统、弘扬民族文化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新疆会馆产生的基础不同于内地,它不是来源于科举制度的附属组织和官场生活的余续,而是内地迁民求生存、图发展、互助共济的社会组织。尽管新疆会馆产生的时间较内地晚,然而其社会作用和历史影响却远远超过其他地区。它作为一种重要的民间团体,在补充国家管理和调节社会生活,维护行业、商业和同乡、民族利益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新疆会馆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尽管存在一定的封建落后性,如它的建立与封建迷信活动紧密相连;会馆既是成员会集议事之地,也是其共同祭神的场所;各个会馆无不拥有自己的保护神,每遇保护神的诞辰日,还要举行隆重的迎神赛会,以祭祀祝福;另外,会馆以同乡为结合纽带,也体现了狭隘的地域观念和封建宗法关系。但不可否认的是,新疆会馆内部的选举制度,如会首、理事均经选举产生,具有近代特征。同时会馆以其独特方式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和边疆开发建设、繁荣,对全面推广、传播中原社会传统文化和推动新疆经济繁荣、民族融合、国家统一,对稳定边疆民心和巩固全民内聚力,都产生了巨大的社会作用。
近代新疆商会作为新疆全体商人的业缘组织,其成立是新疆商业从传统走向近代的重要标志之一。商帮在近代新疆商会的成立、内部组织运作以及经济、社会活动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新疆各级商会的绝大多数会员都是商帮人士,新疆总商会及各地县商会的会长一职多由商帮人士担任,商帮人士在商会会董(议董,1929年7月)、执监委(1929年8月—1945年2月)以及理监事(1945年3月起)等决策层面所占比例极高。商帮人士认真履行议事职责,有力促成了决议案的形成,保障了商会内部组织的良性运转。在商帮人士的带领与支持、参与下,新疆商会在联络工商、调查商情、鼓励商民兴办实业、调解商事纠纷、加强市场管理、维持市场运行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发挥过重要作用。在约束或激励商人行为和商业活动中所采取的措施及形成的规章准则,对推动新疆商业制度现代化功不可没。商帮人士在商会的社会活动中也有积极作为,主要体现在协助政府推行政令、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创办福利救济事宜等方面。可以说,商帮主导下的近代新疆商会,促进了新疆社会的近代化进程,提高了新疆社会的文明程度。
伴随商帮的活动,一个重要的后发效应就是中华传统民俗文化如节日文化、工艺文化、饮食文化、戏曲文化、游艺文化等在新疆地区得到广泛传播,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改变着新疆地区的社会风貌。
同时,商帮通过实现自身的近代化①,对于新疆城市建设的近代化、文化建设的近代化及社会生活变迁的近代化有重要的历史推动作用。特别是在促进新疆城市建设近代化、社会生活近代化方面,可谓贡献卓著。
商帮通过自己的作为,有力地推动了新疆城市建设的近代化进程。具体表现在商帮人士独资或官商合作设立市政工程和公用设施,以及推动城市功能结构的变化。如电力照明方面,津商杨元富1932年在迪化(现乌鲁木齐,下同)创办的“德元电业公司”,使电灯这种新的照明方式首次进入了迪化大十字一带普通商户的门店。后来官商合办的“新光电灯公司”取代了“德元电业公司”。商帮人士对“新光电灯公司”的成立、良性运营发挥了重要作用。商帮人士周海东(津商)、杨元富(津商)、任栋梁、韩君璧(津商)先后担任该公司领导职务。又如民间消防组织方面,近代以降,商帮人士一直是新疆民间救火力量的主要组织者。商帮人士早在1911年(清宣统三年)就在迪化设立了民间消防组织——“清平水会”(俗称“水龙局”。作为唯一的民众消防队,队长均由知名的商帮人士担任,如韩乐常(津商)、韩君璧(津商)、石寅甫(津商)、萧佩华。30年代后期在商帮人士的领导下,新疆其他城镇也开始筹设民间消防队。
商帮促进了近代教育、体育等新疆文化建设领域的近代化。在上述新疆文化建设领域,新疆省政府起了主要作用,特别是盛世才治新的两个三年计划时期(1937—1942),在苏联和国内一些进步人士的帮助、共同努力下,这些领域有了迅猛发展,与此同时,在这些领域中仍然可以看到商帮人士积极作为的身影。在教育方面,商帮创办新式学校主要集中在杨增新、金树仁治新时期。盛世才治新时期,由于政府公办教育事业的飞速发展,商帮人士对教育的贡献就是:(1)积极为学校捐款、捐物、修建教室与校舍。(2)支持汉族文化促进会的发展。(3)推动妇女教育发展。商帮慷慨出资捐助各种近代体育活动的行为,激发了更多的人积极参与其中,促进了新疆体育事业的近代化进程。
随着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领域的变革,商帮活动有力推动了新疆民众的物资消费生活、婚姻家庭生活、休闲娱乐生活、公共卫生领域等社会生活的近代化变迁,有力改变了新疆人民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面貌。物质消费生活的变迁主要体现在衣、食、住、行等方面。婚姻家庭生活的变迁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婚姻习俗变化中婚装的西化,旧时婚俗中新娘的凤冠霞帔、新郎的长袍马褂被逐渐摈弃,随之而兴的是新娘开始穿旗袍、高跟鞋,烫发,头戴花冠,穿水红色的长纱衫(礼服),披白纱,手拿鲜花等,新郎则西服领带,穿皮鞋。商帮人士中的津商主要从事这方面的经营。休闲娱乐生活的变迁首先表现在新的娱乐方式——电影出现。电影在新疆的出现、发展与商帮人士的活动密不可分。1932年新疆历史上第一家电影院——德元电影院,由津商杨元富在迪化创办。其次,商帮人士积极资助新疆各级政府修建公园,伴随着公园的修建,公园成为公共生活的重要场所,逛公园成为人们新的娱乐方式,伴随着逛公园的活动,也使一些中华传统节日习俗得到了很好传承。新疆的第一个公园——1922年建成的迪化鉴湖公园(今人民公园),不但修建经费由新疆商帮人士集资而来,而且工程总设计师和木工也是天津的能工巧匠。公共卫生领域,政府起主导作用,但商帮在此领域仍有一定作为。主要表现为开设私立西医药店、诊所,在为民众治病的同时,还协助政府扑灭疫情。对于街道环境卫生建设,商帮人士通过出资购买卫生车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支持态度。由于近代新疆公共浴室较少,人们清洁洗浴不方便,商帮人士遂创办了一些公共澡堂,有利于培养民众良好的卫生习惯,预防疾病,强身健体。可以说,商帮人士推动了新疆西医诊疗、疫病防控等公共卫生事业的近代化。
总之,近代商帮在中国社会转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既是社会转型的推动者,也是这一过程的缩影,其活动具有鲜明的进步意义。
二、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上,主要采用传统的历史研究法,即文献学的方法。本书大量使用一手资料,如清代官修史书,清代官员的奏稿、奏议等,清末的档案,民国时期的档案、期刊、报纸、省政府公报等,中外时人的游记、考察日记、见闻录、回忆录、论著等,对文史资料、地方志、通志及统计年鉴等加以征引,甚至口述资料也着力搜集并加以利用。基于充实的史料,故论证有据,说服力较强。
由于研究内容涉及社会学、民俗学,所以尝试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进行了多角度研究。这是本书的一个重要优长之处,就是不走传统研究经济史的老路,使研究内容过于单调,而是从兼顾社会史与经济史的研究视角出发,对这一群体进行了全面梳理和多角度研究。
三、研究意义
商帮作为中国近代社会转型进程中的重要社会力量,其历史作用具有多维度的研究价值。本书系统考察了商帮群体在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中的特殊地位,不仅从商业史维度勾勒其发展轨迹,更在城市史、边疆开发史、社会生活史及文化史等多重领域揭示其深刻影响,有效拓展了近代史研究的学术疆域。
本书呈现了商帮在近代化进程中的复合型功能:在经济社会层面,他们通过资本运作、产业布局和商业网络构建,实质性地推动了市场化、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在文化传承维度,其以商道实践为载体,创造性地转化发展传统商业伦理,维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赓续脉络;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层面,商帮跨区域的经济互动客观上强化了各民族间“经济共生、文化互鉴、情感交融”的共同体联结,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注入新动力。这种兼具经济整合与文化融合的双重特质,使商帮研究成为解读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机制的重要锁钥。
本书将历史研究与现实关怀进行了有机结合,彰显了历史学经世致用的当代价值。
其一,通过实证历史维度阐释各民族“经济上相互依存、文化上兼容并蓄、情感上血脉相通”的交往逻辑,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历史注脚;
其二,以边疆开发史中的商帮活动为镜鉴,为新时代推进文化润疆工程、贯彻党的治疆方略贡献历史智慧;
其三,通过挖掘商帮的现代性基因,为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宝贵历史智慧。首先,近代商帮通过创新商业模式、整合跨区域资源和适应市场变化,为中国企业在全球化竞争、数字化转型和区域协同发展中提供了有益参照。其次,商帮的跨区域贸易网络促进了资源流动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为当今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如“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等国家战略提供了历史案例。再者,商帮的“义利兼顾”“诚信为本”核心价值观,对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和企业社会责任具有启发意义。最后,商帮文化中的“和合共生”“以商兴邦”理念,为“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文化交流与经济合作提供了本土化资源,其融合传统智慧与西方制度的经验,有助于增强中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的文化主体性。
总之,近代商帮不仅是经济现象,更是社会转型的缩影。其历史经验既揭示了市场规律与社会结构的深层互动,也为解决当前经济转型中的制度创新、伦理重构和文化冲突提供了重要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