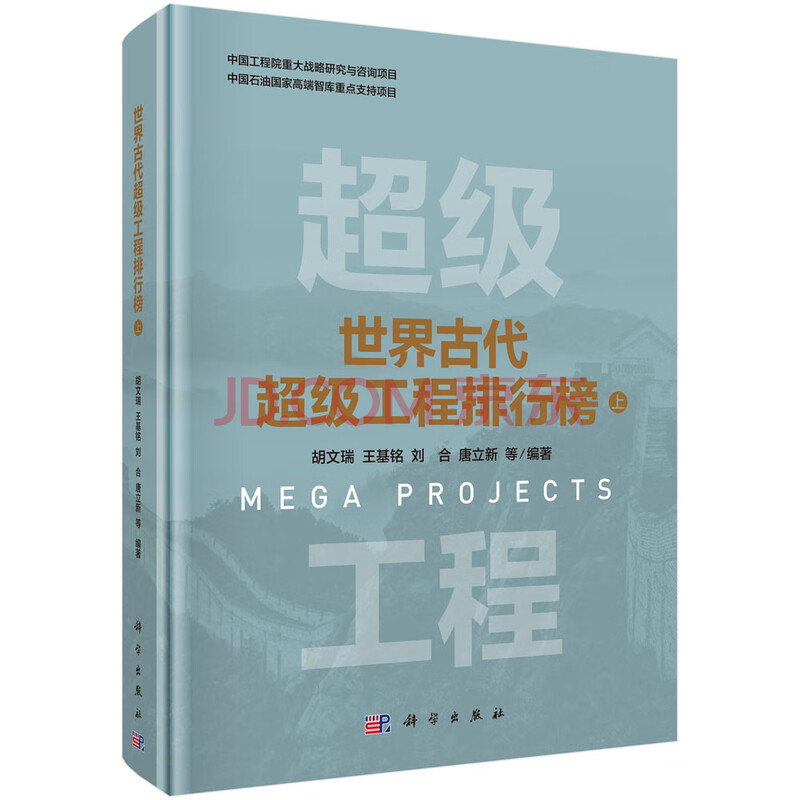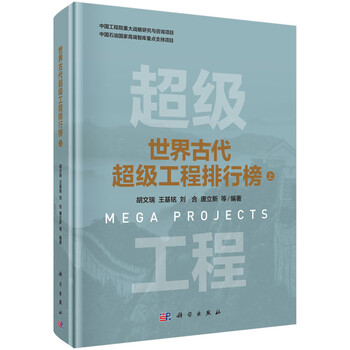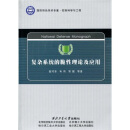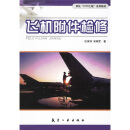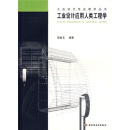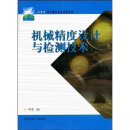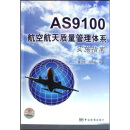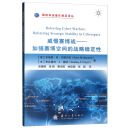内容简介
《世界古代超级工程排行榜》系统梳理了人类文明从新石器时代至工业革命前(约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1640年)*具代表性的100项超级工程,涵盖建筑、水利、交通、军事、宗教等领域,揭示了古代人类在工程规划、资源调配、组织管理和技术创新上的卓越智慧,并探讨其对现代工程实践的启示。
目录
目录
总序
前言
01 城头山遗址工程 3
02 良渚古城与水利工程 11
03 亚述古城 21
04 异教徒坝 29
05 埃及金字塔 35
06 三星堆遗址 43
07 巨石阵 53
08 石峁遗址 61
09 玛雅金字塔 69
10 科菲尼引水坝与引水渠 74
11 阿布辛贝神庙 81
12 恰高?占比尔 89
13 科迪勒拉水稻梯田 97
14 迦太基古城遗址 104
15 罗马古城 113
16 马里卜水坝 123
17 古巴比伦空中花园 131
18 苏州园林 139
19 雅典卫城 147
20 阿尔忒弥斯神庙 155
21 狄奥尼索斯剧场 163
22 *阜三孔 171
23 奥林匹亚宙斯巨像 183
24 帕特农神庙 191
25 摩索拉斯陵墓 199
26 罗马大道 205
27 亚历山大港口 213
28 佩特拉古城 221
29 罗马高架渠 229
30 亚历山大灯塔 237
31 罗德岛太阳神巨像 245
32 都江堰 253
33 秦始皇陵 261
34 万里长城 274
35 灵渠 282
36 秦直道 291
37 阿房宫 299
38 丝绸之路 304
39 汉长安城 313
40 阿旃陀石窟群 320
41 茂陵 329
42 龙*渠 337
43 罗马万神庙 345
44 坎儿井 353
45 嘉德水道桥 363
46 古罗马斗兽场 371
47 阿克苏姆巨石柱 381
48 巴米扬石窟 389
49 圣索菲亚大教堂 397
50 君士坦丁堡 407
总后记 414
试读
01城头山遗址工程
全称 城头山遗址工程,或称城头山古文化遗址
外文名称 Chengtoushan Ruins Project
城头山古文化遗址位于湖南省常德市澧县县城西北约10千米处的车溪乡南岳村境内,总占地面积约15.2万平方米,已发掘面积近9000平方米,出土文物16000余件[1]。城头山遗址所在的溧阳江河冲积平原属喜马拉雅期洞庭湖断陷盆地边缘,地面高程34~52米,相对高差20米以下,地面坡度小于3度。遗址形态略呈圆形,地势西高东低,由护城河、夯土城墙、城门、夯土台基和道路等多种建筑要素组成,城垣外圆直径340米,内圆直径325米,还有围绕城垣的护城河,宽30~50米[2]。
城头山古文化遗址是新石器时代南方大型史前古城遗址,距今7000~6500年[2]。它将中国历史上华夏民族*早的起源地域从黄河流域改写为长江中游流域[2,3]。城头山古文化遗址是迄今中国发现时代*早、文物*丰富、保护*完整的古城遗址,被誉为“中国*早的城市,,“中国**古城址,,[3’4],是世界迄今历史*早(距今6500多年)、保存完好的水稻田遗址[5]。
日本考古学家高桥学和河角龙典估算'要建成完整的城墙和护城河系统,需要劳力约47万人次,按每天人均1立方米计算,如果每天投入200个成人劳力,需要6~7年;以东北城墙和护城河估算,需要总劳力约20万人次,如果每天投入200个成人劳力,则需要2~3年才能建成。城头山城墙长1100多米、宽约13米、高10米以上,即使放到现在,也是一个不小的工程。在五六千年前生产力低下的新石器时代,能完成这样一项庞大工程,绝对是一个奇迹。
城头山古文化遗址的建造者是古代长江中游流域的先民,具体的民族和部落身份难以确定,遗址中发现的大量文物和古代遗迹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式等,对研究当时社会文化具有重要的价值。
城头山古文化遗址的发现,对史前聚落的发展、筑造城历史和技术、长江流域文明因素的形成、稻作农业的兴起和发展等重大学术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代表了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古文明的发展高度,与素称中华文明摇篮的黄河流域古文明相比,毫不逊色。
一、工程背景
结合内部发展和城垣建造的不同时期,城头山古文化遗址的使用时间从汤家岗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时期,直至石家河文化中期(距今约3800年)废弃,存续达2000多年[3]。城头山古文化遗址共经历五次挖壕与筑墙,可归纳为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7]:城头山古文化遗址**次发展是在距今6500年的汤家岗文化时期;第二次发展是在大溪文化时期,经过四次挖壕筑墙后形成底宽8~10米、高1.6~2米的城墙,墙外的壕沟开口宽12米、深2.2米;第三次发展是在屈家岭文化早、中期,距今5000~4700年,该时期整个城址内有了细部的规划,整体外形略呈圆形,由护城河、夯土城墙、城门、夯土台基和道路组成。墓葬区位于城中偏北部,形成了小型土坑墓、大型土坑墓、特大型土坑墓三种埋葬等级。
在城头山发展之初,聚落的基本形态是自然河道加上人工挖掘而形成的围沟,无论是聚落内部还是聚落与聚落之间,都表现出平等的自然发展态势。随着聚落灌溉水平的提升和精耕细作,农业发展得到保障。随着财富的不断积累,城头山的居民开始感到危机,他们开挖沟壕以增强防御能力。
城墙的堆筑与护城河的开挖是同时进行的,并将开挖护城河时所产生的土料作为筑城材料。但这些土料如何从护城河中取土点运送至筑城位置,还无从推测,且目前还未曾发现可以确认为运土工具的遗物。而对于人群的防御则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目前还无法做出明晰的判断[8]。
二、工程价值
城头山古文化遗址中古城址的发掘,改写了我国史前城市规划的历史[2]。遗址中宽广的护城河和高大的城墙与传统的墙壕系统相比,其性质已发生了根本的质变,至少为修建类似古城提供了技术上的启发[8]。
1.工程主要成果
1992年和1997年城头山古文化遗址考古发掘成果两度被评为“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01年入选“中国二十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4]。其考古发掘成果,被镌刻进北京中华世纪坛青铜甬道,写进了中国大学、中学历史教科书[4,5]。2005年国家邮政局发行《城头山遗址》特种邮票,城头山遗址成为国家名片[9]。城头山古文化遗址于2021年入选国家文物局《大遗址保护利用“十四五”专项规划》“十四五”时期大遗址名单。
2.工程主要技术
作为一个完整的城市,城头山古文化遗址承担了精神文明、农业生产、日常生活、政治中心、交通运输、军事、防灾等多种功能,这些功能的实现也充分体现在其城市规划上[2]。
1)龙易文化与太阳崇拜影响下的空间形态
城头山古文化遗址的平面形状大致为圆形,城垣和护城河的形态也为适应圆形的城市平面而筑成圆形。据考证,城头山古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祭坛、祭坑、水坑、堰塘等均呈现圆形形态,不少玉玦、玉璜呈现C形,表明当时龙易文化思想的普遍性。圆形城市也是此后方形城市形制的基础[2]。
城头山古城自筑城伊始就有城市方位和通道的规划。城市在东南西北的城墙处修有基本对称的城门。就当时的科技水平来说,其对方位的测量是比较准确的,这也反映出我们的祖先已经清楚地知道东西南北四个方位并能在实践中运用。为了使水稻等农作物拥有充分的日照,且由于对太阳的博大和神奇的崇拜,因而将东门定为城市的正门。东西城门之间以一条长300米、宽2米的红烧土铺成的道路连接,南北城门之间也有大道直接相连,从而构成了古城十字形交叉的大道,并把古城划分为四区。城市中部发掘出的祭台和作坊等也都朝向东方。这样的空间结构也体现了城头山人阴阳两仪、四象生八卦的母易概念[2]。
2)阶级社会过渡时期形成的城市分区
随着城头山古文化遗址的不断发掘,我们也见证了其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过渡。在对遗址房屋的发掘中发现,早期遗迹中的房屋为群落型且有规则地以小屋群围绕一个大屋,各组小房子的门朝向与大房子一致,都朝向村落的中心广场。而在发掘出的大溪文化晚期至石家河文化时期的遗址中发现,房屋的面积逐渐缩小,长度也逐渐缩短,大家庭逐渐变为小家庭,贫富差距开始出现,城市分区逐渐明显,居住区的房屋质量也有了分化。同时,城市的分区规划变得更加合理。城头山古城的政治中心为王宫,位于城头山古文化遗址*高处,表明了它在功能分区中的重要地位。除此之外,城头山古城还规划有公共活动区[2]。
3)防御体系和灌溉体系的结合
城头山古文化遗址的城墙与壕沟都尊重了城市的圆形平面,围绕城市筑成环形。考古勘探发现,城头山古城从大溪文化一期筑造之日起就采用了城垣与壕沟相结合的造城形式,此后在屈家岭文化时期的三次扩建重修都不曾改变这种造城形式。长江中游地区原始稻作农业发展的不平衡导致聚落之间出现贫富差异,因而聚落之间常常出现掠夺性行为。由此推断,城头山古文化遗址城墙环壕设施的*要功能应该是军事防御。城头山古文化遗址使用了城墙和壕沟相结合的双重屏障,自然也就给城内的发展提供了安全的环境,才有了后来的人丁兴旺[2]。
城墙与壕沟不仅可以作为军事防御设施,对自然灾害也有一定的抵抗力。城头山古文化遗址虽为适应周边西高东低的地势建在澧阳平原西部高处,但其所在的澧阳平原整体地势较低,西侧平均海拔也仅为45米左右,且远在新石器时代,当地水网比今日发达,受洪水威胁的概率较高。因此,开沟筑墙也是为了抵御洪水来袭。同时,考古发现沿着壕沟底部与城墙修筑了许多排水沟,筑墙是为挡水,开沟是为排水,开沟的土可用来筑墙,可谓一举两得[2]。
就城头山古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情况而言,其农业生产力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城头山人在稻作农业上已经有了经规划修筑的人工灌溉系统。他们巧妙地利用地形西高东低的特点,将城市防御与稻作农业的灌溉系统结合起来。城墙北面西北部为蓄水用的堰塘,自此堰塘有南北两条壕沟顺城墙流下,于东门河流形成堰堤,流入低位的平地。稻田主要分布于城市东部,从而得以享受水系的天然灌溉。同时,除了北门蓄水的“庙大堰”以外,城头山古文化遗址水田周边也存在不少与“堰”有关的蓄水装置。
环形城墙、壕沟形成的双重体系既是城头山古城这样一个经济政治中心的良好屏障,也构成了农业文明先驱的自然灌溉体系[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