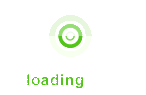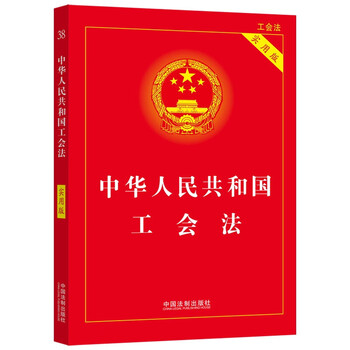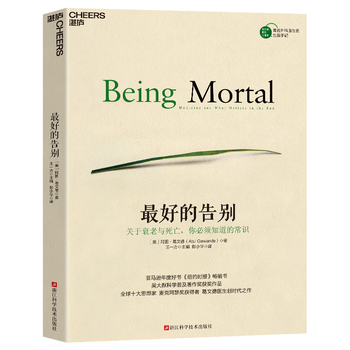内容简介
我叫乔纳斯,即将四十九岁,妻子离开了我,妈妈的记忆消退到经常认不出我,我有一个女儿,确切地说,她不是我的女儿,我也是最近才知道我们之间没有血缘关系。
我怀抱过刚出生的黏糊糊的婴儿,在12月去树林里砍过圣诞树,手把手教过孩子骑自行车,在或长或短的深夜里跟现实搏斗。我无比清楚人生有哭有笑,有爱有恨,每个人都有写诗的天赋,而且人们都深知自己终有一死。
我买了一张单程机票,来到一个远方国度的寂静旅馆,准备自杀,可我单薄的行李以及随身携带的工具箱却意外引起了旅馆主人和客人们的兴趣……
精彩书评
在这本小说中,我们会遇到一个中年男子,他带着一个工具箱前去一个被战争摧残过的欧洲国家。他本想去那里结束生命,在这趟旅程中,他逐渐意识到每个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工具箱,关键在于怎么用它。这本含义深远的小说,充满微妙的幽默感,用充满活力的语言探问人生大问题:生与死,个体与集体,我们的权利和义务。最终是责任感给了人类对抗黑暗的工具。
——2018北欧文学理事会评审团颁奖词
《寂静旅馆》是我很长时间以来读到的最人性的小说。
—— 《大鱼》作者丹尼尔·华莱士
书中的故事就像一个个水晶球,体积虽小却每一个都完美的收容着一个完整的世界。一部充满人文气息和艺术感的作品。
——法国《世界报》书评
试读
特里格威的文身房里,桌子上摆放着装有各种颜色墨水的玻璃罐,年轻的文身师问我是从已有的图片中选一张,还是要自己想一个图案或者符号。
他自己全身布满了文身。我观察到他脖子上的蛇样图案,那条蛇紧紧缠住一块黑色骷髅。墨水顺着他的胳膊往下蔓延,经过随着文身机针头一起一伏跳动的肱三头肌。
“许多人来到这里是为了遮掉皮肤上的伤疤。”文身师盯着镜子对我说。当他转过身时,我能隐约看到他的背心之下,一匹即将立地飞跃的骏马扬起马蹄。文身师将一堆折叠的塑料文件夹打开,从中取出一块,眼睛扫着上面的图案,精心为我挑选。
“翅膀图案是中年男人的心头好,”我一边听他讲,一边观察他另一条胳膊上一块四剑同刺焰心的文身。
在我身上一共有七处伤疤,以肚脐作为原点,四处位于肚脐上方,三处位于下方。如果文上一支鸟的翅膀,从肩部开始,穿过脖子直到锁骨,就能够盖掉其中两处甚至三处。就像一个彼此知根知底且相处起来轻松舒服的旧相识,那支丰满的羽翼将覆盖我的内心,成为我的庇护与堡垒。油墨画成的翅膀亦将保护我那因暴露在外而脆弱不堪的粉红色肉体。
那个年轻人轻轻翻着图册,向我介绍各式各样的翅膀图案,最后用他的食指指着其中一张说:“老鹰翅膀是最流行的图样。”我猜,在他看来似乎每一个男人都有一个关于雄鹰的梦想——孤独地滑过天空,翱翔在高山流水和沼泽泥潭之间,搜寻自己的猎物什么的。
但他只说了句:“你可以慢慢考虑。”
然后他跟我介绍坐在窗帘那一侧的另一位客人,那位客人坐在椅子上,即将完成他的国旗文身——几乎可以看到国旗迎风飘动的身影。
他压低自己的嗓音:“我跟他说过了,一旦他胖个两公斤,旗杆就会弯掉,但他坚持要文国旗。”
我打算在妈妈睡觉前去看看她,所以这个事情得越快越好,我拿定了主意。
“我想文个钻机。”
虽然对我的选择感到意外,但他并没有表露什么,只是很快在他的文件夹里找起来。“应该可以找到钻机的,在某个地方,应该是在电器这一边,”他说,“比起上个礼拜有个顾客要求文一台四轮越野车,这可要简单得多了。”
“算了,”我说道,“我开玩笑的。”
他盯着我,气氛凝结起来,我难以判断他是否被冒犯到了。我迅速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起来的纸。然后把它展开,递给他。你把那张纸朝各个方向转了转,最后拿到灯光下。这一次我真的让他感到相当意外,他的脸上写满了困惑。
“这是一朵花还是……?”
“一朵睡莲。”我毫不迟疑地说道。
“就一种颜色?”
“就一种颜色,白色。而且不要阴影。”
“也没有任何文字?”
“嗯,没有任何文字。”
他把文件夹都推到一边,说自己可以徒手画出睡莲,而且现在就可以直接拿起针开始干活。
“你想文在什么地方?”
当我开始脱下衬衣要给他展示心脏附近的位置时,他把文身机的针头浸入一瓶白色的液体中准备。
“得先把这些毛剃掉,”他一边说着关掉了文身机,“不然,你的这朵花会消失在森林的阴影里。”
国家,在那里人们借“生活”的名义慢性自杀
前往养老院最快的路线就是从墓地里穿过。
我经常幻想在5月结束自己的生命,在以数字5结尾的某一天,不是5月5日,就是5月15日,或者5月25日。5月也是我出生的月份。湖里的野鸭刚刚过了交配的时节,同美洲鹬和紫滨鹬一起,没日没夜地在春日里歌唱。我期待在这个春天之后,我将不复存在于人世。这个世界将会怀念我吗?我想不会。没有我世界会缺点什么吗?也不会。没有我世界将继续存在吗?是的。世界因为我的到来而变得好一点了吗?没有。我可以做点什么来让世界变得更好一点吗?我想没有。
走在什克索斯维嘉尔大街上,我一路思考如何向我的邻居斯瓦纽开口借一把猎枪。这会像借一块接线板那样简单吗?但五月初又有什么动物能作为捕猎的对象呢?不可能是金斑鸻,金斑鸻可是春天的使者,刚刚才回到岛上;也不可能是那些正在孵卵的鸭子……我是不是可以跟他说,我想射下那些整日吵闹不休、扰得我难以入睡的黑色海鸥?但我居住在市中心居民区顶层的公寓里;如果我说是为了保护那些雏鸭,斯瓦纽毫无疑问会起疑心……再说了,斯瓦纽知道我对打猎一窍不通。尽管我曾经站在荒野里冰冷的河流之中,寒冷就像一堵黏湿厚重的墙压在我的身上,我的长靴底下满是细碎的石块;我能察觉到湍急的河水在拉扯着我,河床仿佛正在坍塌消失,我望进那凝视着我的漩涡之中,自始至终却没有开过一次枪。最后一次钓鱼,我带回了两条鲑鱼,我把它们切成条,和种在阳台上罐子里的细葱一块儿炒了。而且自从斯瓦纽试图带我去电影院看《虎胆龙威4》之后,他就知道我对暴力深感恐惧。在五月时节,我们究竟可以朝什么开枪,自己吗?或者朝另外一个人类来一枪?斯瓦纽对这一切都了如指掌。
话虽如
前言/序言
我很清楚自己裸露的时候看起来有多么滑稽古怪,但我还是脱掉了。我先是脱掉裤子和袜子,然后解开衬衫的纽扣,展露出粉色肉体之上那朵耀眼的白色睡莲,它躺在我左侧的胸膛上,与那团每天要泵出8000公升血液的肌肉,只有半把刀子的距离,最后我脱掉了内裤。大家都按这个顺序脱。这花不了太多时间。我现在已经赤裸,站在木地板上,面对着一个女人,是神创造了我的这般模样,如今已有49年零6天,而我的思绪在这一刻却未曾向着神。我们之间隔了三块木板的距离,这些都是从附近森林里砍伐来的松木,这种红松在被开采的矿山上到处都是。不用理会那些空隙,每块木板有30厘米宽,我伸出手朝她的方向摸索着,就像正在寻找方位的盲人,我先是触碰到她肉体的外在之物,她的肌肤。窗帘的缝隙间透进来一丝月光,轻抚着她的背。她向我走了一步,我往前走,木地板咯吱作响,此时她也伸出手,把她的手掌贴在我的手掌上,生命线贴着生命线;我旋即察觉自己的动脉中血流汹涌,我的膝盖和胳膊迎来一阵悸动;我感觉到血液在所有的器官中奔腾。寂静旅馆11号房间,床铺之上的壁纸带着树叶的花纹,我心想,明天我要给木地板抛光打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