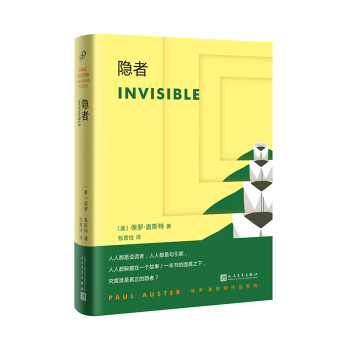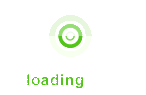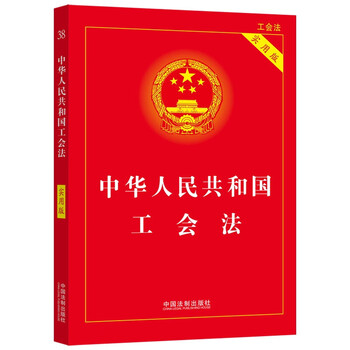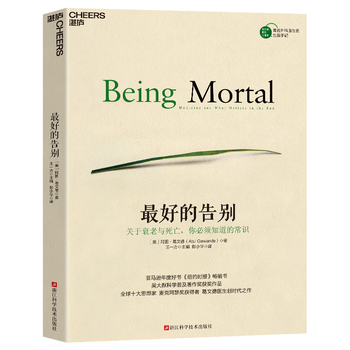内容简介
1967年春,纽约:二十一岁的哥伦比亚大学学生、诗人亚当·沃克结识神秘的法国学者鲁道夫·波恩和他沉默、迷人的女友玛戈。亚当迅速爱上玛戈,却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古怪的三角关系,它很终导向一件骇人的暴力突发事件,就此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2007年春,作家吉姆读着一个迷人却恐怖的故事。但这并非虚构小说,而是老友亚当寄给他的部分回忆录。吉姆为亚当的际遇深深震撼,并与亚当相约见面。然而还来不及等到见面那天,亚当已离开人世,仅留下零星不全的笔记。吉姆整理着老友遗留的字字句句,同时也被卷入亚当的伤心故事里:一个永不结束的四季,一颗忧郁的心,一些近似真实的妄想,一种逼近绝望的哀伤……
试读
和他第一次握手是在一九六七年春。我当时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二年级学生,一个一无所知的毛头小伙,嗜书如命,坚信(或者说是错觉)终有一天能够自称诗人。我读诗,所以已在但丁的地狱里和他的同名者打过照面了:一个在《地狱篇》第二十八歌最后几节里拖着脚走路的死人。贝特朗·德·波恩,十二世纪普罗旺斯诗人,手里提着自己被割掉的头上的头发,头颅像灯笼一样前后晃荡,在那本厚厚的幻觉与酷刑目录手册中,这显然是最阴森的形象之一。但丁是德·波恩作品的坚定支持者,然而,德·波恩建议亨利王子反抗自己的父亲国王亨利二世,但丁为此把他打入永劫不复之地,又因为德·波恩离间了这父子俩,使他们反目为仇,但丁便恰如其分地判他身首分离。于是,无头的躯干在地狱里哀号,向那位佛罗伦萨旅人提问:还有什么痛苦比他的更可怕。
他作了自我介绍,说他叫鲁道夫·波恩,我立马就想到了那位诗人。贝特朗的亲戚?我问。
啊,他回答,那个丢了脑袋的可怜虫。或许吧,不过恐怕不太可能。少了个“德”。贵族名字里才有“德”,悲哀的真相是,我和贵族沾不上边。
我完全记不起自己为什么会在那里。一定是有人约我同去,是谁呢?早已从我的记忆里蒸发得干干净净。我甚至记不起是在哪儿开的派对——在住宅区还是闹市区,在公寓还是阁楼里——也记不起我一开始怎么会接受邀请,因为当时的我讨厌扎堆,讨厌喧嚣的人群,我在陌生人面前会被腼腆击垮,这也令我尴尬。令人费解的是,那晚我答应了,由着那位现已被遗忘的朋友带我去随便什么地方。
我只记得这个:那天夜里某个时刻,我独自站在房间的一个旮旯里,边抽烟边望着人群,几十具年轻的身体在这封闭的空间里挤挤挨挨,我听着话语和笑声杂糅的喧响,不知道自己究竟在这里做什么。我想,或许是时候离开了。我左边的散热器上放着一只烟灰缸,就在我转身要摁灭烟头时,那只底部已满的容器却朝我升了起来——在一个男人的掌心里。我这才留意到,有一男一女坐在散热器上,两人都比我大,毫无疑问比屋里任何人都大——他三十五岁上下,她二十八九或三十出头。
我觉得他俩很不相称。波恩穿一件皱巴巴、脏兮兮的白色亚麻外套,底下的白衬衫也是皱巴巴的,那个女人(她叫玛戈)却是一身黑。我谢谢他递烟灰缸给我,他礼貌地朝我快速点了一下头,说他乐意之至——带着一点点外国口音。我没法辨别是法国腔还是德国腔,因为他的英语几乎无可挑剔。在那初会的时刻我还看见了什么?苍白的皮肤,蓬乱的带点红色的头发(比那时大部分男人剪得短),宽阔而英俊的脸上没有特别引人注目的特征(一张寻常的面孔,一张在任何人群里都会隐形的面孔),坚定的棕色眼睛,寻根究底的眼神,一个看起来天不怕地不怕的人才会有这种眼神。不胖不瘦,不高不矮,但是让人觉得健壮有力,或许是因为他的手特别厚吧。而玛戈呢,她纹丝不动地坐着,眼神儿直直的,仿佛她生命中的首要任务就是露出无聊的样子。不过,她的黑发,黑色圆翻领套头毛衣,黑色迷你裙,黑色皮靴,绿色大眼睛边黑色的浓妆,这些在二十一岁的我看来是迷人的,非常迷人。或许不是个美人儿,却是美人儿的拟像,仿佛她时尚而成熟的外貌中包含着某种这一年龄女性的理想典范。
波恩说,他和玛戈正要离开时瞧见我一个人站在角落里——看起来那么郁郁寡欢——他们决定过来给我提提劲,确保我不会在天亮前划破自己的喉咙。我不知该怎么理解这话。我想,这人是在挖苦我呢,还是真想对一个迷途的陌生小子表现一点善意?这些话本身挺顽皮的,足以让人消除戒心,但波恩说话时的眼神却是冷漠而疏远的,不由得我不觉得他是在试探我,嘲弄我——至于为了什么,我可完全没有头绪。
我耸耸肩,朝他微微一笑,说:你相信吗,其实我快活着呢。
这时他站了起来,同我握手,告诉我他的名字。在我问了那个关于贝特朗·德·波恩的问题后,他把我介绍给玛戈,后者沉默着对我微笑了一下,然后继续投身于凝望空间的使命。
从你的年纪看来,波恩说,从你对无名诗人的了解看来,我猜你是学生。显然是学文学的。纽大还是哥大?
哥大。
哥大,他叹了口气。真是个沉闷的地方。
你熟悉?
九月以来我都在国际事务学院教课。访问教授,为期一年。谢天谢地,现在是四月了,还有两个月我就可以回巴黎了。
那你是法国人了。
就境况、习性、护照而言,是的。但我生于瑞士。
法语区瑞士还是德语区瑞士?从你的声音里两者都能听到一点。
啧啧,波恩咂着舌,凑近来瞅着我的眼睛。你的耳朵很灵,他说。事实上,两者都是——我母亲说德语,父亲说法语。整个成长途中我就在两种语言间不断切换。
我沉默了一两秒,不确定接下来该说什么,然后问了个无伤大雅的问题:你在咱们这所阴沉的大学里教什么呢?
灾难。
这可够宽泛的,你说呢?
说具体点,就是法国殖民主义造成的灾难。我教的一门课讲阿尔及利亚的损失,另一门讲印度支那。
我们从你们那儿继承的那场可爱的战争。
永远不要低估战争的重要性。战争是人类灵魂最纯净、最栩栩如生的表达。
你这会儿听起来倒像我们的无头诗人。
哦?
我猜你没读过他的诗?
一个字都没有。我只是从但丁的诗篇里知道他。
德·波恩是个好诗人,甚至可能是个杰出诗人——但他令人不安。亨利王子死后,他写了一些迷人的爱情诗和一首感人的哀歌,但他真正的主题,似乎也是唯一令他真正魂牵梦萦的主题,就是战争。他从中得到狂欢。
我明白了,波恩朝我露出反讽的微笑。一个完全符合我心意的人。
我说的是那种,看着人们敲开彼此的头颅,看着城堡坍塌焚烧,看着长矛从尸体侧面穿出的快感。一派的鲜血淋淋,相信我,德·波恩眼都不眨。单是战争这个念头就令他快活无比。
我猜你对当兵不感兴趣。
没错。我宁愿坐牢也不去越南打仗。
假定你既不用坐牢,也不用参军,有什么计划?
没有计划。就是把手头的活儿继续下去,希望有天能成功。
是什么活儿呢?
写作。乱涂乱写的美妙艺术。
和我想的一样。玛戈在房间那头看见你时对我说:看看那个有一双悲哀的眼睛和耽于冥想的面孔的男孩,我敢打赌他是个诗人。你是吗——一个诗人?
我是在写诗,也给《目击者》写些书评。
本科生的玩意。
每个人都得有个起点。
挺有趣的……
一般。我认识的人有一半想当作家。
为什么说“想当”?如果你已经开始了,那就与未来无关。就在此时此刻,它已经存在。
因为现在要知道我够不够好还太早。
你的文章赚稿费吗?
当然不。那是份学校报纸。
当他们开始为你的作品付稿费时,你就会知道,你够好了。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波恩就兀自转向玛戈宣布:你没看错,我的安琪儿,你的小伙子是个诗人。
玛戈朝我抬起眼睛,带着一种中立的、评鉴的表情,第一次开了金口。事实证明她的外国口音比她的同伴重多了——毋庸置疑的法国口音。我从来不会看错,她说。到今天你该明白这点了,鲁道夫。
一个诗人,鲁道夫继续对玛戈说道,有时是个书评家,高地上那座抑郁城堡里的一名学生,这就意味着他或许是咱们的邻居。但他没有名字,至少我不知道他有。
我叫沃克,我说。我意识到自己和他握手时没有自我介绍。
亚当·沃克。
亚当·沃克,波恩重复道,同时把视线从玛戈转到我身上,再度闪现出他那谜样的微笑。一个又好又实在的美国名字,那么强健,那么平淡,那么可靠。亚当·沃克。宽银幕立体声西部片中孤独的赏金猎人,骑着棕栗色骟马,带一支猎枪和一支六连发左轮手枪纵横沙漠。要不就是日间肥皂剧里一名善良而规矩的外科医生,不幸同时爱上了两个女人。
听起来实在,我答道,但美国没有一样东西是实在的。这名字是我祖父一九〇〇年登陆埃利斯岛时别人分派给他的。移民当局显然觉得华辛斯基太难发音,随口就叫他沃克。
好一个国家,波恩说,文盲公务员轻轻一挥毫就夺走了一个人的身份。
不是身份,我说,只是名字。他在下东区当了三十年的好屠夫。
后面还有很多,在长达一小时的谈话中,话题漫无目的地从一个跳到另一个。越南和与日俱增的反战情绪。纽约和巴黎的差异。刺杀肯尼迪。美国对古巴的贸易禁令。没错,都不是什么私人话题,但是波恩对每件事都有强硬的观点,往往是些狂野的、不正统的观点,由于他说话的样子半带嘲讽,狡黠而故作谦逊,我无法判断他是否认真。有时他听起来像个鹰派右翼分子,有时,他支持的观点却使他听起来像个扔炸弹的无政府主义者。我问自己,他是想激怒我吗?或是这不过是他的习惯,是他在星期六晚上找乐子的一贯作风?与此同时,那位深不可测的玛戈离开了散热器,向我要了一支烟,随后就一直站着,几乎不为谈话贡献只言片语,事实上她简直就是一言不发,只是每当我开口时,她便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像个好奇的孩子。我得承认,被她这么看着很受用,尽管这让我有点局促。我觉得其中有种模糊的情色意味,但在那时还没有老成到可以判别她是在向我发信号,还是纯粹打量打量而已。事实是,以前我从没碰见过这样的人,他俩对我而言太陌生,其影响太新颖,因此我和他们谈得越久,他们就越显得不真实——仿佛是我脑海中某个故事里的虚构人物。
我们是不是喝了酒,我已经忘了,不过,要是这个派对和我到纽约后参加的那些派对大同小异,那么现场一定会有大罐大罐的廉价红酒和大堆的纸杯,就是说,我们越谈越醉。但愿我能忆起他还说了什么,然而一九六七年过于遥远,无论我如何努力回想初会时波恩的话语、手势和游离的话外音,几乎总是一无所获。不过,一片模糊中还是有几个鲜明的时刻,比如波恩把手伸进亚麻布夹克的内袋里,掏出一支吸了一半的雪茄,接着用火柴点燃它继续吸起来,一边告诉我这是“基督山”,最好的古巴雪茄——当时在美国是违禁品,现在仍然是——他是通过在华盛顿大使馆工作的某个相识搞到手的。接着他又说了一点卡斯特罗的好话——几分钟前他还在为约翰逊、麦克纳马拉、威斯特摩兰在与越共威胁作战时的英勇表现辩护。我记得自己被这位不修边幅的政治学家从口袋里抽出半支雪茄的场面逗乐了,我说,他让我想起一名在丛林里待得太久而发疯的南美咖啡种植园主。波恩笑了,很快补充道,我说的离真相不远,因为他童年的大段光阴都是在危地马拉度过的。我请他多说说那段日子,他却用一句“下次吧”打发了我。
我会把整个故事都告诉你,他说,但得在个安静点的地方。至今为止关于我那难以置信的生活的一切。你会看到的,沃克先生,有一天,你会写我的传记。我可以保证。
波恩的雪茄,我作为他未来传记作者的角色,还有玛戈用右手触摸我的脸,低声说:对自己好些——这些准是临近尾声的片段,我们当时正要离开,或者已经下了楼,但我对离开或者告别都毫无印象。那些已被四十年的时光抹得一干二净。他们是我青年时代的一个春夜在纽约某个喧嚣的派对上邂逅的陌生人,那个纽约如今已不复存在,仅此而已。也有可能记错,但我几乎可以确定,我们甚至没交换电话号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