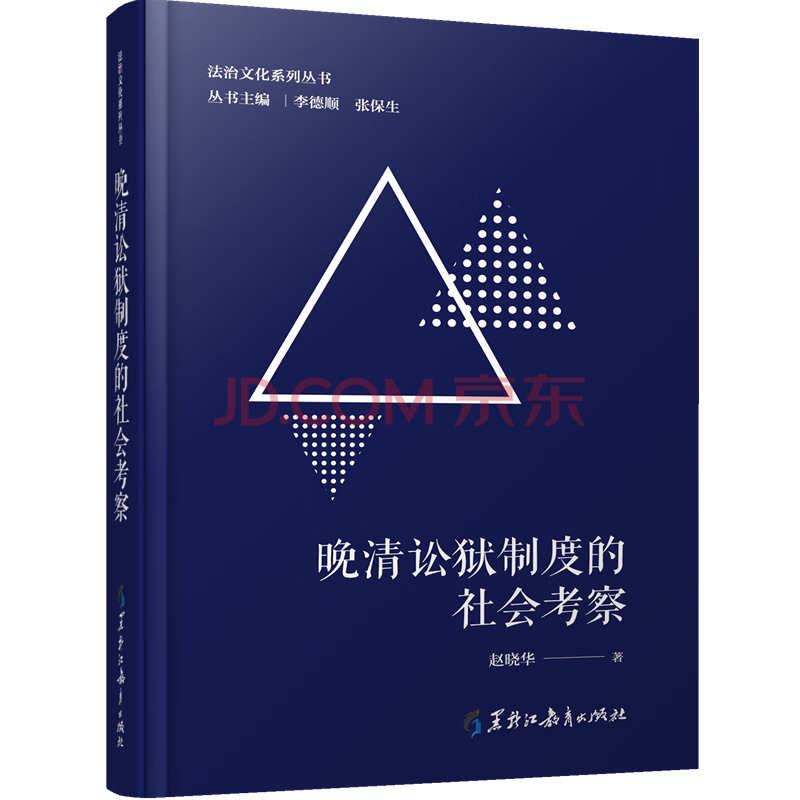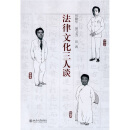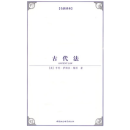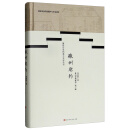内容简介
《晚清讼狱制度的社会考察》通过对晚清讼狱制度的观察与分析,体现了所考察的历史时段的特殊重要性。清朝是我国最后一个君主专制主义统治的封建王朝,它同今天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着紧密的联系。不仅今日的版图疆域及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人口基数奠定于清朝,而且当代中国的经济、政治、外交、民族关系等诸多方面的问题,也大都由清朝演化、延伸而来。
从鸦片战争开始的晚清时期,对于中国历史来说,更是一个极为特殊也极不寻常的历史时期。错综复杂的矛盾,急剧深刻的变化,激烈尖锐的斗争,交织成一幅令人目眩神迷的历史画卷。新与旧,悲壮与凄凉,追求与失落,如此独特又如此奇妙地纠结在一起,赋予了历史极其深邃的内容。
目录
引 言
第一章 晚清讼狱制度概述
第一节 晚清的诉讼审判程序
第二节 清代对诉讼权利的限制
第三节 诉讼费用
第二章 “理讼决狱”——吏治与法制的二重载体
第一节 吏治与法制
第二节 晚清诉讼制度中的幕吏擅权
第三章 晚清的积案问题
第一节 积案问题的严重性
第二节 积案问题的社会成因
第三节 清政府处理积案问题的对策及实际效果
第四章 待质积弊
第一节 问题的严重性
第二节 地方与中央政策的脱节
第三节 待质公所的设立及其效果
第五章 晚清监狱生活及狱政改良
第一节 晚清监狱生活状况
第二节 清末狱制改革中的实际问题及其效果
第六章 晚清的京控制度
第一节 清代的京控制度及晚清京控案件的增多
第二节 晚清京控案件增多的社会原因
第三节 晚清京控的结果
第四节 晚清京控制度与社会矛盾的尖锐化
第七章 晚清的刑讯制度
第一节 清代的刑讯制度
第二节 晚清的刑讯制度——兼论晚清酷吏的角色分类
第三节 合法刑讯制度的废除
第八章 讼狱制度影响下的社会心理
第一节 厌讼与惧讼心理
第二节 厌讼心理与传统国民性的互为影响
结 语
主要参考文献
后 记
附:法律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再版后记
试读
晚清的刑讯制度——兼论晚清酷吏的角色分类
从历史的角度看,刑讯本身即“人类因自身弱点而制造的种种祸害”之一。另一方面,任何一种法律制度的执行都是与各级执法者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与此相对应,与酷刑逼供联系在一起的必然是形形色色的酷吏群体。作为一个特殊而较为稳定的社会群体,酷吏几乎存在于历史上的每一个盛朝与衰世。从社会角色来看,酷吏群体当以用法酷烈和不遵奉法律为其鲜明的社会特征,但如若我们再具体分析,可见酷吏实际上是集贪酷之吏与能治之吏双重角色于一体的一个复杂而矛盾的社会群体。从一定意义上说,酷吏正是封建皇权与法制相矛盾的产物。在社会矛盾异常激化的晚清社会,酷吏的这两种角色体现得愈加鲜明。仔细分析一下晚清酷吏的角色分类,必将使我们对晚清讼狱制度中的执法群体有更具体的认识。以下试分别做一些分析。
一、贪酷之吏
人们习惯上总是将贪官与酷吏联系在一起。一般来讲,贪官酷吏的泛滥往往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统治秩序失衡和吏治腐败的明显表征。晩清时曾有人甄别古今酷吏说:“古之酷吏,虽深文周纳,不足语于导德齐礼之教,然引是非,明曲直,争天下大礼,严峻而无伤焉。后之所谓酷吏,舞文弄法,杀人以利己。”这段话反映了时人对酷吏只知“舞文弄法”、凌虐百姓的鄙视。概括起来,贪酷之吏以酷刑取供的动机主要是以逞私志、满足个人欲望为内容,大体来看,主要包括以下三种目的。
(一)速求定案,以博上司嘉奖赏识
我们在第三章中提及,有清一代,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和稳定社会秩序,渴求“刑期无刑”的清统治者对审理词讼的期限做了种种限定,清讼者奖,积案者罚。于是,各级官吏为了取悦上司,往往不择手段,借酷刑逼供,以速求定案。晚清小说家李伯元在《活地狱》书中描述了一个叫姚明的山西阳高县知县,专以酷刑取供,任何重案疑案一到他手,“不上三天,无供的立时有供,有供的永远不翻”。姚明不久即因“听断精明,案无留牍”而“官声大着,连着上司都知道他是个好官,便把他的名字记在心上”,不久即得以升迁,而身受其苦的百姓却对他恨之入骨,避之如避瘟疫。像姚明这样的官吏在当时是不少见的。为了迅速结案,“各州县每遇审讯,不论何犯酷用刑威,且有私设非刑以示严厉者”。如此必然导致欺下瞒上,所谓“严刑之下,何求不得”,冤案错案频发不断,因刑讯殒命者不计其数。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湖北通城县知县林逢年因民人魏圆圭被控窝贼,“喝令用小竹板责打四次,跪链压膝二次,并吓称如再刁狡,即用烟熏鼻”,但“魏仍未供,旋因病保出身故”。类似这样的冤案是屡见不鲜的。
(二)借酷刑贪污索贿,中饱私囊
“千里为官只为财”,许多酷吏正是以酷刑审讯为敛财搜刮的手段,以折磨受讯者而达到其收受目的。同治年间,甘肃省署礼县知县溶恬“于民人白鼎之妻自缢之案,酷刑索贿至三千两之多”。贵州省邓尔巽于署理遵义府绥阳县时,“勒逼民捐,不输者以香炙背,并添班卡勒捐,设立木站笼,致人死命。河南沈丘县知县丁土选之父,家不中资,因勒捐不遂,一家五人均毙囹圄”,该县在调任遵义县知县后,又将生员文新元勒捐押入站笼,令其倾家以赎。而这样一个酷吏,竟因为“屡冒军功升任道府”。酷吏借刑讯索钱表现在审讯的各个环节中。有的酷吏与差役狼狈为奸,“通同一气,暗中瓜分”,使得差役“肆意妄行”。在当时,公堂之上甚至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凡是犯罪的人,晓得自己理屈,今日难免责打,必须预先花钱给这个掌刑的,托他留情些,这板子下去,是有分寸的只要打得响,纵然皮破血流,决无妨事,过两天就会好的。若是不花钱,这板子打下来,记记是死的,大腿上不免就要受伤。”于是,犯罪之人“当比责之际,悉袖出钱筹一二枚以与差役,则被答时无痛楚,几若不知己身受笞也者。设无此物则甫笞数十下,即已流血满地,而呼痛之声竟令人惨不忍闻”。原、被两告如若事先不给予差役一些好处,则一旦受到刑讯,必然会得到比行贿者更惨痛的皮肉之苦。《活地狱》中一位叫张进财的原告,只因为讨三吊钱的账,便被昏官刑讯,而张进财因为“决计不曾料到自己挨打”,所以在掌刑的皂隶面前,“竞丝毫未曾关照”,差役们于是“满肚皮的没好气,也要借此发泄”,张进财最后竟被打了一千板子。
(三)以酷刑草菅人命,公报私仇
任何一种法制的执行效果与执法者的个人素质、性格都是有着很大关系的。刑讯制度无疑成为那些天性暴虐的人发泄私欲的种工具。《官场现形记》中的瞿耐庵,只因为上任接印时,被一个身穿重孝名叫王七的乡下人拦轿喊冤,便认为犯了忌讳,他不问喊冤人有何冤仇,就下令重责:
两旁差役一声吆喝,犹如鹰抓燕雀一般,把王七拖翻在地,剥去下衣。霎时间两条腿上,早已打成两个大窟窿,血流满地。瞿老爷瞧着地下一摊红的,方才把心安了一半。原来他的意思,以为:“我今日头一天接印,看见这个身穿重孝的人,未免太不吉利,如今把他打的
前言/序言
中国封建政治的特点之一,是各级官吏行政权与司法权的混一。又因为封建政权的职能主要着眼点在于维护现存统治秩序,而相对弱化于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的组织管理,因此,“断狱听讼”便成为封建官僚最主要、最经常的政务活动,这便是所谓“讼狱乃居官之首务”。与此相适应,法律制度和讼狱制度的内容及实施状况,也就成为反映封建政治本质的一种最重要、最直接的表现。
赵晓华同志《晚清讼狱制度的社会考察》一书所论述的问题其意义首先就在于通过对晚清讼狱制度的观察与分析,深入揭示封建政治的黑暗与罪恶。
本书容易引起读者兴趣的,还在于它所考察的历史时段的特殊重要性。清朝是我国最后一个君主专制的封建王朝,它同今天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着紧密的联系。不仅今日的版图疆域及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人口基数奠定于清朝,而且当代中国的经济、政治、外交、民族关系等诸多方面的问题,也大都由清朝演化、延伸而来。从鸦片战争开始的晚清时期,对于中国历史来说,更是一个极为特殊也极不寻常的历史时期。错综复杂的矛盾,急剧深刻的变化,激烈尖锐的斗争,交织成一幅令人目眩神迷的历史画卷。新与旧,正义与邪恶,抗争与屈辱,悲壮与凄凉,追求与失落,如此独特又如此奇妙地纠结在一起,赋予了历史极其深邃的内容。
晚清的讼狱制度,当然不能不带有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时代烙樱虽然已经过时,但凭借着全部暴力机器的支持而顽强存在的旧的制度与运作机制,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主宰着人们的生活和命运;近代化的转变已经开始,但却步履蹒跚,举步维艰。本书对这两个方面都给予了关注,但不难发现,作者着力之处,主要还是在前一方面。我以为,这并非作者的疏忽,倒是当时社会状况的客观反映。
1897年,孙中山曾专门撰文揭露清廷讼狱制度的黑暗与腐败。他说:“在中国对任何社会阶层都无司法可言……地方行政官和法官的存在只是为了自己发财致富和养肥他们的顶头上司,直至皇室自身。民事诉讼是公开的受贿竞赛;刑事诉讼程序只不过是受刑的代名词—没有任何预审—对被告进行不可名状的、难以忍受的严刑拷打,不仅对可能有证据的嫌疑犯是如此,而且对任何个兵勇或地位较高者告发的人也是如此。”我们不妨把孙中山的这段话看作是本书的提纲絜领的概括,也可以把本书看作是孙中山这段话的具体而形象的演绎。当然,我们这里只是讲二者之间的客观联系,作者在写作时是未必见得到这一点的。
有的人是不大主张写历史上的黑暗和苦难的,我却以为读读这方面的东西颇有益处。至少,了解一点封建时代的令人窒息的罪恶统治,才能够对近代志士仁人们如此热烈地追求民主、自由的思想和实践多一点理解;了解一点我们民族曾经遭受过的种种难以想象的苦难,才能够对今天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与巨大前进多一分珍惜。
赵晓华同志写作本书时,曾同我讨论过几次。其间,我们还合作过一篇题为《厌讼心理的历史根源》的文章,发表于《光明日报》。现在书要出版,让我写几句话作为序言,我自然是义不容辞的。不过,在学生吹捧老师、老师吹捧学生、同行间互相吹捧几乎成为时尚,一开口不把老的称作“大师”“权威”,小的不称作“新秀”“新星”好像就对不起对方的今天,我的小序就只便限于谈一点对本书主题意义的看法,而把对作者和作品内容评价的权利留给读者。这样做,可能不够“新潮”,难免招到“不懂包装”之讥,但无论对于我,于作者,都会更加心安理得一些。
李文海
于中国人民大学林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