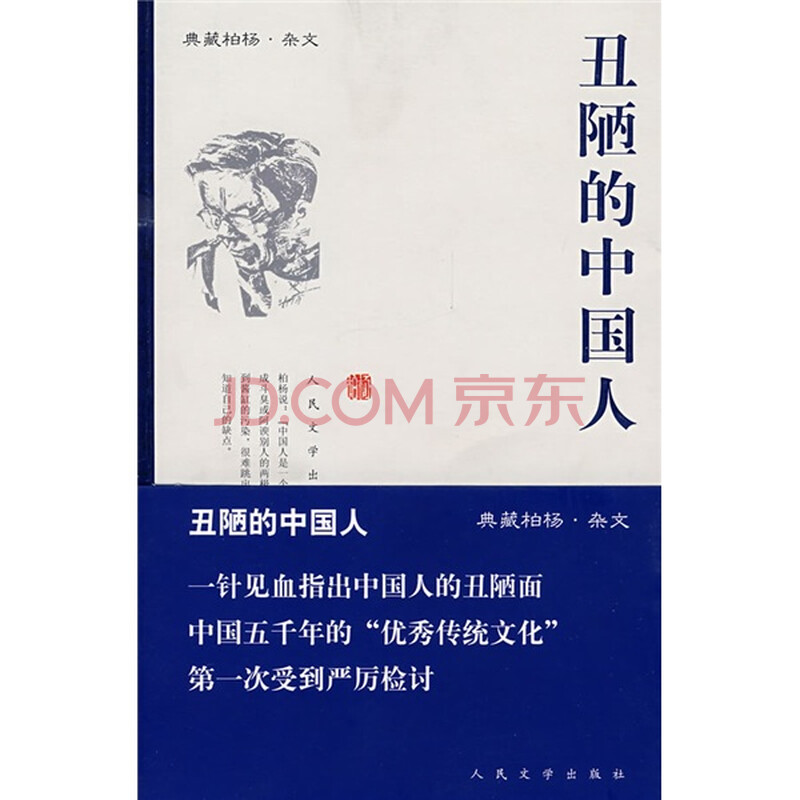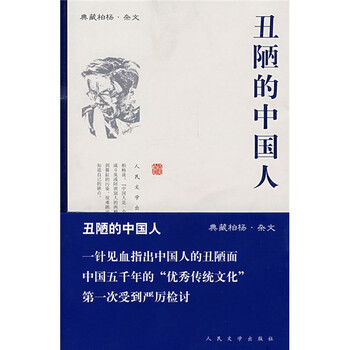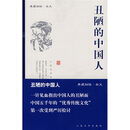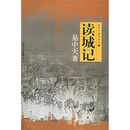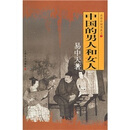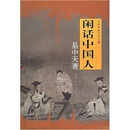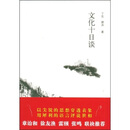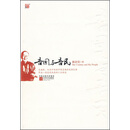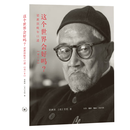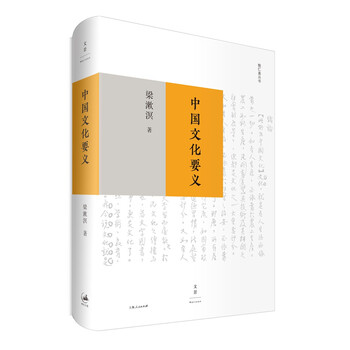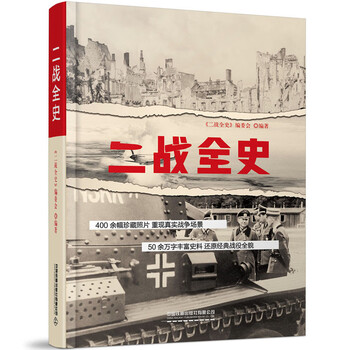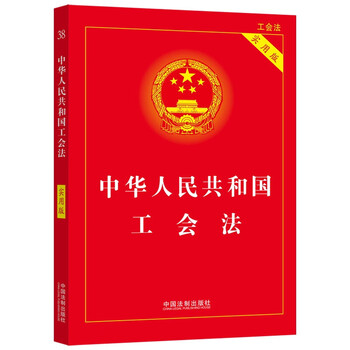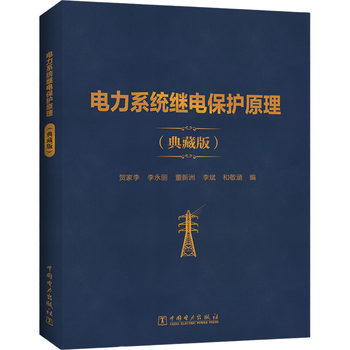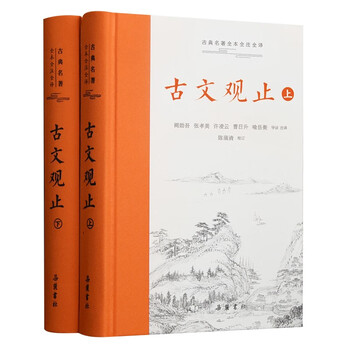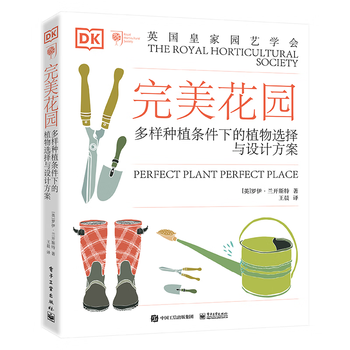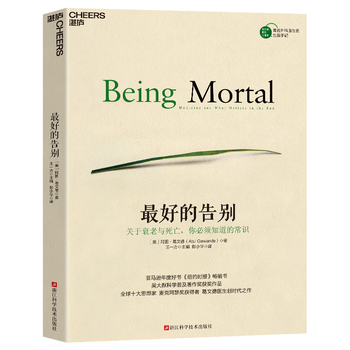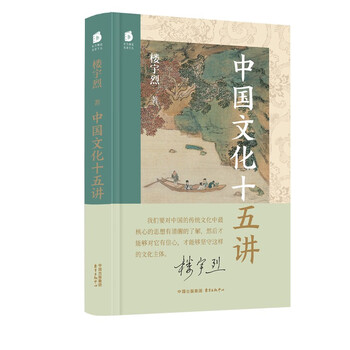内容简介
《丑陋的中国人》是柏杨在1984年9月24日美国爱荷华大学演讲,强烈批判中国人的“脏、乱、吵”、“窝里斗”以及“不能团结”等,并将原因归结到“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滤过性病毒,使我们的子孙受到了感染,到今天都不能痊愈”。次年8月,此篇讲稿和另外两场演讲的记录《中国人与酱缸》、《人生文学与历史》,一篇访问稿《正视自己的丑陋面》,以及柏杨的三十几篇杂文、近二十篇的回应文章结集出版,是为轰动一时的《丑陋的中国人》。
著名漫画家方成先生,以八十九岁的高龄特为八十八岁的柏杨先生绘制漫画插图,两位年近九旬老者的携手,珠联璧合,实为两岸文化交流的一大盛事。
柏杨曰:
脏、乱、吵,窝里斗!三个中国人加在一起,就成了一头猪!
死不认错;为了掩饰一个错,不得不用很大的努力再制造更多的错,来证明一个错并不是错。
喜欢装腔作势,记仇,缺乏包容性,中国人打一架可是三代都报不完的仇恨!
自傲、自卑,就是没有自尊,缺乏独立思考能力,更恐惧独立思考。没有是非、没有标准,只会抽风发飙。
目录
中国人丑陋吗? 冯骥才
酱缸国医生和病人(代序) 柏杨
上辑·沉痛出击
丑陋的中国人
正视自己的丑陋面
中国人与酱缸
人生文学与历史
老昏病大展
起敬起畏的哲学
缺少敢讲敢想的灵性
对事不对人
只我例外
谋利有啥不对
沉重的感慨
第一是保护自己
尿入骨髓
洋人进一步,中国人退一步
最大的殷鉴
把羞愧当荣耀
炫耀小脚
臭鞋大阵
为别人想一想
不会笑的动物
礼义之邦
三句话
排队国
到底是什么邦
酱缸蛆的别扭
目光如豆
不讲是非,只讲“正路”
一盘散沙
唐人街——吞噬中国人的魔窟
《春秋》责备贤者
谈丑陋的中国人(陈文和)
虚骄之气
恐龙型人物
崇洋,但不媚外
种族歧视
集天下之大鲜
下辑·怒涛拍岸
我们还可以做个好儿子
柏杨余波
也是丑陋中国人余波
中国传统文化的病征——酱缸
如何纠正死不认错之病
推理能力发生故障
从酱缸跳出来
“酱缸文化”
要隐恶扬善,勿作践自己
贱骨头的中国人
丑陋的王亦令
评王亦令《贱骨头的中国人》
王亦令越描越丑
不懂幽默
中国人的十大奴性
没有文明哪有文化
中国文化不容抹黑
中国文化之“抹黑”与“搽粉”
伟大的中国人
你这样回答吗
试读
本文是柏杨于1984年9月24日在美国爱荷华大学讲辞,吕嘉行记录。
多少年以来,我一直想写一本书,叫《丑陋的中国人》。我记得美国有一本《丑陋的美国人》,写出来之后,美国国务院拿来作为他们行动的参考。日本人也写了一本《丑陋的日本人》,作者是驻阿根廷的大使,他阁下却被撤职,这大概就是东方和西方的不同。中国比起日本,好像又差一级,假定我把这本书写出来的话,可能要麻烦各位去监狱给我送饭,所以我始终没有写。但是我一直想找个机会,把它作一个口头报告,请教于各阶层朋友。
不过作一个口头报告也不简单,在台北,请我讲演的人,一听说要讲这个题目,就立刻不请我了。所以,今天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用“丑陋的中国人 ”讲演,我感到非常高兴,感谢各位给我这个机会。
有一次,台中东海大学请我演讲,我告诉他们这个题目,我问同学会会长:“会不会有问题?”他说:“怎么会有问题?”我对他说:“你去训导处打听一下,因为我这个人本来就被当作问题人物,又讲一个问题题目,那可是双料。”跟训导处谈过之后,他打电话到台北来说:“问题是没有的,不过题目是不是可以改一改?训导处认为题目难听。”接着把他拟定的一个很长的冠冕堂皇的题目告诉我,他问:“同意不同意?”我说:“当然不同意,不过你一定要改,只好就改!”那是我第一次讲有关“丑陋的中国人” 。我对他说:“希望我讲的时候能做个录音,以后我就可以把它改写成一篇文章。”他慷慨承诺。结果讲过之后,把录音带寄来,只有开头的几句话,以后就没有了声音。
今年我六十五岁,台北的朋友在3月7日给我过了一个生日,我对他们说:“我活了六十五岁,全是艰难的岁月!”我的意思是:不仅仅我个人艰难,而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艰难。在座的朋友都很年轻,尤其是来自台湾的朋友们,多数拥有富裕的经济环境,同你们谈“艰难”,你们既不爱听,也不相信,更不了解。我所谈的艰难,不是个人问题,也不是政治问题,而是超出个人之外的,超出政治层面的整个中国人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人经历了患难,不仅仅是我这一代经历了患难。假使我们对这个患难没有了解,对这个有毒素的文化没有了解,那么我们的灾祸还会再度发生,
前言/序言
人与人确实会擦肩而过,比如我和柏杨先生。
1984年聂华苓和安格尔主持的“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对我发出邀请,据说与我一同赴美的是诗人徐迟。同时还从台湾邀请了柏杨先生。但我突然出了点意外,没有去成,因之与这两位作家失之交臂,并从此再没见过。人生常常是一次错过便永远错过。
转年聂华苓再发来邀请。令我惊讶的是,在我周游美国到各大学演讲之时,所碰到的华人几乎言必称柏杨。其缘故是头一年他在爱荷华大学演讲的题目非常扎眼和刺耳:丑陋的中国人。一个演讲惹起的波澜居然过了一年也未消去,而且有褒有贬,激烈犹新,可以想见柏杨先生发表这个演讲时,是怎样的振聋发聩,一石撩起千层浪!其实作家就该在褒贬之间才有价值。我找来柏杨先生的讲稿一看,更为头一年的擦肩而过遗憾不已。其缘故,乃是当时我正在写《神鞭》和《三寸金莲》,思考的也是国民性问题。
国民性是文化学最深层的问题之一。国民性所指是国民共有的文化心理。一种文化在人们共同的心理中站住脚,就变得牢固且顽固了。心理往往是不自觉的,所以这也是一种“集体无意识”。对于作家来说,则是一种集体性格。由于作家的天性是批判的,这里所说的国民性自然是国民性的负面,即劣根性。鲁迅先生的重要成就是对中国人国民劣根性的揭示;柏杨先生在《丑陋的中国人》所激烈批评的也是中国人国民性的负面。应该说,他们的方式皆非学者的方式,不是严谨而逻辑的理性剖析,而是凭着作家的敏感与尖锐,随感式却一针见血地刺中国民性格中的痼疾。鲁迅与柏杨的不同是,鲁迅用这种国民集体性格的元素塑造出中国小说人物画廊中前所未有的人物形象——阿Q,遂使这一人物具有深刻又独特的认识价值。当然,鲁迅先生也把这种国民性批判写在他许多杂文中。柏杨则认为杂文更可以像“匕首一样”直插问题的“心脏”——这也是他当年由小说创作转入杂文写作的缘故。故而柏杨没有将国民性写入小说,而是通过杂文的笔法单刀直入地一样样直了了地摆在世人面前。他在写这些文字时,没有遮拦,实话实说,痛快犀利,不加任何修饰,像把一张亮光光的镜子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把自己看得清清楚楚,哪儿脏哪儿丑,想想该怎么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