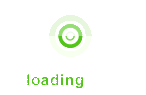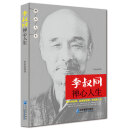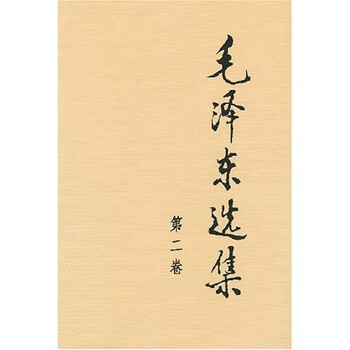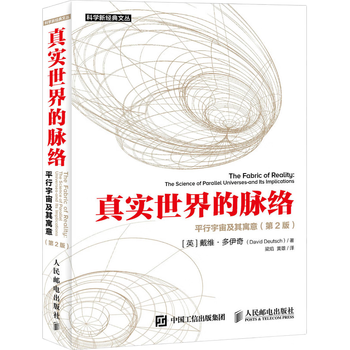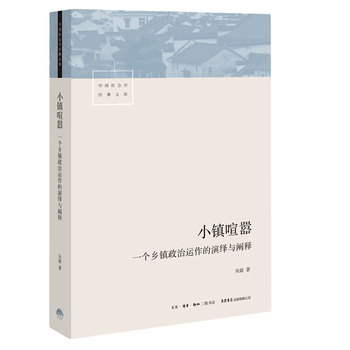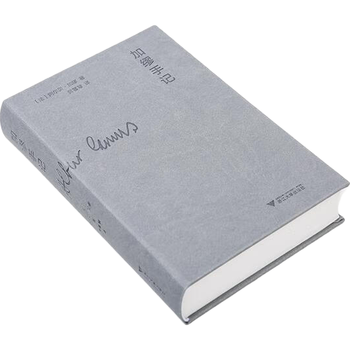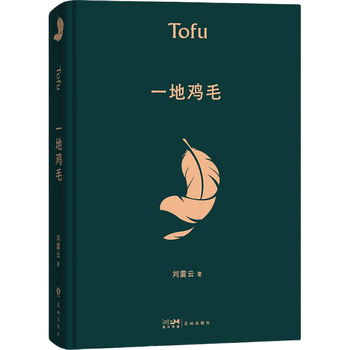内容简介
真正能够承受虚空的唯一方式,就是意识到虚无,否则生命便是无法忍受的。但是,如果你意识到了虚无,那么你经历的一切都可以保持正常比例,而不会被绝望夸大成疯狂的比例。
即使在极度绝望的时刻,我也有笑的力量。这就是人类比动物强的地方。笑是一种虚无主义的表现,就像愉悦可以是一种哀悼的状态。
当我的朋友——或者陌生人——经历苦恼和绝望的时刻,我只有一个建议能给他们:“去墓地走走。”
*
在生命zui后的二十五年里,齐奥朗陆续接受来自世界各地的采访。在这些谈话中,齐奥朗回忆在罗马尼亚的童年和青春岁月、移居法国的经历、思想的来源、与友人的关系,并谈及自己为何抛弃母语,改用法语写作。
访谈真实呈现了贯穿齐奥朗作品的核心主题,汇聚了其碎片化思想的精髓:无聊、失败、死亡、神秘主义……机锋与笑语之间,折射出这位“异端”思想家的矛盾本性——激进的悲观主义中,总是伴随着欢快、幽默和嘲讽。
目录
与弗朗索瓦·邦迪的对谈
与费尔南多·萨瓦特尔的对谈
与黑尔佳·佩尔茨的对谈
与让–弗朗索瓦·杜瓦尔的对谈
与莱奥·吉莱的对谈
与路易斯·豪尔赫·哈尔芬的对谈
与韦雷娜·冯·德·海登–林施的对谈
与何塞·马里亚·西莱斯的对谈
与莱亚·韦尔吉内的对谈
与格尔德·贝格弗勒特的对谈
与埃丝特·塞利格松的对谈
与弗里策·J. 拉达茨的对谈
与弗朗索瓦·费伊特的对谈
与本杰明·伊夫里的对谈
与西尔维·若多的对谈
与加布里埃尔·利恰努的对谈(节录)
来自贝尔纳–亨利·莱维的三个问题
与乔治·卡帕特·福克的对谈
与布兰卡·博加瓦茨·勒孔特的对谈
与迈克尔·雅各布的对谈
译名对照表
试读
与费尔南多·萨瓦特尔的对谈
齐奥朗?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您想问的是,我为什么不简简单单地选择沉默?为什么要侵扰我周围的一切?您在责备我明明有闭嘴这个最好的选择,却还要四处挥洒哀号。首先,并非人人都有幸英年早逝。我的第一本书是二十一岁时用罗马尼亚语写的,写完那一本,我就向自己保证此后不再写作。然后我又写了一本,接着又做出同样的承诺。这出喜剧在四十多年里不断重复着。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正是写作——即使只是很少的写作——帮助我活过一年又一年,因为我的顽念一经表达就会减弱,甚至有些已经被克服了。我确信,如果我不写些什么的话,那我很久前就已经自杀了。写作是一种超凡的宽慰。发表作品也是如此。您会觉得这话可笑,但它又千真万确。因为书就是生命,或者说是生命的一部分,从而让人得以置身事外。我们可以把我们所爱的一切和所恨的一切都丢进去。我甚至可以说:如果我没有写作的话,我可能会成为一个杀手。表达是一种解放。我建议您试着做以下练习:当您厌恶某个人,想摆脱他时,拿一张纸,写下某人是猪、强盗、恶棍、怪物的字眼。您会立刻察觉到,自己对他的憎恨减轻了。这正是我的做法。我用文字辱骂生命,辱骂自己。结果呢?我因此更能容忍自己,也更能容忍生命。
费尔南多·萨瓦特尔(以下简称萨瓦特尔)?齐奥朗,对这个话题,您还能做些补充吗?
齐奥朗?说实话,我没法再多讲些什么了……或许我可以!事实上,这关乎生命力的问题。为了讲明白这一点,我得先谈谈自己的出身。我与农民有着深厚的渊源;我的父亲是一名乡村神父,我出生在喀尔巴阡山脉的一片极为原始的山区。那是一个真正粗犷的小村庄,农民们整周辛勤劳作,却常常花上一夜大喝一场,挥霍掉他们的全部收入。我当时是个相当健壮的小伙子。如今我身上这些虚弱的地方,那时都曾经充满活力!您可能会有兴趣了解,那时我最大的志向是成为最出色的九柱戏玩家。我十二三岁时,经常为了赢钱或啤酒和农民们打球。我在星期天和他们比赛,尽管他们比我强壮,但我依然常常获胜,因为当时的我无所事事,可以花一整周的时间来练习……
关于罗马尼亚
萨瓦特尔?您的童年幸福吗?
齐奥朗?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从未见过谁的童年比我的更幸福。我在喀尔巴阡山脉的田野和山间自由自在地玩耍,没有任何义务和责任。那是个非凡幸福的童年。之后,我在与人交谈时从未找到过任何能与之相提并论的东西。我多么希望自己从未离开过那个村庄。我无法忘记父母让我坐上汽车去城里上学的那天。那是我梦的终结,是我世界的毁灭。
萨瓦特尔?您对罗马尼亚记忆最深刻的东西是什么?
齐奥朗?我最喜欢罗马尼亚的一点就是它极其原始的一面。当然那里也有文明人,但我更偏爱那些没有文化,甚至连字都不识的人……二十岁之前,我最喜欢的事情就是逃离锡比乌,钻进山区里,与那些大字不识一个的牧羊人和农民攀谈。我花了大把时间和他们聊天、喝酒。我认为一个西班牙人能够理解这种极为原始的一面。我们无所不谈,我几乎立刻就能和他们建立起联结。
萨瓦特尔?在您记忆中,您年轻时祖国所处的历史状况是什么样的?
齐奥朗?好吧。当时奥匈帝国占据西欧。位于特兰西瓦尼亚的锡比乌属于帝国的一部分,而我们梦中的首都是维也纳。我总是觉得自己以某种方式与帝国相连……然而在帝国,我们罗马尼亚人却是奴隶!1914年的战争中,我的父母被匈牙利人驱逐……我在心理上觉得自己和匈牙利人很亲近,我们的品味和生活习惯都很接近。匈牙利的吉卜赛音乐深深令我动容。我是匈牙利人和罗马尼亚人的混合。奇怪的是,罗马尼亚人是世界上最相信宿命论的人。他们用模糊不清的形而上学概念——比如命运、命定——来解释世界,这曾令年轻时的我非常愤怒。可我年龄越大,反而越觉得自己贴近自己的根源。现在,我本应该认同自己是欧洲人、西方人,但事实绝非如此。我了解很多国家,读过很多书,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罗马尼亚农民才最懂道理。这些农民什么都不信仰,他们觉得人类早已迷失,已经无事可做,他们感觉自己被历史压垮了。这种受害者心理最终也成为我当下的观念,我的历史哲学。实际上,我所受的一切的知识教育,到头来全然无用!
书是一种创伤
萨瓦特尔?您曾写过:“一本书必须深入创伤,甚至刺激创伤。一本书必须是一种危险。”您的书在什么意义上是危险的?
齐奥朗?好吧,听着,好几次有人告诉我,我在书中写了一些不该说的东西。《解体概要》出版时,《世界报》的评论家给我寄来一封充满责备的信:“您没有意识到,这本书可能会落入年轻人手中!”这太荒谬了。书应该有什么作用?供人学习吗?这完全没有意义,因为那样的话,人只要去上课就行。不,我认为一本书应该真正地成为一种创伤,它应该以某种方式改变读者的生活。我写书是为了唤醒人们,鞭笞人们。我的书都是从我的不安和痛苦中涌现出来的,所以它们也应该以某种方式把这些东西传播给读者。不,我不喜欢那些读起来像报纸一样的书:一本书应该颠覆一切,质疑一切。为什么呢?我不太关心我写的东西是否有用,因为我几乎从未真正想到读者:我为自己而写作,为了让自己从顽念和紧张中解脱而写作,仅此而已。最近,一位女士在《巴黎日报》上这样评价我:“齐奥朗写的是每个人都只会低声自语的那些东西。”我写作的目的不是要“创作一本书”供人阅读。不,我写作是为了抛下自己肩上的重担。但在写完之后,我才会思考我的书该有何种功能,那时,我才对自己说,它们应该像一种创伤。如果读者读完一本书后毫无变化,那这本书便是失败的。
萨瓦特尔?在您所有的书中,与我们可以称为悲观的、黑色的风格比肩的是一种奇特的欢乐,一种无法言喻却令人宽慰,甚至给人活力的愉悦。
齐奥朗?很奇怪,您说的这话,很多人都曾说过。我的读者不多,但我可以告诉您,我身边的人从很多人那里都听过这样的话:“如果我没有读过齐奥朗,我就已经自杀了。”因此,我认为您说的很有道理。我认为这来自我的激情:我不是个悲观主义者,我很粗暴,正是这一点让我的负面话语显得如此令人振奋。实际上,当我刚才提到创伤时,我并没有从负面角度来看待它:让一个人受伤绝不等同于让他一蹶不振!我的书既不抑郁,也不消沉。我怀着愤怒和激情完成每一本书。如果我的书可以被冷静地完成,那就太危险了。可我不能冷静地写作,我仿佛患了病,但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会狂热地克服自己的病弱。《解体概要》的第一个读者是诗人于勒·苏佩维埃尔,当时这本书还只是一份手稿。那时候的他已经很老了,深陷抑郁,他告诉我:“您的书激发了我,真是难以置信。”在这个意义上,您可以说我就像魔鬼,既是一个积极的个体,也是一个撼动事物的否定者……
萨瓦特尔?尽管您主动将自己的作品与所谓的经典哲学区分开来,但在十九世纪的伟大哲学体系崩溃后,占据其位置的是多样化的自我批判性活动,若是把您的作品置于这一框架内,似乎也不无道理。哲学还有什么意义呢,齐奥朗?
齐奥朗?我认为哲学只有在作为碎片的时候才是可能的。要以爆发的形式。已经不可能再用论文的形式一章接一章地阐释哲学了。在这个意义上,尼采是一个卓越的解放者。正是他打破了学术哲学的风格,抹杀了体系的观念。他是解放者,因为在他之后,人们可以畅所欲言了……现在,我们全都是碎片主义者,即使我们写的书貌似很有条理。这也与我们文明的风格相适应。
萨瓦特尔?这也与我们的诚实有关。尼采曾说过,成体系的野心缺乏诚实……
齐奥朗?提到诚实,我可以给您讲述一些事情。当一个人开始动笔写一篇四十页的论文时,他事先已经在内心有了某些论断,他被监禁于这些论断之中。某种诚实的思想会迫使他一路走下去,尊重自己内心的论断,不能自我违背;但随着他写作的进展,文本又会给他其他的诱惑,他不得不拒绝这些诱惑,因为它们会使他偏离已经设定的道路。我们就这样被困在自我划定的圈子里。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努力做到诚实时,便会陷入虚伪和缺乏真实的境地。如果一篇四十页的论文都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一个体系又何尝不会呢!这就是所有结构化思维的悲剧之处:不允许矛盾存在。人们就这样陷入错误,就这样为了保持结构的紧密而欺骗自己。与之相反的是,如果我们制造碎片的话,就可以在同一天讲述一件事的正反面。为什么?因为每个碎片都来自不同的体验,而这些体验是真实的:它们才是本质。有人会说这样做不负责任,但如果以这样的角度来看,人生本身就是不负责任的。碎片化思想可以反映生活体验的每个角度;而体系化思维却只能反映一个角度,那是受控制的角度,因而也是贫瘠的角度。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表达了每一种可能的人性,每一种可能的体验。而在体系中却只有控制者和领导者可以说话。体系传达的永远是领导者的话语,这就是为什么每个体系都是极权的,而碎片化思想却能保持自由。
萨瓦特尔?您接受过哪些哲学教育?哪些哲学家是您最感兴趣的?
齐奥朗?年轻时我曾读过很多列夫·舍斯托夫的作品,他当时在罗马尼亚很出名。但我最感兴趣的——应该说是最喜欢的哲学家是格奥尔格·齐美尔。我知道,齐美尔在西班牙很出名,因为奥尔特加对他有浓厚兴趣,而在法国,他则遭到全然的忽视。齐美尔是一位出色的作家,也是优秀的哲学家兼评论家。他曾经是卢卡奇和布洛赫亲近的朋友,这两人受到他的影响,后来却不承认这一点,在我看来他们毫不正直。如今,齐美尔在德国已完全被人遗忘,甚至陷入沉寂,但在他的时代,连托马斯·曼和里尔克等人都很欣赏他。齐美尔也是一位碎片化思想家。他的作品中最精彩的就是那些碎片。我还深受狄尔泰等被称为“生命哲学”的德国思想家影响。我以前也读过很多克尔凯郭尔的书,那时他还并不时兴。总的来说,最让我感兴趣的一直是告解式哲学。无论是哲学还是文学,最令我感兴趣的都是案例,以及那些几乎可以被称作临床诊断意义上的“案例”的作者。我对那些走向灾难的人感兴趣,也对那些超脱于灾难之外的人感兴趣。我最钦佩的是那些在崩塌边缘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尼采和奥托·魏宁格。或者像罗扎诺夫这样,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风格不断刮擦着伤口的宗教作家。像胡塞尔这样仅仅提供一种智力体验的作家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感触。对于海德格尔,我感兴趣的是他克尔凯郭尔式的一面,而不是胡塞尔式的一面。但首先,我在寻找案例:在思考和文学中,我的兴趣尤为集中在脆弱和不稳定性之上,我关注即将坍塌的事物,也关注那些虽然抵御着坍塌的诱惑,但也永远面临威胁的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