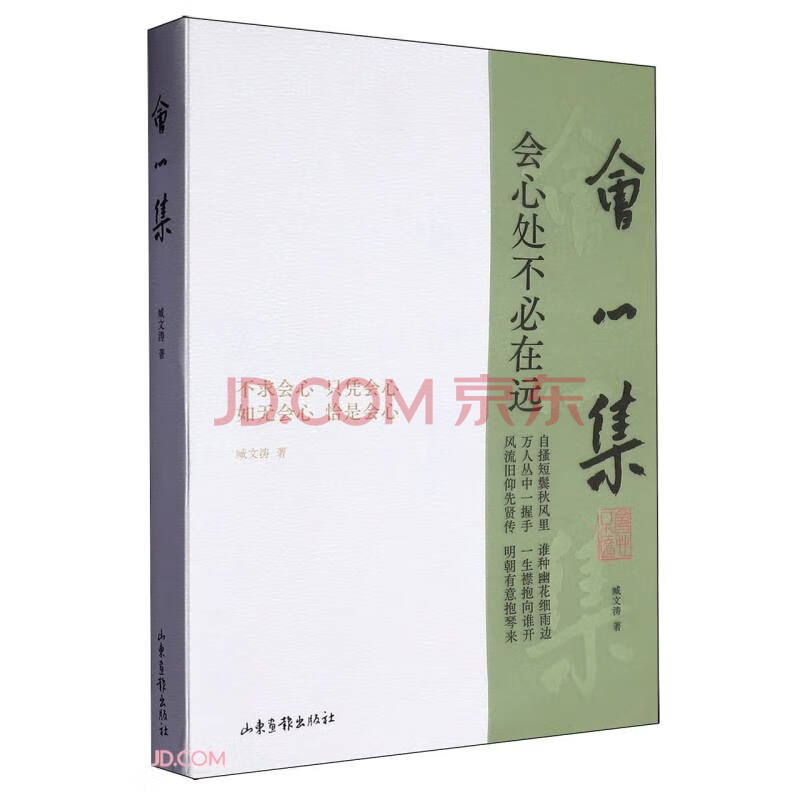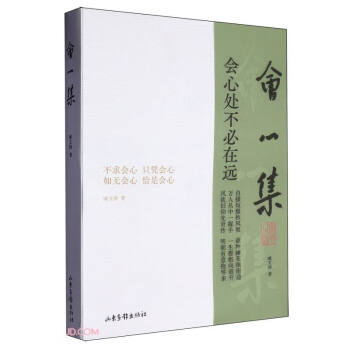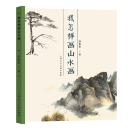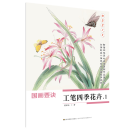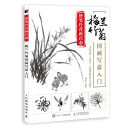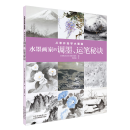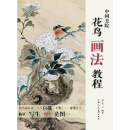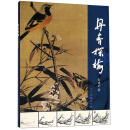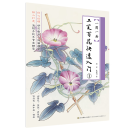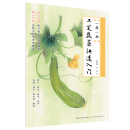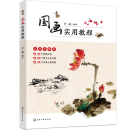内容简介
《会心集》以通透的笔触,探讨艺术与文化的关系。为什么山东艺术家难以成为全国性大家?从木心到董其昌,造神与被造神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文化逻辑?每一个话题都扎根历史,却直指当下。书中既有对中国传统书画精神内涵的挖掘,也有对当下艺术生态的批判与建议;既有关于个案艺术家细致入微的研究,也包含了宏观视野下的整体观察。
目录
序 笑指凌云得得来——读臧文涛
第一章 自搔短鬓秋风里
从木心说到董其昌
所谓流量密码,其实是你的DNA动了
当反常识成为常识——告别2021
为什么山东难出大家?
我们是不是太low了
谈一谈书画里的“文心”
今天,我们如何纪念魏启后先生
青年画家应注重“画外功夫”
女神们,请下凡!——从两位山东女画家说开去
文艺评论要警惕“星宿派”
只见江山不见人
跟女明星学文化
当不再色艺双绝,请至少德艺双馨——2017年私人书架
莫忘初心
回归常识
野蛮生长
第二章 谁种幽花细雨边
假如你错过了彭想
哭荣东
心如朗月 笔似清风——李兴杰的花鸟画
袖手无言味最长——郭英培与他的花鸟画
从海滨邹鲁到孔孟之乡——吴泽浩的文化自觉与艺术实践
风景总在险峻处——说说陈龙伟的人物画
张德娜:绘画是永不满足的工作
幸有我来山未孤——李庆杰山水印象
大写意·大尺幅·大手笔·大志向——郭志光与他的巨幅花鸟画
捕捉大时代的微妙悸动——魏晔石油画创作简评
自饶韵致 非关烟云——张玉泰的水墨新语境
有情有趣 挥洒自如——刘书军画钟馗
法度与自由——李济民的中国人物画
陌上花开缓缓归——读李恩成的水墨画
神完气足 明心见性——李承志的花鸟画与书法艺术
当清风拂过心田——我读李学明的扇面画
八旬桂花香更浓——写在单应桂美术馆开馆暨单应桂先生八十寿诞之际
“眼前一黑”之后——我读吴建军的山水画
渴笔营丘壑成画为真知——读孙文韬的水墨山水
李庆杰:传统笔墨与人文情怀
当“克隆”遇到“转基因”——从于明诠书法艺术看传承与创新
创造条件也要“遁”——说说韦辛夷
快乐总是赤条条的——观李学明先生画作有感
尹延新的华丽转身
第三章 万人丛中一握手
刘曦林:我为什么念念不忘
六个男人,与他们的第一个十年——写在“芥英·十年”展览开幕之际
投之苦瓜脸 报之蜜桃臀——刘彦湖“书写的意志”个展随想
有一种搭档叫岳海波李兆虬
在平行世界相遇——“平行·进行——山东青年艺术家邀请展”前言
清风入怀——贾荣志 常朝晖 王宇鹏扇画微展前言
煮酒论英雄 书画看山东——画说山东·中国画名家邀请展前言
花间集——当代青年花鸟画家状态展序
读“尤墨”,永遇乐——“永遇乐——书画小品七人展”前言
参到无言处——潘梦石篆刻艺术工作室展览序
与君同做少年游——万钧祝清跃小品展前言
山在心里 梦在石外——无山·梦石作品展前言
原来你是这样的小胖——写在祝清跃首次个展之前
无水墨 不动向——“水墨动向”第二届当代中青年美术家学术提名展前言
第四章 一生襟抱向谁开
笔墨闯关东——韦辛夷《闯关东》三部曲的双重价值
落墨见高襟——观李学明中国画《高凤翰》
暗夜里的那簇光——韦辛夷新作《苟坝的马灯》观后
以读书对抗精神的荒芜——韦辛夷国画《拾荒者》简析
穿越时空的致意——我读张志民《风雨孔府》
精神的丰碑绘画的丰碑——我读李学明《沂蒙丰碑》
第五章 风流旧仰先贤传
允文允武侠之大者——李苦禅的武术与绘画
柳子谷:颠沛未改兰竹魂
关友声:济南真名士,齐鲁大画家
于希宁:一代梅痴,三魂一心
黑伯龙:人清石冷,平淡天真
第六章 明朝有意抱琴来
一个展览一个城市——浅议济南国际双年展对济南在地文化的激活
冷水沟与李恩成——李恩成《芳华》新书分享会主持词
“致广大”与“尽精微”——山东博物馆“溪山雅集”发言
寻常题材中的意味——“一枝一叶总关情——韦辛夷红竹迎春展”座谈会主持词
花鸟画与当代空间——“花间集”漫谈主持词
李学明与文人画的当代发展——在李学明扇面作品展座谈会上的发言
说不清楚——“永遇乐——关于绘画、文学与幽默的漫谈”主持词
向阳而生——“蜀葵花歌——吴泽浩近作展”座谈会发言
中西合璧·以书入画·与古为新·天人合一——李奇茂先生艺术浅析
停电了,你还能写作吗?——谈谈写作的输入与输出
后记
试读
木心何辜,去世十余年后又一次成为关注的焦点。
2014年,南京大学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卢虹贝发表了一篇论文,题为《木心文学创作中的“文本再生”现象研究》,文中详细考证梳理了木心公开出版的著作中存在的大量非原创性内容。不知为何,这篇沉寂数年的论文,壬寅春节后又被翻了出来,在豆瓣、在微信被广为引用、转发,而且把论文中很谨慎的用语“文本再生”,上升为“抄袭”这样严厉的指控。
文本再、非原创、洗稿、抄袭……无论用哪个词,指向性都已经非常明显。
看到“洗稿”这个时髦的词儿,很难不想到另一个热词——“塌房”。
木心先生要“塌房”了吗?
木心有点丽。
不知道批评他的人,有没有细读过《文学回忆录》。
如果细读过应该知道,木心本人三番五次拒绝出版《文学回忆录》。一开篇的《出版说明》里就说了,“2006年先生归国后,本社曾拟出版这份讲义,未获先生同意,理由是,那不是他的创作”。最后面陈丹青的《后记》里也说了,“日后几次恳求他出版这份讲义,他总轻蔑地说,那不是他的作品,不高兴出。前几年领了出版社主编去到乌镇,重提此事,木心仍是不允”。
木心去世后,陈丹青和出版社还是“悍然”出版了这份讲义,虽然作者栏注明了“木心讲述,陈丹青笔录”,毕竟还是给如今的批评者提供了一个靶子。
《文学回忆录》中木心还说过一句:“我不承认什么文学家、画家。我的内行,是吃喝玩乐。我的序就说我是个玩家。”
只想当玩家游戏江湖的,被捧为大师顶礼膜拜。各种场合不遗余力推介,联系出版社出书,在木心老家乌镇为其建设美术馆……
你说,这怨谁?
木心也不冤。这个木心,指的是陈丹青、广西师大出版社理想国,以及各位文青,共同打造的那个木心。
木心拒绝出版《文学回忆录》,因为他认为这份讲义是根据郑振铎20世纪20年代编著的《文学大纲》讲述的,并不是自己的原创。然而从文本来看,《文学大纲》只是骨骼,最精彩的“肉”还是木心大量的解释与阐发。能够看出木心对中西文化都有着较为全面的了解,其中不乏让人掩卷沉思的灼见。
另外,让木心在文青中奠定地位的,还有他那首叫《从前慢》的小诗。
其他成就,恕我无知,实在不太了解。
由于时代和个人经历的原因,木心的成就肯定是被遮蔽了。但究竟是不是陈丹青所背书的殿堂级的人物呢?
我非常理解陈丹青。他赶上了一个文化断裂的时代,在纽约遇到木心,久旱逢甘霖般痛快,痛快之后就是崇拜,崇拜之后就是感恩,感恩之后,就是要让天下人都知道“他”的好。
这种情况下,不用力过猛反而不正常了。P8-11
前言/序言
笑指凌云得得来——读臧 文涛 韦辛夷 “今朝清晴可喜”——今天 当得起这句话。 暖气停了,春天来了, 紫玉兰也开了。 天气真好,晨光偎进窗 里,是大光明。 榻间看着《会心集》文 稿,心下倏然就生出一片透 亮。 臧文涛要出书了,可喜 可贺!着我写点东西,许久 没有码字了,心手枯涩,便 有些踌躇。翻赏文稿,思绪 渐渐拢来,在《会心》的状 态下“会心”,果然就聚萃了 一些头绪,只好不计工拙, 忝弄月旦。先用两句话概括 一下我心目中的文涛: 文涛其人——“讷于言而 敏于行。” 文涛其文——“纤笔一枝 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 我一直搞不清楚,是什 么原因,让这两种看上去并 不相谐的特质集于他一身? 平日里的文涛,沉静如水, 独步脱巾,一旦看他摇笔行 文,就妙机其微,空潭泻春 ,他弹指间就能飞花摘叶, 缭绕烟尘,身手功夫好生了 得!恰如其名讳“文思如涛” ,想必他父亲大人早有期许 ,早早地把一颗文心的种子 植进他的“一米阳光”里,使 得他“真体内充,返虚人浑” 。 与文涛相识、相熟、相 知也有二十多年了吧?他在 报社当文化记者,那时主要 负责书画艺术板块,我在美 协工作,都是和画家打交道 ,自然交往就多。根据实践 、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 理论;根据由感性认识上升 到理性认识的理论;根据由 特殊到一般的理论;根据两 次飞跃的理论,在一个相对 较长的时间跨度之内,在无 可计数的过往、交际中,得 出了哲学认识论上的结论: 文涛不简单、文涛厉害、文 涛是一个峨峨南山般的存在 ! 在我的认知中,文涛有“ 三力”——亲和力、专业能 力和执行力。试述之: 先说亲和力。 美术圈他熟。全国的和 省里的他都熟,省城“贵圈” 他尤熟。但凡有点模样的画 展都少不了他的身影。通常 在展览现场,他都是静静地 待在一隅,静静地看着台上 人折腾。此时的他静若处子 ,却内心玲珑。领导或画家 或凑热闹的人们与他相晤, 他都会不失礼数地打着招呼 。他能够眼观六路、耳听八 方,记下方方面面的细节, 他这是在为写报道收集和储 备有效信息。 再说专业能力。 常常是上述的展览甫一 结束,他那边的文字稿件就 出笼了,第二天《济南时报 》的文化板块,一准儿刊出 有他署名的报道。其报道行 文规范、滴水不漏、语言精 炼、切中肯綮,让读报的人 看着畅快明了,让参展画家 看着心里舒服,两两适意, 皆大欢喜。 那时不兴什么微信、微 博、公众号,都是靠手写, 后来才是在键盘上敲字,再 后来,智能手机就揽了全活 。在我的印象中,那时候办 展览,如果展览信息官媒报 纸不给登一下,这展览等于 没办,就这么豪横,没办法 (当然,还要上电视,那是 另一个序列,不在此文论及 )。这是他处理日常工作的 方面。 另外,还有更大的一块 ,是他写的**文章,这才 是他思绪飞扬的领地。这才 是他驰骋才华的疆场。这才 是“书之岁华,其日可读”的 学术峻峰。 几十年过来,他给近百 位画家写过鼓吹文章,同时 也写出了为数不少的艺术类 学术**文章。还有参加座 谈会、担任主持人,每每他 都有高论,余不禁叹道,是 水就激湍,是树就摇风,慧 言频出,便成一时光景;嘉 文广布、静谛四方回声。 文涛在业内写文章有“刽( 快)子手”美誉,他文笔犀利 老辣,常常是见人之所未见 ,发人之所未发。如长天瀑 水,一泻千里;如快刀斩麻 ,嘁里咔嚓!时常读着他的 文章在快意涨屏时,心生恍 惚:这是他写的吗?行文中 “冲塔”的气息,笔底下逼人 的气势,似乎与他的温文尔 雅对不上号。定神之后,确 认的确是他写的,此时虽无 唾壶可击,却常常是暗自在 袖中悄悄竖起大拇指!有分 教:在冬若燠火、在夏若嚼 冰,春秋之际,刚刚好,杨 柳依依时春风拂面;秋水伊 人处蒹葭鸣蛩。 数十年来,文涛用功甚 勤,他读书,阅读量极大, 且“胃口”很好,中西通吃。 他的日常工作极其冗忙,即 便这样,他总是利用“三上” (枕上、车上、厕上)去读书 。不但读,他还想;不但想 ,他还用;不但用,他还都 用在了点子上。聚沙成塔, 集腋成裘,日积月累,玉汝 于成,呶,就成就了这本书 。 第三,说说他的执行力 。 如果仅仅把文涛看成是 文章作手,那就小看他了, 他还有极强的公关能力、协 调能力、策划能力和行政能 力。 这几十年来,经他策划 并组织实施的大型美术活动 得有几十个。令我印象最深 的,就是延续了好长时间的 、一年一度的“齐鲁画坛年 度艺术家”评选活动。此项 评选活动成为当时山东中国 画界的风向标,每次当选画 家的评出,都会成为美术界 和社会的热议话题。 他还参与创办了一个高 端美术栏目——《艺周刊》 ,一时间众望所归,风头无 两。凡国内、省内有影响的 美术大咖,纷纷粉墨登场, 无论是学术**、理论文章 ,还是应时展览、美术新作 ,统统笼入彀中,令“圈内” “圈外”周期性地眼热心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