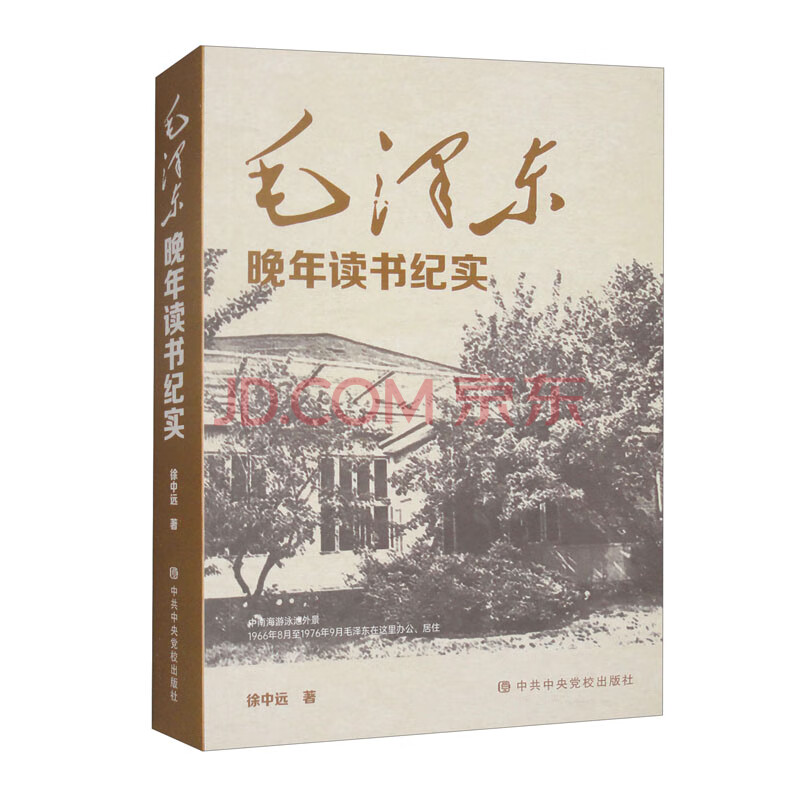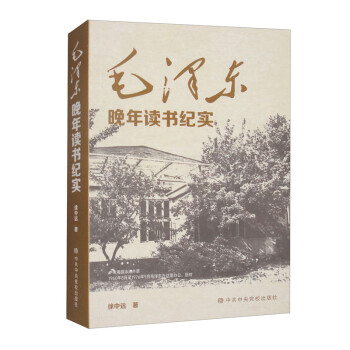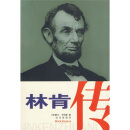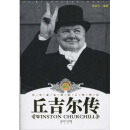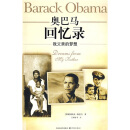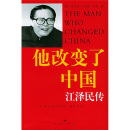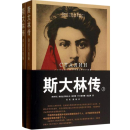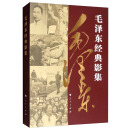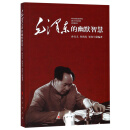内容简介
毛泽东终身酷爱读书,博览群书。不管工作多忙,他每天都要挤出时间坚持读书。进入20世纪70年代,特别是从1971年林彪叛逃事件之后,毛泽东的体质愈来愈差,多种疾病接连不断。在病魔缠身的最后几年,他一直喜爱的散步、游泳等运动几乎全都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他真的是年老了,体弱了,病多了,两腿不能走路了,眼睛看不清东西了,听力也下降了,说话也越来越让人难以听懂了。可是他老人家还日日夜夜一页一页地读,一本一本地看,一笔一笔地画,一字一字地写批注。眼睛看不见了,就让人读;手拿不动了,就让人举着;精装本、平装本重了,就读大字线装本的。白天读,夜里读,常常是通宵达旦地读。是白天,还是黑夜,他老人家是不关注的,吃饭、睡觉、工作、看书,天天如此。吃饭时他也常常要看书,他常说吃饭用嘴巴,看书用眼睛。有时看书忘记了吃饭,有时一顿饭,凉了热,热了凉,热来热去,端来端去,反复好几次,他老人家才能吃上一点。吃的时候,他常常也是大口大口地、以军人的速度很快吃完,然后把碗筷往旁边一推,又全神贯注地看起书来。具体吃什么,每天吃几顿饭,他老人家都不关注,肚子饿了,想吃了,就找东西吃。有时吃两块红薯,喝一杯糊糊,就算一餐饭。他常说:“饭可以少吃,觉可以少睡,书可不能不读啊!”他老人家看书,没有固定的时间,也不分什么时间,吃饭前、会客前、开会前、睡觉前,一有空就看,睡不着觉时也看。他老人家睡眠不好,有时失眠,靠安眠药助睡。吃完药,入睡前,他总是习惯看书。常常看着看着睡着了,睡醒觉接着看。他老人家看书,也没有固定的地方,会议室里、办公桌旁、会客厅的沙发上、卧室的床上、游泳池旁、吃饭桌旁、浴室间、卫生间,到处都有书,随手翻开看。
目录
一、毛泽东晚年爱读什么书
二、读马列著作终身不懈
(一)从毛泽东读第一本马列著作谈起
(二)读《反杜林论》和《资本论》
(三)读《国家与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四)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
三、读逻辑学论文和专著
四、读中国五部古典小说
(一)把《红楼梦》当作历史读
(二)“《水浒》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
(三)“看《三国演义》不但要看战争,看外交,而且要看组织”
(四)读《西游记》,“要看到他们有个坚强的信仰”
(五)“《聊斋志异》可以当作清朝的史料看”
五、读鲁迅著作
(一)鲁迅著作伴终身
(二)读鲁迅的小说和杂文
(三)爱读爱书写鲁迅的诗
六、读二十四史
(一)二十四史是毛泽东晚年最爱读的、读得最多的书籍
(二)读二十四史时写的批注
(三)毛泽东是怎样读二十四史的
(四)读二十四史的视角
七、读中国古诗词曲赋
(一)终身爱读屈原的诗作
(二)最爱读唐代“三李”的诗作
(三)也爱读晚唐罗隐的诗
(四)圈画最多的是辛弃疾的词
(五)爱读中国历代名家赋作
(六)读古代诗话
八、读报章杂志
(一)读报章杂志每天都不能少
(二)每天必读的一报一刊
(三)爱读《人民日报》的学术、理论文章,对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哲学》《史学》等专刊特别有兴趣
……
九、潜心学习自然科学
十、读笑话书
十一、博览群帖,研究书法
十二、读《智囊》
十三、读《-种清醒的作法》
十四、读《柳文指要》
十五、读《容斋随笔》——生前要读的最后一部线装书
十六、读新印的大字线装书
十七、毛泽东读书的启示
附录
后记
试读
《毛泽东晚年读书纪实》:
这些意见代表了当时中国共产党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基本看法。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这个问题后来演变成为中苏论战的一个重要方面。
毛泽东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中提出,哲学家都是为政治服务的。他说,冯友兰在《四十年的回顾》中,用自己的事实驳斥了所谓哲学不为政治服务的说法。
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赞同性意见主要有两条:
第一,关于十月革命普遍规律和各国具体特点相结合的问题。《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认为十月革命“树立了一个榜样,表明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内容应当是怎样的”,各国社会主义革命“在主要方面和基本方面是一致的”;“但是它在每一个脱离了帝国主义体系的国家中必然具有自己特别的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这些形式和方法是由每一个国家发展的历史、民族、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人民的传统,以及某一个时期的国际环境产生的。”这段话甚合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一贯思想,无疑受到他的赞赏。他说:我们始终强调要按照十月革命的道路办事,要讲“任何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内容”都是一样的,这就和修正主义者对立起来了。“每一个”国家都“具有自己特别的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这个提法好。莫斯科宣言中,就讲到了普遍规律和具体特点相结合的问题。
第二,关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必然性。《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社会中的阶级斗争的整个进程,不可避免地会使社会主义用革命手段代替资本主义”。由“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便“产生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必然性”。这个观点同样深为毛泽东所赞赏。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要“代替”资本主义,是“不可避免”的,要“用革命手段”。这个提法好,不能不这样讲。“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必然性”,这个“客观必然性”很好,很令人喜欢。既然是客观必然性,就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也就是不管你决议里是赞成还是不赞成,它也还是“客观必然性”。
不过,毛泽东也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必然性提出了他的疑问:“革命为什么不首先在西方那些资本主义生产水平高、无产阶级人数很多的国家成功,而首先在东方那些资本主义生产水平比较低、无产阶级人数比较少的国家成功,例如俄国和中国,这个问题要好好研究。”
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在资本主义有了一定发展水平的条件下,经济愈落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愈容易,而不是愈困难。人愈穷,才愈要革命。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就业人数比较多,工资水平比较高,劳动者受资产阶级的影响很深,在那些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现在看并不容易。这些国家……重要问题是人的改造。”即是说,“在目前的情况下,越往西越富,革命也越困难”。
那么,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必然性又如何体现呢?毛泽东虽然提出了这个极有意义的问题,也看到了理论与现实的反差,但是无论是研究思路还是结论都是值得讨论的。毛泽东认为列宁的观点是正确的。列宁指出:“由于历史进程的曲折而不得不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那个国家愈落后,它由旧的资本主义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系就愈困难。”唯其如列宁所说,由于历史进程的曲折性而不得不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落后国家才需要有一个相当历史时期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又如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问题。毛泽东认为,《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说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说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都没有提到对敌人的镇压,也没有提到阶级的改造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他不仅重申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和“国家的性质是一个阶级压迫另_个阶级的机器”,而且认为即使共产主义建成后国内没有需要压迫的敌对势力了,对于国外的敌对势力,国家的性质也还没有变。与此相关联,他认为《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无产阶级专政是真正的民主”的说法,也“不确切”。因为民主只能说有资产阶级的民主,有无产阶级的民主;有少数人的民主,有大多数人的民主。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中,发表了富有创造性的意见。例如向共产主义过渡及共产主义的阶段性问题。对于这样一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新问题,毛泽东提出了革命的多阶段说。他认为,一种生产关系代替另一种生产关系是质的飞跃,就是社会革命;由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转变为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是生产关系的变革,因而也不能不是革命。
……
前言/序言
2011年12月26日,是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诞辰118周年。毛泽东虽然离开我们已经35年了,但全国各族人民包括湖南家乡的人民,曾经与他一起战斗、工作、学习、生活过的同学、同志和战友,曾经为他服务过和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员,当然也包括我,始终无比敬仰、无比爱戴、无比怀念他。说起毛泽东,广大共产党员,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年岁大一些的老同志、老工人、老农民、老将军、老战士,都会有滔滔的话语。亲历的往事、生动的故事、种种逸闻趣事,讲不完,说不尽,道不全。毛泽东永远是我们心目中最敬爱的、最难以忘怀的伟大的导师。
我们是从1966年开始为毛泽东做图书服务和管理工作的。直到1976年9月9日,毛泽东离开之后,我们几个有关的同志依然像往常一样,一直伴随着他老人家生前阅读批注过的数万册图书,依然每天进出在他曾工作生活长达27个春秋的中南海故居。故居的主人虽然随着流逝的岁月离我们越来越远,然而,每天每时,当我们走进故居,看到故居的主人生前用过的一件件物品、一直很喜爱的一册册字帖和一件件古今著名人物的字画,整理抄录一册册他老人家生前读了又读而且写了许多批注的图书的时候,我们的脑海中不由得就浮现出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和一件件往事,仿佛他老人家仍在我们身边。他老人家仍是那么神采,那么慈祥,那么幽默,那么令人敬仰、令人难忘。他老人家一直活在我们心中。
毛泽东终身酷爱读书,博览群书。不管工作多忙,他每天都要挤出时间坚持读书。进入20世纪70年代,特别是从1971年林彪叛逃事件之后,毛泽东的体质愈来愈差,多种疾病接连不断。在病魔缠身的最后几年,他一直喜爱的散步、游泳等运动几乎全都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他真的是年老了,体弱了,病多了,两腿不能走路了,眼睛看不清东西了,听力也下降了,说话也越来越让人难以听懂了。可是他老人家还日日夜夜一页一页地读,一本一本地看,一笔一笔地画,一字一字地写批注。眼睛看不见了,就让人读;手拿不动了,就让人举着;精装本、平装本重了,就读大字线装本的。白天读,夜里读,常常是通宵达旦地读。是白天,还是黑夜,他老人家是不关注的,吃饭、睡觉、工作、看书,天天如此。吃饭时他也常常要看书,他常说吃饭用嘴巴,看书用眼睛。有时看书忘记了吃饭,有时一顿饭,凉了热,热了凉,热来热去,端来端去,反复好几次,他老人家才能吃上一点。吃的时候,他常常也是大口大口地、以军人的速度很快吃完,然后把碗筷往旁边一推,又全神贯注地看起书来。具体吃什么,每天吃几顿饭,他老人家都不关注,肚子饿了,想吃了,就找东西吃。有时吃两块红薯,喝一杯糊糊,就算一餐饭。他常说:“饭可以少吃,觉可以少睡,书可不能不读啊!”他老人家看书,没有固定的时间,也不分什么时间,吃饭前、会客前、开会前、睡觉前,一有空就看,睡不着觉时也看。他老人家睡眠不好,有时失眠,靠安眠药助睡。吃完药,入睡前,他总是习惯看书。常常看着看着睡着了,睡醒觉接着看。他老人家看书,也没有固定的地方,会议室里、办公桌旁、会客厅的沙发上、卧室的床上、游泳池旁、吃饭桌旁、浴室间、卫生间,到处都有书,随手翻开看。
1972年之后,他老人家看书大多是半躺着看的,看的大多是大字线装书,因为线装书比较轻,又是竖排的,一册一册拿在手里看起来很方便。从1972年底到1976年初,他先后看了129种数百万字的新印的大字线装本书刊。没有大字本的,就用放大镜一行一行、一字一字地看。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毛泽东说已经收到马克思给他的请柬,他知道留给他的时间不是很多了。所以,他每天手不释卷,不分昼夜地读书。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地,在外出的列车上,走到哪里,书就带到哪里。无论在北京还是在杭州、武汉等地,毛泽东日常生活的地方什么最多?书籍最多。他睡觉的木板床上总是大半边放满了书,只留下一个人睡觉的空地方。有一次,他病情加重,发烧到39℃,还要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