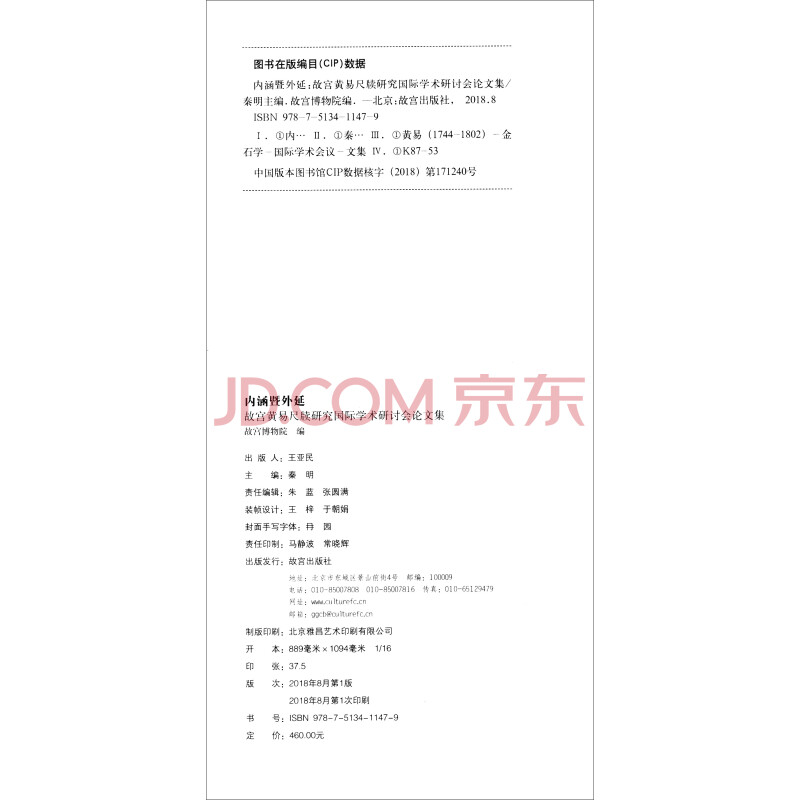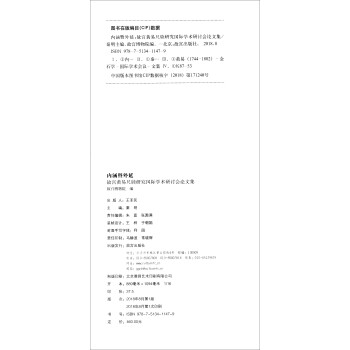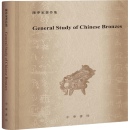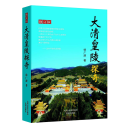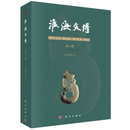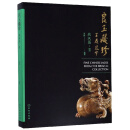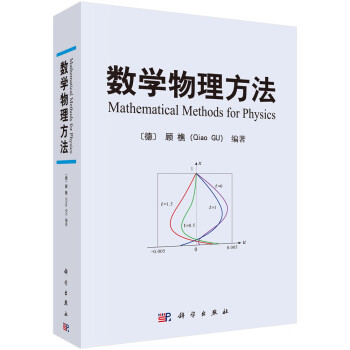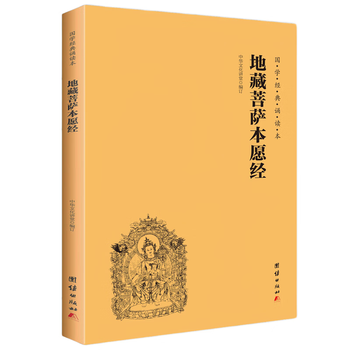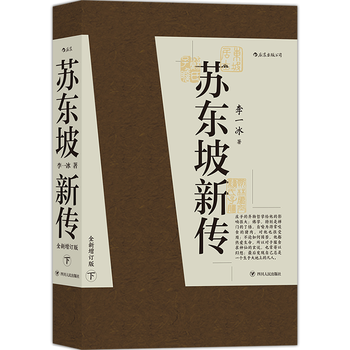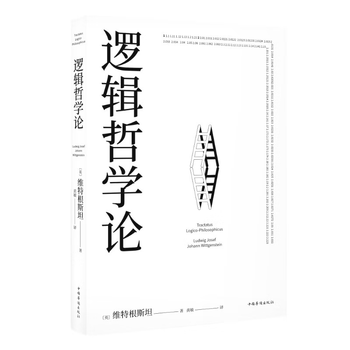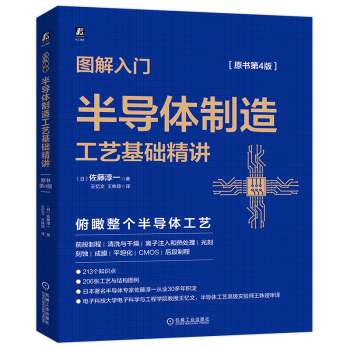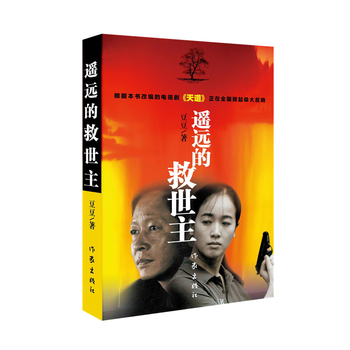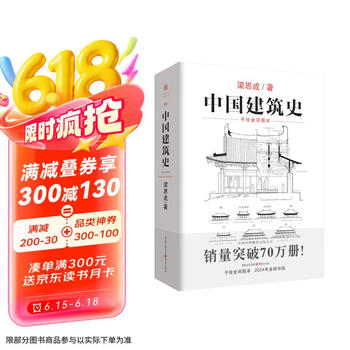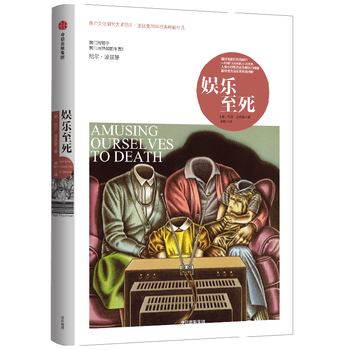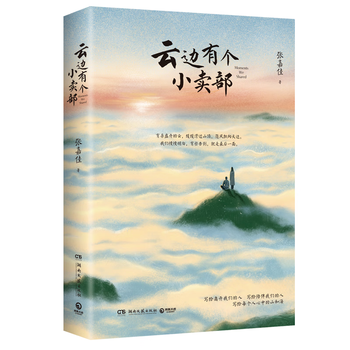内容简介
本次会议推动了黄易尺牍的整理和研究。近年来尺牍越来越引起学界不同领域的重视。前年秦明先生等整理出版故宫藏黄易手札时,我写了一篇序,专门谈到了整理稿本尺牍的重要性。2017年3月初,凤凰出版社出版了上海图书馆藏的《庞虚斋藏清朝名贤手札》。2017年8月至10月,上海博物馆举办了“遗我双鲤鱼:上海博物馆藏明代吴门书画家书札精品展”,出版了图录和论文集。信札的整理、研究、出版将是今后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内重要的学术工作。本次会议不但走在了学术的前沿,也实实在在地推进了尺牍的整理和研究。
围绕着尺牍而展开的学术工作,大致可以分为整理和研究两方面,两者有区别也有联系。整理工作应该努力和研究工作结合在一起,整理为研究服务,研究带动整理,因为某些尺牍只有在积累了一定的研究之后才能准确释读。整理释文,提供简单的注解,固然也是学术贡献,但若能够从中发现问题,提出有意义的议题,进行比较深入的分析讨论,则更为理想。我觉得今后参与古代书画(包括书札)整理的人们,可以思考如何在整理工作中发现一些有意思的问题来分析研究。
本次会议的主持者秦明先生多年来坚持不懈地推动黄易的研究工作。他在继故宫博物院科研课题——黄易金石学研究(一)(二)完成之后,又将开展黄易金石学研究(三)的项目——以金石学为主线的《黄易全集》的整理编纂与出版,这无疑将是黄易研究重要的文献工作。在主要文献工作接近尾声之时,如何将黄易研究推向深入,也将成为我们面临的新挑战。
目录
序一 回顾与回响
序二 《故宫黄易尺牍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序
黄易《小蓬莱阁金石文字》拟目——兼谈作者的编书思想
黄易及其友人的知识遗产:对Recarving China's Past(《重塑中国往昔》)有关问题的反思
武梁祠画像是伪造的吗?以汉代材料验证之
散见黄易尺牍丛考
故宫博物院藏黄易致王毂札考释
故宫藏黄易致张爱鼎五札补证
辽宁省博物馆藏《秋盒书札》考及相关问题(修订稿)
国家图书馆藏《黄小松友朋书札》综述
国家图书馆藏赵怀玉致黄易札考释
翁方纲致黄易《河南札》小考
翁方纲致黄易《新锓札》小考
《黄小松辑释吉金拓本》综述
故宫藏与黄易相关之晋唐碑帖拓本概述
武梁祠画像石题字黄易监拓本考
黄易与《七姬权厝志》的石墨因缘
孝堂山石祠上的后人题刻——由黄易嘉庆元年细拓石祠画像想到的
黄易与邹城北朝佛教摩崖刻经
遍访齐鲁山幽处,尽拓北朝石刻书——浅论黄易对山东北朝摩崖石刻的贡献及影响
黄易隶书风格探究——以“书画册”“隶书册”作品为主
黄易临《郭有道碑》三种——参与李铁桥“戏作”的可能性
由黄易双钩古碑衍生的相关书学信息初探
故宫藏黄易《携琴访友图卷》考——兼谈黄易早期绘画中的古琴要素
故宫藏黄易绘武亿像读记
黄易书画中的“文人气”探析——以广东省博物馆藏品为例
上海博物馆藏《余集画黄小松像》考辨
黄易小像研究补证
散论黄易题签的禹之鼎摹绘赵孟頫自画像
黄易《嵩洛访碑图》中的嵩山历史建筑
清黄易《明湖秋水(烟柳柴门)图卷》本事、逸事索解
18世纪后期文化商品的价格:以黄易的朋友圈为中心
黄易与何道生交游考略一以嘉庆五年南池嘉会为中心
邓石如与黄易交游新证——兼议清中期皖派与浙派的篆刻交流
孙星衍与黄易的金石交
艺术与学术之间——关于焦山鼎的再思考
乾嘉时期的秦汉瓦当收藏
《泉文》与黄易的钱币收藏
上海博物馆藏黄易篆刻简述
天津博物馆藏黄易铭砚小考
故宫藏《小松集拓研铭册》述考
故宫藏明清碑形墨
故宫明清尺牍文物数字化影像采集札记
附录:故宫藏黄易友朋书札(补充)
故宫藏黄易友朋书札(补充)释文
前言/序言
2017年3月29日至30日,“内涵暨外延:故宫黄易尺牍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济南市召开。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三十多位学者提交了论文,我受会议组织者秦明先生的委托,作会议总结。经过一年的修改,会议论文结集出版,我又受命作序。在此我将自己在济南会议上作的总结发言稍作扩充整理,发表一点意见,供大家参考。
我在济南的总结中,指出了本次会议取得的三个主要成果。
一、本次会议虽然以尺牍研究为名,但由于黄易的经历丰富,研究、收藏的面广,所以会议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远远超出了尺牍。学者们提交的论文涉及黄易本人的艺术(绘画、书法、篆刻、双钩等),黄易的收藏(拓片、钱币、吉金、瓦当等),黄易的生平(交游、地方官在他的金石生涯中的作用等)。三场主旨演讲也涉及了黄易金石著录拟目所反映的编书思想、围绕着武氏祠的一场辩论、和黄易有关的石室等遗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次会议是继2009年11月故宫举办的“黄易与金石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后的又一次关于黄易研究的学术盛会,对于推进黄易和清代中期金石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二、本次会议的另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学者们在论文中公布了不少珍贵的资料,譬如说,山东博物馆藏《黄小松辑释吉金拓本》。2012年7月,我曾和秦明先生一起观看了这部册页,当时就觉得非常有价值。收藏青铜器,在宋代曾经成为风气,在接下来的元明时代则逐渐衰落。在我曾经研究过的明末清初,金石收藏主要是石而非金,当时的金石学著作也是如此。在乾嘉的后期,文人收集吉金开始逐渐流行起来,阮元、伊秉绶、孙星衍、张廷济、吴荣光等都有收藏。道光以后风气更盛,陈介祺、吴云、李宗岱、潘祖荫、吴大潋等都竭力收藏“金”。过去我们对黄易收藏的石刻拓本比较熟悉,而山东博物馆所藏的这套《黄小松辑释吉金拓本》,全是“金”,对我们了解黄易收藏活动的广度,很有帮助。
这套吉金拓本也可以澄清学界的一些错误认识。我在美国教书二十年,虽然在两年前海归,但是对于海外艺术史界的动态还是有所了解的。近些年来,海外和港台的学者关注从传统金石学向现代考古学的转向,“器物”这个概念的出现,以及中国文人何时开始收藏三维的雕塑。在传统的雕塑中,佛像是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从什么时候文人开始收藏立体的佛像呢?有位美国学者说是从王懿荣开始的,因为王懿荣的妻子信佛教,所以收藏佛像。这明显是错误的。山东济宁博物馆收藏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