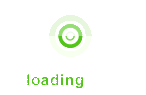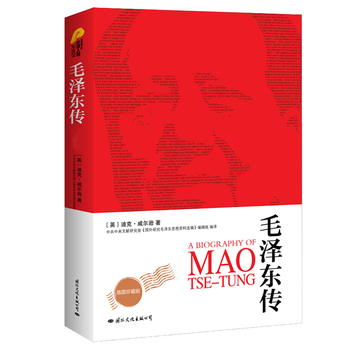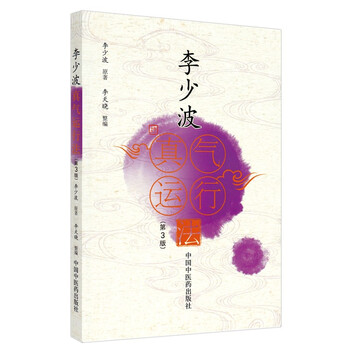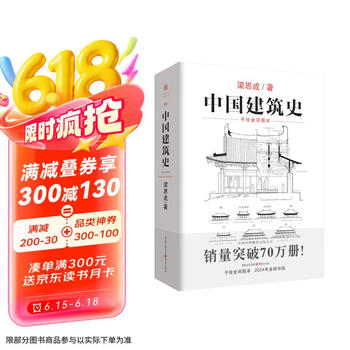内容简介
我遇到一位名叫巴列霍的病人,他得了一种不停打嗝的怪病,医生们都束手无策。我试图用催眠术给他治病,却遭人暗中阻挠。
我被人跟踪,又跟踪了别人。与此同时,我叉偶遇过去一起学催眠术的朋友,得知了我们共同朋友的自杀之谜。
记忆深处的噩梦对我紧迫不舍,我正在慢慢失去同现实的联系……
精彩书评
★《佩恩先生》是波拉尼奥最初的创作成果之一,却已展露出他那炼金术士般的耀眼天赋,他能将生活中的绝境炼成危险的谜团。
——《出版商周刊》
★《佩恩先生》留有未解之谜,在清晰和怪异间取得了非常吸引人的平衡。
——《泰晤士报文学增刊》
目录
作者手记
佩恩先生
声音的尾声:大象之路
试读
《佩恩先生》:
我立刻站到巴列霍身边。巴列霍翻了一下身,张了张嘴,但是没有说话。雷诺夫人用手捂住了嘴,仿佛要阻止自己喊出声来。房间的寂静仿佛充满了孔洞。
我把手停在离床头三十厘米的地方,开始等待。病人的瘦削面孔胆怯地展露在我面前,他脸上现出一切被关在医院里一段时间之后的人所共有的那种古怪的耻辱表情。其余部分都显得模糊不清;一缕缕的黑发,被睡衣遮盖得不严的脖子,没有汗渍的光洁的皮肤。在房间的安静中,只听到他的打嗝声。我知道,我将永远不能够描绘出巴列霍的面孑L,至少无法描绘出在这次唯一的会面中我所看到的样子;但是打嗝,那种呃逆的性质——它包裹着一切,只要稍微听一下,或者说,你几乎不需要真正去听就会发现这一点——任何描绘都办不到,同时又与任何描绘相符,就像一种能出声的细胞外质或某种超现实主义发现。
我所说的“呃逆的性质”的特点之一,或许是,或在我看来是:这性质的根源来源于自身。我们都知道,打嗝是一种肌肉的收缩,是引起间断且猛烈的呼吸的膈膜痉挛,它会引发一种间歇性的独特声响;然而,巴列霍的呃逆却相反,它似乎掌握了全部自主权,不理会我的病人的肉体,仿佛不是我的病人忍受呃逆的痛苦,而是呃逆施加给他痛苦。这便是我所想的。
我在床边待了两个小时。幸好,只过了几分钟,那个穿长外套的人就走了。门关时发出的轻微声音把迷失在凭空想象的小路上的我拉回来,我把注意力集中在疾病和重症病人即巴列霍身上。我愉快地发现,和两个女人及病人在一起,就像一个人独处,但是在一种和谐的、轻松的、像哲人说的比钟表快的孤独中。
“他醒了。”雷诺夫人低声说。
我望着她,把一个手指放在嘴上,示意安静,巴列霍在睡觉,几乎一动不动,他的虚弱很明显。巴列霍夫人站在她丈夫旁边,在床头的另一端,面对我。我对她打了个手势,让她躲开。当顺从的巴列霍夫人回到床尾时,我发现雷诺夫人的面色突然变白了。巴列霍睁开眼睛,望着他妻子,结结巴巴地说了两三个模糊不清的字。他在说胡话。然后闭上了眼睛,让人觉得他睡得很平静。我没有动。我感到仿佛有一只微小的但是很重的蜘蛛在我那整个这段时间一直悬在空中的手背上爬。
走向门边时,我感到极为疲倦,肩部疼痛得仿佛支出了过分多的体力,没有兴致说话。我想找个空旷的地方咳嗽,在那里不会打扰任何人,并想在夜晚临近的时候一个人走路。
我坚信,我的病人一定能康复,我怀着这样的希望,古怪地觉得我不仅和这两个女人联结在一起——她们正在从房间的不同角落望着我,而且和不知道这里所发生的事情的大多数巴黎居民联结在一起。
巴列霍夫人疑感地望了望我。
“还有希望。”我走到门边时平静地说。
雷诺夫人站在窗前没有动。她看向我(然而,她看到的并不是我),然后打开了百叶窗。
“还有希望。”我微微一笑,同时试图在我朋友的表情中寻找某种东西,一个信号。
“再见,佩恩先生。”我在雷诺夫人的嘴上猜出了一种低语。
我明白,她是表示感谢,她要留下来和巴列霍夫人在一起。没有别的。巴列霍的打嗝停止了;我是后来知道的,因为当时打嗝声仍然在我的脑海里回荡。我感到幸福,这很正常。
……
前言/序言
多年前,1981年或1982年,我写了《佩恩先生》。它的命运不同平常,且有点冒险。它以《大象之路》为题获得西班牙托莱多市政府授予的费利克斯·乌鲁瓦延中篇小说奖。在此前不久,它以另一个名字在另一次省级比赛中获得提名。前者获得30万比塞塔。后者,我想我记得,获得大约12万比塞塔。我的书在托莱多出版,并让我担任下一次比赛的评委。在另一个省首府,我被人们忘得比我后来忘记他们还快。我一直不知道那本书是否出版了。这些情况,我在《地球上最后的夜晚》中的一篇小说里都讲述了。时间,是十足的幽默家,后来它让我得到一些重要奖项。但是任何一项奖也不如我在西班牙各地获得的奖重要,那是一头红皮毛水牛为生存而必须外出捕食而获的奖。我作为一个作家,从来也不像那时感到那么骄傲和不幸。关于《佩恩先生》,我可以再说一点。我讲述的一切,都是在现实中发生的:巴列霍的呃逆,轧死居里的那辆马车,居里和催眠术的某些方面有密切关系的最后一项工作或最后的某项工作,没有好好为巴列霍看病的那些医生。佩恩本人是真实存在的。若尔热特在她那充满激情、痛苦、无助的回忆录的某一页上提到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