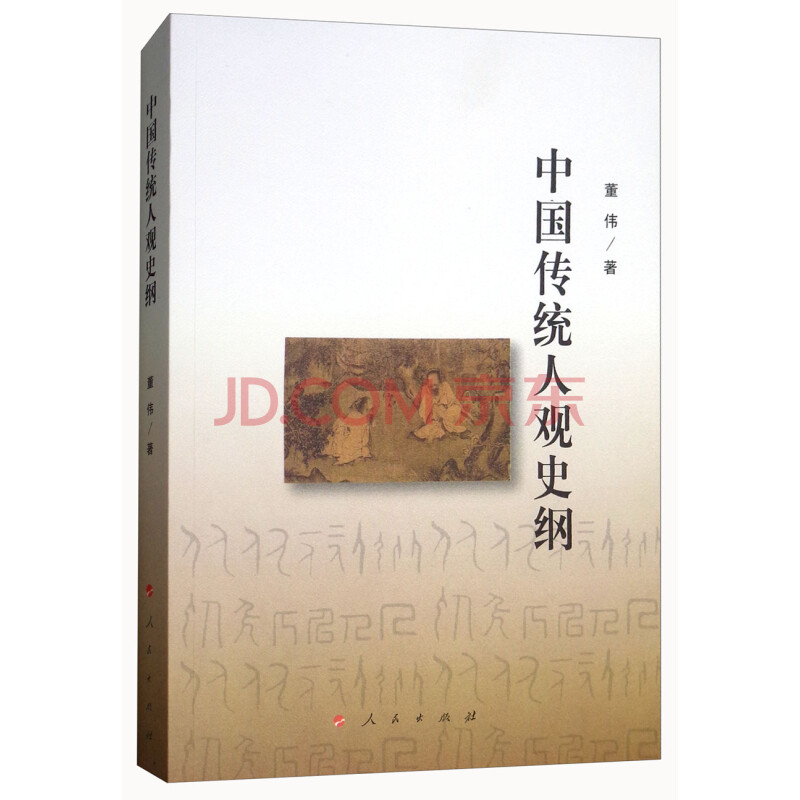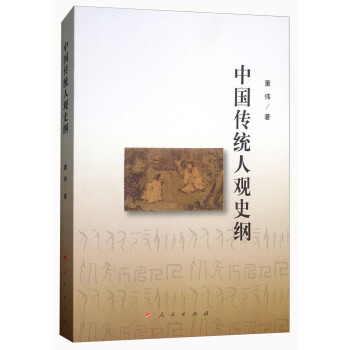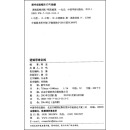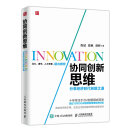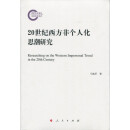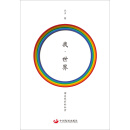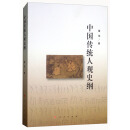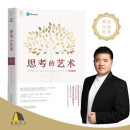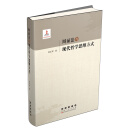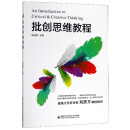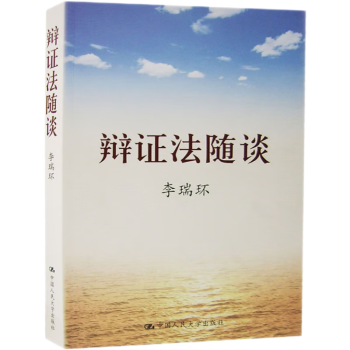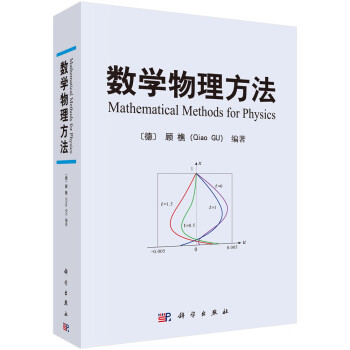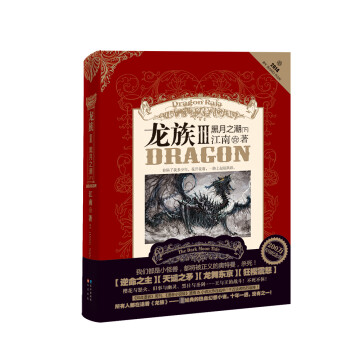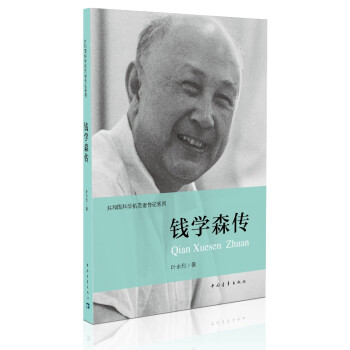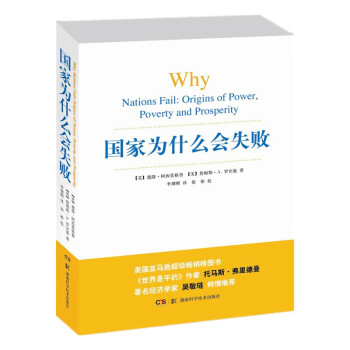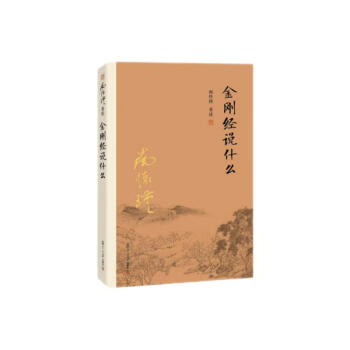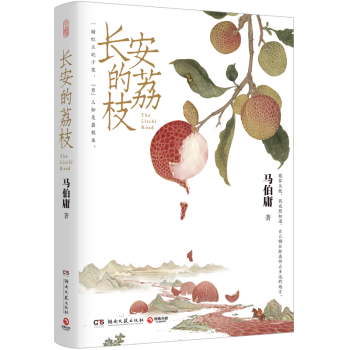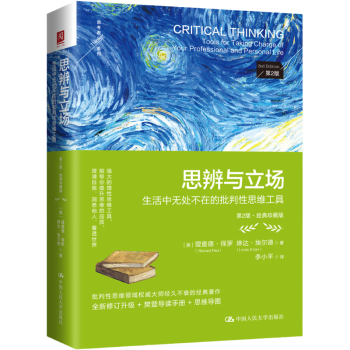内容简介
人性为何,人、禽有无分别,这是中国文化讨论何以谓人的起点。中国文化中的人性观复杂多样,不是性善、性恶之说可以概括的。人性之外,对于人的能力与价值,中国文化既有夸张又有贬低。中国文化对人的生理的认识深受关于天人关系看法的影响。在生死问题上,中国文化突出了人文精神的一面,这种人文精神也反映在圣人观上。在天人关系中,中国文化既讲天人合一,也讲到天人相依、天人相分与互胜;传统美学中的人观其实也可以看作是天人关系的一部分。关于人与社会的关系,中国文化讨论零散,但对于人性与政治之关系却有较为系统的理解。
试读
《中国传统人观史纲》:
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现代意义的心理学,但也非常关注人的各种精神现象。需要注意的是,中国文化对于人的心理倾向的理解,主要并不是为了知道“人是什么”,而是为“成人”、为修养。不知道人有多少种以及什么样的心理特征无甚紧要,只要人能修道成圣。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文化解释心理现象多与本体、形而上有关的原因,显示了中国文化对人的精神认识的一个独特视角。中国文化谈人的各种精神现象,多是散见的,少有系统的讨论,术语也是一个逐渐丰富的过程。
一、心
“心”是中国文化一核心理念。中国文化的主题之一就是来认识、应对这个心。各家论心,众说纷纭。心在中国文化中至少有五层含义,一是生理之心,二是一种心理活动、心理功能,三是指精神的我,四是天、道、性与人的一种联结,五是本体意义上的宇宙心①。
所以,理解中国文化中的心观念,虽然也要以生理之心为基础,但更要脱离肉体心而把它理解为一种性、一种能动性。如朱子所说:“程子所谓心如谷种,仁则其生之性是也。然但谓之仁,则人不知其切于己,故反而名之日人心,则可以见其为此身酬酢万变之主,而不可须臾失矣。”(《孟子集注·告子上.“仁人心”章》)
(一)先秦儒家说心
1.孔孟说心
在孔子那里,心有当代人所谓“意志”义。如,孔子说自己能“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
也可以指心思、倾向性。孔子批评那些平时不知道该干些什么的人,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论语·阳货》)
孔子谈心无多。至孟子,对心就喋喋不休,无怪乎后人称心学远承孟子。
孟子以心指精神和心意活动的总体。他告知梁惠王:“《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孟子·梁惠王上》)孟子自道人生理想,“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詖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孟子·滕文公下》)
心也是道德本源。孟子提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又举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为仁、义、礼、智之端。(《孟子·公孙丑上》)后面又讲:“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性善(仁义礼智)的根源在心。但心何以有四端?孟子是通过类比得出的,他说:“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孟子·告子上》)
心、性相联,由孟子肇其端。孟子道:“尽其心者,知其性也。”(《孟子·尽心上》)尽其心则能知其性。
但孟子也看到了心的难以把捉性。他引孔子的话说:“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乡。惟心之谓与?”(《孟子·告子上》)所以,对于心的把捉就是修养的关键之一。孟子认为首要在“求放心”——“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心会放,也就是承认了外物对心的引诱;同时,也暗示了心有被动性的一面。
孟子又首倡心具知之能。他说:“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孟子·告子上》)心能知,是天所予人的一种能力,但孟子并没有明指能知的心就是肉体生理之心,后来的儒家学者也大都不以肉体心作为能知之心。
孟子论心,很少以心与私、欲等贬义相关,这是他不同于后儒的地方。只有一处,孟子提到:“养心莫善于寡欲。”(《孟子·尽心下》)孟子还提出了赤子之心,他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孟子·离娄下》)
……
前言/序言
关于人观、人学研究应该涉及的范围,本书取义较狭,就是从具体的人出发,看中国文化如何理解人的本性、精神活动、生理以及由此生发的人与宇宙、社会的关系等。有学者认为,诸如人生观之类也都应该划人人学,但依笔者之浅见,果真如此,似乎没有什么学问不可以被称作人学了。
在本书的叙述中将会看到,人禽(物)之别是中国文化讨论何以谓人的起点,其中,有学者强调人之德,有学者强调人之能,也有学者强调人的社会性。但中国文化讨论人最多的还是人的本性问题(包括人的心、情、欲、意等都要与本性相联系才能被理解),儒家主流以孟子为代表指出人性本善,但荀子则认为人性恶,道家强调自然本性,法家则指出人的自私性,佛学讲二性论。人性之外,中国文化有夸张人的能力与价值的观点,但也存在贬低人的能力与价值、存在反智主义的一面。中国文化对人的生理的认识受哲学观念(如天人合一观)影响很深,因为缺乏实证研究传统,中国文化在认识人的生理时多有想象成分,但中国文化中的养生学、中医学仍有它难以替代的价值。在生死问题上,儒家重生的价值,道家以生死为自然循环,佛学泯灭生死的界限。传统文化中各学派以各自的圣人观作为生命价值的追求。在天人关系中,中国文化除了强调天人合一之外,也讲天人相依、天人相分与互胜。中国文化中的人观也部分地反映在传统美学中。虽然中国文化没有现代意义的“社会观”,但作为一种现实,中国文化也讨论了人与社会的相依性、社会对人的戕害,且对于人性与政治之关系有较为系统的理解。
拙著有几点还算属个人心得。首先是对性善论者如何看待不善做了勾勒;其次,提出中国文化中人性本体性的问题;再次,对天人关系的讨论,突破那种仅仅从天人合一或者天人相胜的角度来看待的局限;第四,在对“命”的讨论中,揭示中国文化有对“命(运)”超越的思想;第五,单独讨论了艺文中的人观;第六,对社会与人的关系做了单章陈述。虽然各种讨论都不详尽,但希望能为他人进一步研究中国文化中的人观提供必要的线索。
这是一部讲“是什么”的书,着重于对中国文化中人观本来面目的直接呈现,以概念为纲,按照主题的历史变迁来叙述,没有刻意从中寻找内在的逻辑。不能否认有些论题的历史有着逻辑上较强的因果联结,但对于中国文化来说,对相同题目的讨论,更主要与不同作者的感悟、现实对他的触动有关,后人的观点与前人的论述在因果关系上很可能只是众多因果链条中的一个。
本论著时间下限为1840年,进入近代以来的人观变迁不在论说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