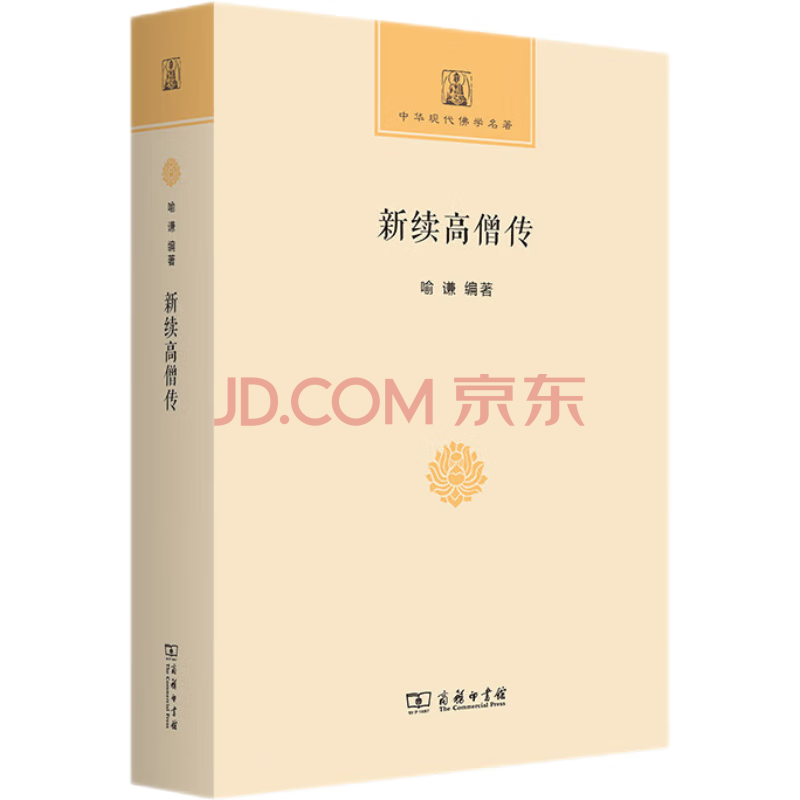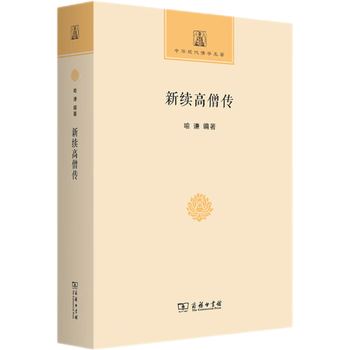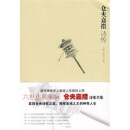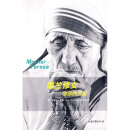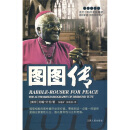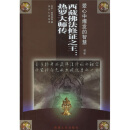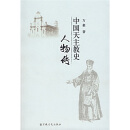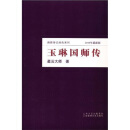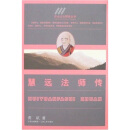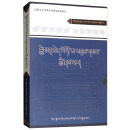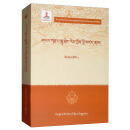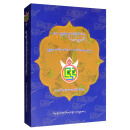内容简介
《新续高僧传》为高僧传记,上自北宋,下迄清末宣统年,千百年来,硕德耆宿,莫不采录。历经五年,成书六十卷。民国喻谦编著。此系续赞宁等之宋高僧传而作,集录北宋至民国初年凡九百余年间之高僧事迹。全书计分十篇,依次为译经篇、义解篇、习禅篇、明律篇、护法篇、灵感篇、遗身篇、净读篇、福兴篇、杂识篇等,总收正传788人、附传628人,计有1416人。
目录


试读
《新续高僧传/中华现代佛学名著》:
明五台山圣光寺沙门释福登传
释福登,字妙峰,姓续氏,平阳人,续鞠居之裔也。生秉奇姿,唇掀齿露,鼻昂喉结。七岁,失怙恃,为里人牧羊。年十二,祝发。携一瓢,至蒲坡,行乞村市。夜栖文昌阁庑下,阁为山阴王所建。一日,王晨出游,值登裴回阶间,见而异之,谓阁僧曰:“是子五官皆露,而神凝骨坚,他日造诣殊未可量,曷善视之?”顷之,地大震,屋宇倾覆。登压于下,三日不死。王闻,益奇之。因修中条栖岩兰若,使居焉。登乃闭关习禅,取棘刺列四旁,以绝依倚。不设床坐,昼夜鹄立,三年心忽开悟。始至介休山,听讲《楞严》,遂受具戒。策杖南走,遍参知识。浮南海,礼普陀而归。复于中条深处,诛茆辟谷,日饮勺水。又三年,大有会心。
山阴王建梵宇于南山,延登居之。登每念二亲幽灵未妥,卜吉迁葬,刺舌血书《华严经》一部,欲报劬劳,借感人天。复下山,设无遮大会,结文殊万圣缘。时明神宗御极,皇储久虚,遣官武当,祷祈请乞,礼视高媒。登闻之,乃曰:“吾徒凡所为,皆为国报本。今宜专诚尽忠,为皇上祈子。”乃启会,至百二十日,九边八省缁白奔赴者,道路不辍。事毕,一钵飘然,结庵芦芽。期年,皇长子生,奉敕就芦芽建华严寺,造万佛铁塔于山巅,加赐金帛,命往秦晋中州饭僧。已,忽念故山,往修万固寺三载。塔殿楼阁,焕然一新。渭川河水病涉,宣府西院议建大河桥,登应命至,度之水阔沙深,乃建桥二十三孔,亦竟成。
尝愿范金成三大士像,以铜为殿,送三名山,各就其显化之地祀焉。己亥春,杖锡潞安,谒沈王。王适造渗金普贤像,送蛾眉。登言铜殿事,王问费几何?登曰:“每座须万金。”王欣然愿造峨眉者,即具辎重,送登至荆州,听其监制,用取足于王。殿高广丈余,渗金雕镂诸佛菩萨像,精妙绝伦,世所未有。殿成,送至蛾眉。大中丞霁宇王公抚蜀,闻登至,请见问心要,有契。公即愿助南海者,乃采铜于蜀,就匠氏于荆门。工成,载至龙江。时普陀僧力拒之,不果往。遂卜地于南都之华山,奏圣母,赐建殿宇安置,遂成一大刹。登乃造五台者,所施皆出于民间,未几亦就。乙巳春,躬送至五台,议建台怀显通寺。上闻,遣御马太监王忠,圣母遣近侍太监陈儒,各赉帑金往视,卜地建殿安奉。以丙午夏五月,兴工鼎新,创立大殿。前后六层,周匝楼阁,重重列耸,规模壮丽,赐额“大护国圣光永明寺”。工竣,先事峨眉,继事南海。会倭夷构难,海氛未靖,中途而止。乃三卜三吉,至得宝华山。诣京都奏请,特敕许之,赐予有加,慈圣太后更赐造寺金及藏经、佛像、幢幡之属。落成,乃之五台,鸠工庀材。帝与太后,复赐内帑,建寺赐额。建华严七处九会道场,所费悉出内帑。初,五台山路崎岖,行者苦之。至是平铺石片,三百余里,溪有津梁,道有亭院,以相接待,迄今利赖。造桥于阜平县,赐名日普济。筑庵于龙关外,敕日惠济院。渴饮病医,皇慈施舍岁费帑金。御书著妙峰,额之于院。随颁《龙藏》,起阁供之,更创七如来殿。
……
前言/序言
晚清民国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比较特殊却又非常重要的发展阶段。与清王朝的极度衰落相对应,中国佛教也进入一个“最黑暗时期”。在汉传佛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宁波天童寺的“八指头陀”和南京金陵刻经处的杨仁山居士,一僧一俗,遥相呼应,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佛教复兴运动。
晚清民国的佛教复兴催生了一大批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佛教思想家。其中,既有以佛教为思想武器,唤醒民众起来推翻封建帝制的谭嗣同、章太炎,又有号召对传统佛教进行“三大革命”的太虚大师,更有许多教界、学界的知名学者,深入经藏,剖析佛理,探讨佛教的真精神,留下了数以百计的佛学著作。他们呼唤佛教应该“应时代之所需”,走上贴近社会、服务现实人生的“人间佛教”之路。这种“人间佛教”思潮,对当下的中国佛教仍然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晚清民国佛教复兴的另一个重要产物,是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留下一大批哲学、佛学名著。诸如谭嗣同的《仁学》、太虚的《即人成佛的真现实论》、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等。这批著作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既推动了当时中国佛教实现涅槃重生,实现历史性转变;也是那个时代整个社会思潮历史性转向的一个缩影,是一份极其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
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讲话中指出:“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但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演化,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留下了深刻影响。”
从宗教、文化传播、发展史的角度说,佛法东传,既为佛教的发展焕发出生机,又为中国传统文化注入了活力。13世纪后,佛教在其发源地——印度日渐消失,与此不同,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却是另外一种景象。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两千多年来,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在既相互排斥斗争,又相互吸收融合的道路上砥砺前行,逐渐发展成为一股与儒、道鼎足而三的重要的思想、学术潮流。此中,佛教在中国化过程中的契理契机,是其所以能不断发展壮大、历久弥新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佛教的中国化,尤其是中国化佛教的形成,既成就了佛教自身,也进一步丰富和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
首先,中国化的佛教本身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例如最能体现中国佛教特质的“禅宗”,它本身就是一种中国传统文化。对此,学界、教界应已有共识。
其次,佛教的中国化,一直是在与中国本土文化互动的过程中实现的。在这个过程中,佛教对于中国本土传统文化影响之广泛和深远,在许多方面也是人们所始料未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