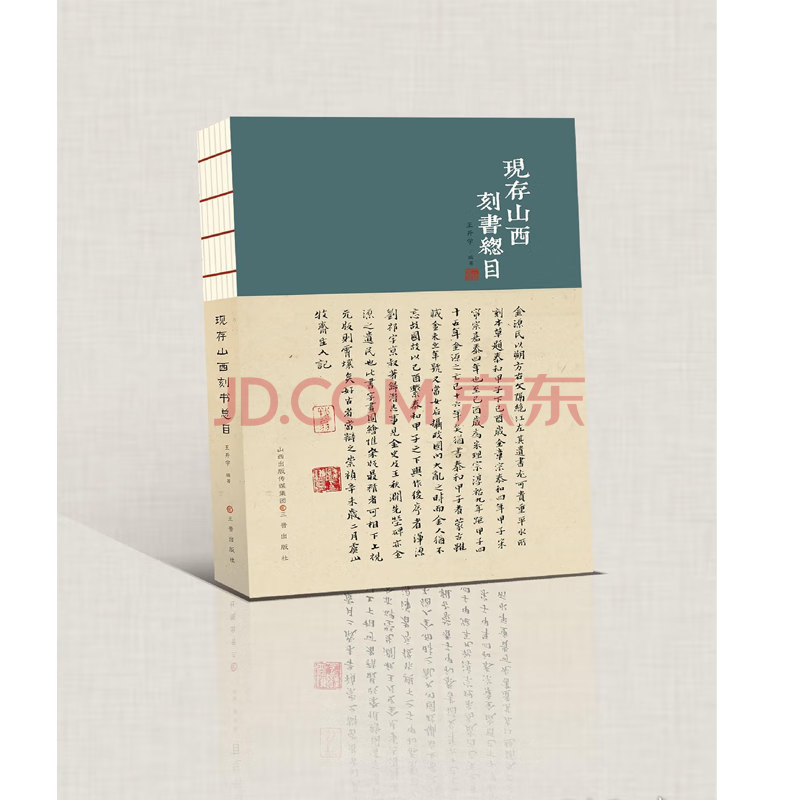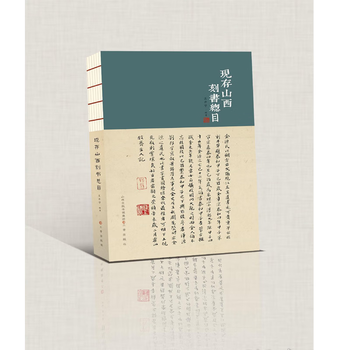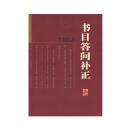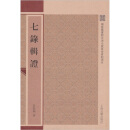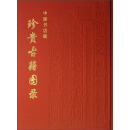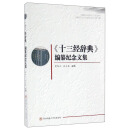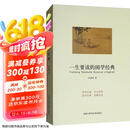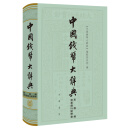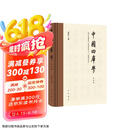内容简介
在中国刻书史上,山西一直是一个独特而重要的存在,可以说,在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山西刻书都有它值得称道的地方。项目以宋辽金元编、明代编、清代编、方志编四个板块,收录了唐末至1912年之前古代山西刻书(包括同一时期的稿抄本、活字本等)目录,“平水本”、“晋藩刻本”及各地不知名刻本均有收录,是古代山西刻书目录全本。
本书内容除书名外,还记录有存佚状况,收藏单位,极大方便了学界对于古籍图书的使用需求。本项目之所以在“山西刻书总目”之前冠以“现存”二字,其目的是专注于实际利用,故佚书一概不收,并在每一条目后标明收藏单位或个人,方便学者搜寻。
目录
宋辽金元编
明代编
清代编
省属
太原
大同
阳泉
长治
晋城
朔州
晋中
运城
忻州
临汾
吕梁
方志编
省志
太原
大同
阳泉
长治
晋城
朔州
晋中
运城
忻州
临汾
吕梁
附录一:书名索引
附录二:著者索引
附录三:收藏单位简称对照表
附录四:部分现存山西刻书书影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前言/序言
说到山西刻书,人们首先想到的几乎都是金元时期的“平水本”(或“平阳本”),最多再加上明代的晋藩刻书。这似乎已是一种普遍的认识。的确,金元时期的平水(即平阳)是同时期全国的四大刻书中心之一,在中国北方独领风骚,平水本也早已与浙刻本、闽刻本、蜀刻本一样,深入人心。但论及山西刻书,如果仅关注平水本,这显然是失之偏颇且不全面的。在中国刻书史上,山西一直是一个独特而重要的存在,可以说,在历史的任何一个时期,山西刻书都有它值得称道的地方。
如果把山西刻书史比作一条河流的话,那么它呈现的特点就是:其源也远,其势也壮,其流也长。
中国的雕版印刷肇始于唐代,现已基本成为学界的共识。唐咸通九年(868),王玠为二亲敬施雕印的《金刚经》卷子,是这一论点最得力、最切实的实物佐证。当然,其他的实物证据还有一些。如果从可信的文献记载来推断,则中国雕版印刷的产生还要比唐咸通九年再早一些,这也是确信无疑的。在这一具有标志性的人类文明成果诞生过程中,山西也不甘落后、身在其中,共同为中华印刷文明导源开路、披荆斩棘。先来看看文献方面的记载。
唐范摅《云溪友议》卷下云:“纥千尚书泉苦求龙虎之丹十五余稔。及镇江右,乃大延方术之士,乃作《刘宏传》,雕印数千本,以寄中朝及四海精心烧炼之者。”文中提到的“纥千尚书泉”即雁门(今代县)人纥干泉,他于唐宣宗大中元年至三年(847-849)任江南西道观察使。当时唐朝的帝王、大臣多迷信金丹可使人长生不老,纥干泉也痴迷于龙虎丹。《刘宏传》是道家烧炼之书,于是他就“雕印数千本”来送给京城内外的同好。作者范摅是唐咸通年间人,与纥千泉生活的时代很近,也可以说是同时代人。唐宣宗大中元年至三年比咸通九年早约二十年。
再如五代后蜀宰相蒲津(今永济市)人毋昭裔(935年任宰相),曾仿《唐石经》,主持刊刻了浩大的《蜀石经》(即“孟蜀石经”“后蜀石经”)工程。同时,又以个人名义刊刻了很多书籍,《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史记》《汉书》《后汉书》……这些大部头的文学总集、类书和正史都是毋昭裔出私财所为。他去世之后,其子孙还因其所刻之书版而加官晋爵(其子毋守素将藏书与刻板献于北宋朝廷)。他对刻书事业的倡导和身体力行,为蜀地文化繁荣做出了贡献,自然也是山西人的骄傲。
与文献记载相比,实物更具有说服力。近年来被发现并收藏于国家图书馆的《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陀天经》(北凉释沮渠京声译),经著名佛教文献学家方广錩先生鉴定,认为:“说它与《金刚经》同时代,或晚一点,完全可以成立。即使留有余地,本件的年代不会晚于五代、宋初。”在该卷的卷尾有“隰州张德雕版”牌记。经专家考证,此隰州即山西隰州,张德即是此经的实际雕版人。或许有人认为,张德只是一名刻工,并非出资人,因此不能算刻书主持者。但笔者认为,在信息不完整的情况下,张德作为该书唯一的雕版人,不管他是不是主持者,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且在雕版印刷的早期,在刻工这一专业雕版大军尚未形成或正在形成的过程中,在交通条件并不便利的古代山西,刻工的游走谋生不会离开家门太远。那由此是否可以推论,这部由隰州刻工雕版的经卷,就刻印于山西本土,甚至就刻印于张德的家乡隰州或以近地方?这也不是猜想,就在距隰州不远的绛州,另一部山西刻书可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提供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