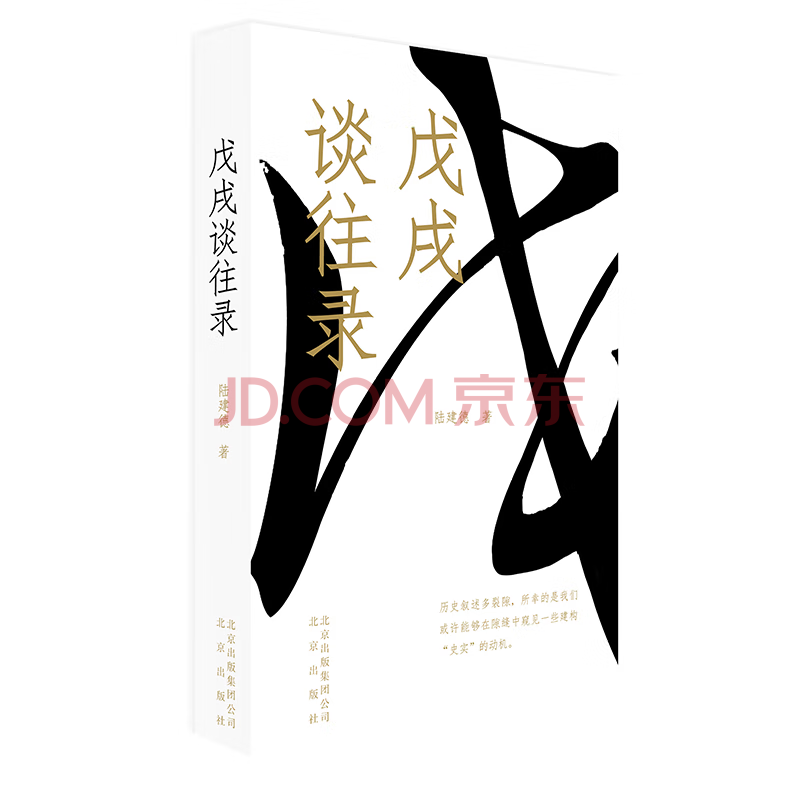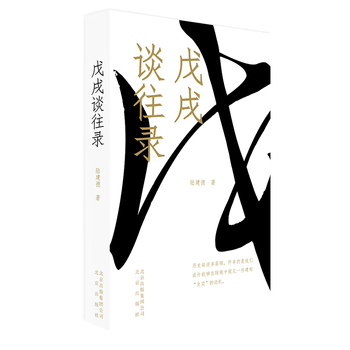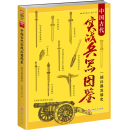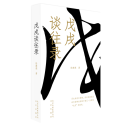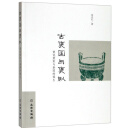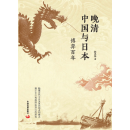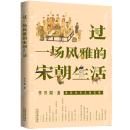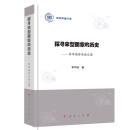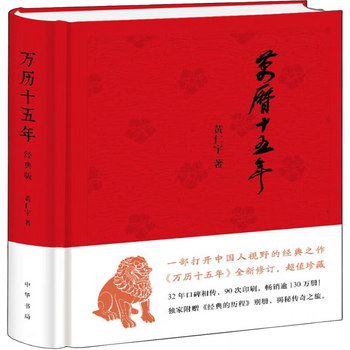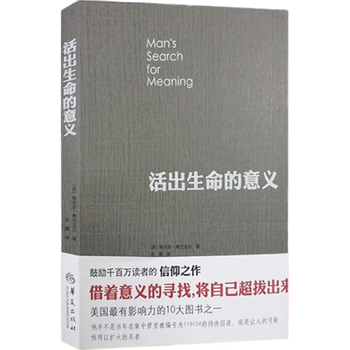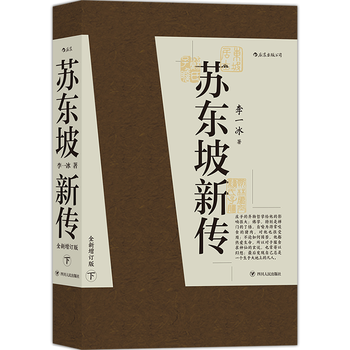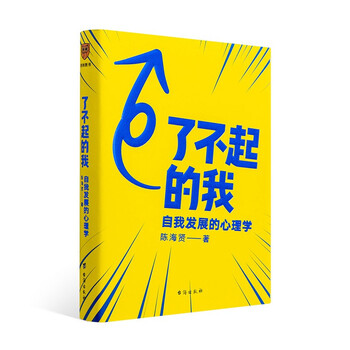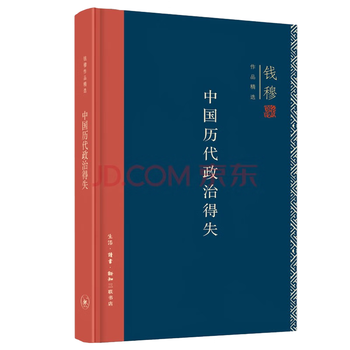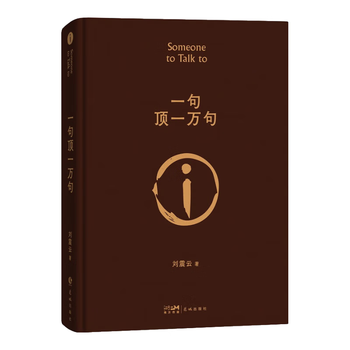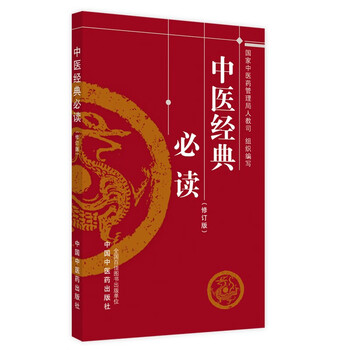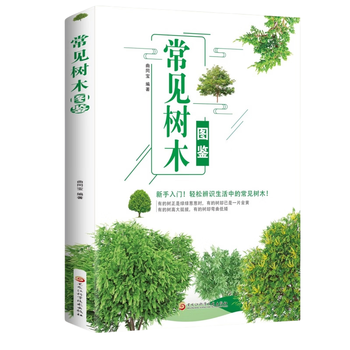内容简介
辛亥革命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四川保路运动。以往,学界对保路运动的研究过于依赖反对铁路国有的宣传材料,而忽略了成都绅商争夺地方财权的动机。本书试图揭示运动的部分真相,并指出地方分离主义势力与清廷必要的集权行为形成冲突,最终导致局面失控。自此之后,地方势力坐大;而所谓的共和,掩盖不了国家已接近分裂的事实。辛亥革命研究应该引入新的视角,尤其应该重视列强如何利用内乱加强对中国的控制。本书还对晚清社会的腐败现象有所关注。
目录
陆建德, 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1983年赴英国剑桥大学留学,1990年获剑桥博士学位。多年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2010年调该院文学研究所,任所长兼《文学评论》主编。著作包括《破碎思想体系的残编——英美文学与思想史论稿》《思想背后的利益——政治文化评论》《高悬的画布——不带理论的旅行》和《海潮大声起木铎:陆建德谈晚清人物》等。近年从事中国近代史和鲁迅研究,现为厦门大学外文学院讲席教授。
试读
一百年前,保路运动直接导致清廷崩溃,各省宣布独立,其意义之大,再怎么说也不过分。关于这次事件的资料倒是大致齐备的,只是史学界未能“物尽其用”。隗瀛涛的《四川保路运动史》作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虽在1981年出版,不免为当时的“正确”观点所主导,对五花八门的宣传材料属意过多,其实把动乱的原委以及后果说清楚就好。雪珥的《辛亥:计划外革命》(中国画报出版社,2011年)重新评价保路运动,吸纳了学界近年新观点,是本难得的好书。最大的遗憾是全书不见一条注释,连作者熟读的《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全三册)也未提及,不知是谁失职?封面上有两行醒豁的大字:“经济掀翻政治,晚清政改的不归路。”这种经济与政治的简单两分法不得要领,除了太俗,还与全书的基本论点不合,大概是编辑添附的。在作者名字下面,还有两行小字:“改革太快太猛,社会失控。改革代价承受者成了社会离心力量。”前一句不错,后一句也有点想当然,同样背离了与这本书的出彩之处——改革的得益者即地方利益集团欲望膨胀,煽动毫无判断力的民众,把惠民政策解释为卖路卖川之举,先是颠覆政府,而后抢夺筑路余款。封底的介绍文字比较可靠:晚清中央政府在铁路国有政策上出轨倾覆,乃因地方势力过大,又加上新成立的咨议局只代表既得利益集团,动辄以民意发难,中央失控,土崩瓦解。《辛亥:计划外革命》进一步证明,地方分离主义与中央集权是晚清的主要矛盾,保路运动是这一矛盾的大爆发。
茅海建先生在《戊戌变法史事考》自序中的一段话说出了当务之急:“在不可靠的史实之上,现在正运行着的大量的推导、演绎、归纳也只能是不可靠的。学术发展到今天,我们手中已经不缺乏结论,相反的是,我们的思考却为各种各样相互抵牾的结论所累。其中一个大的原因,即为各自所握的史实皆不可考。因此……最重要的工作似为史实重建。”
要了解保路运动的真相,郭沫若的《反正前后》远胜于同盟会、国民党的“辛亥老人”和“首义元勋”们的回忆,是本很好的入门指南。这本自传出版于1929年,写作时间当在作者1928年赴日以后。身处东瀛,郭沫若自然敢于表达直率独立的见解。他说,四川铁路由商办转国有,无非是贪污者不断侵蚀从民间集中起来的资金,国家不得不干预:
重要的原因在当时的人所触目到的便是办事人的中饱。一方面中饱的恶习差不多是中国社会的胃癌,而中国的资本的来源又敌不过这个无限量的中饱。所以像盛宣怀那样比较有点产业上智识的人,他自然会提出这种国有政策,而以外来的雄厚资本,来代替类是刮骨抽筋而来的一点薄弱资本了。
郭沫若倒是没有用“卖国”和“出卖路权”等近代史家常用的套话。他还指出,军容杂乱滑稽的保路同志军是“土匪领导下的一些暴民”,“他们并没有一定的计划,并没有一定的目标,只是好像山泉暴涨了之后的洪水一样,弥山遍野的横冲直撞,发挥他们的无意识的盲目的破坏。”触目的乱象说明四川多匪,更与乡风民俗以及中国社会失治相关。这些初版的文字不见于20世纪50年代的《沫若文集》中的《反正前后》,可见与时代精神不合。郭沫若肯定了暴民推翻政府的功绩,然后又说他们只是别人手里的工具:
他们不过是被有产者利用来做为争路的工具罢了。他们根本没有收拾四川的能力,也没有人期待他们来收拾四川。演傀儡戏的人,在把戏钱骗到手之后,傀儡又要被收拾进破箱子里面去。
前言/序言
收在本集的文章,写作跨度较长,有的是十多年之前的旧作,如《厨子于八、德国粮台、瓦赛公案:关于腐败的想象》发表于2006年10月8日的《南方周末》,而《致乱的金苹果——下落不明的川汉路余款》是上个月才写毕的。在《南方周末》的那篇文章里,我特意讲到中国商人或传统文化中习以为常的回扣。近来经常读到一些弘扬传统文化的美文,个别作者往往设定,中国人使用中文,天然具备其他语言使用者不具备的能力和高尚情操。我以为我们必须进入历史细节才能对自己所属文化中的行为特色有所认识,鲁迅绝不过时,不可不读。本书中三篇文章(外加两条附录)有关四川保路运动,值得再说几句。保路运动是武昌军变的先声,在较长的一段时期里,相关研究却或多或少地受制于后来形成的一套话语系统以及几个抽象概念,一些重要问题(如中央政府是否应该参与并主导铁路建设、外资是否可以利用以及商办川路公司的财务,等等)反而被边缘化了。我试图从新的角度评述这场运动的性质,抉发保路宣传背后的地方官绅利益和普通民众的损失。我在1978年秋入读复旦大学之前,做过几年街道企业的出纳,祖父又是浙江大学会计,对川路公司的账簿产生兴趣也是合乎情理的吧。
研究保路运动离不开三大册《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出版,以下简称《汇纂》),在此特向数十年如一日收集、保存这些史料的四川大学历史系戴执礼教授(1916—2013年)致敬。在海峡两岸同时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之际,四川大学历史系系主任伍宗华先生在《汇纂》的序言中给保路运动定性。他写道:“令人感触至深的,是《汇纂》辑录无可辩驳的资料,令人信服地说明,保路运动以及为之而献身的志士仁人当时所具有的先进性和革命性,揭示了这一运动在辛亥革命史,乃至中国近代史上的开创功能,并以铁血铸成的文字颂扬了千百万誓死捍卫路权的群众,在推翻满清政权的伟业中所建树的不朽功勋。可以说,该书无异是献给辛亥革命先驱们的一份极有价值的厚礼!”这篇序言的语调和措辞,可以暂时不论,它写于1991年11月,当时编者已经在数年前将史料全数捐献给来大陆开会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张玉法先生,委托该所编辑出版。当时讲求经济效益的中国大陆出版社未能认识《汇纂》的价值,实在是一大憾事。《汇纂》也收有戴执礼先生本人撰写的序言,观点与伍序完全一致。按照那时的标准表述,盛宣怀是“卖国奴”,在宜昌主持建造川汉路的重庆秀山人李稷勋则是盛宣怀的“走狗”。果真如此吗?
建造川汉路,确需非凡的勇气。当年投身这一事业的人士中,我最佩服的是盛宣怀手下的邮传部参议李稷勋。今年是戊戌年,两个甲子之前的“戊戌变法”又成为媒体的热门话题。猛进者“破天一声挥大斧”(谭嗣同诗),而李稷勋这位戊戌年的殿试传胪是踏踏实实为国效力的。与李稷勋一度共事的还有詹天佑,后者亲自踏勘设计川汉路宜昌至归州一段,并出任总工程师兼会办。詹天佑是留美幼童之一,虔诚的基督徒,他怎能料到川汉路内部的贪腐和结局?晚清新政期间废除科举,在新的学制下一些学工程的回国留学生获“工科进士”称号,詹天佑是其中之一。川籍的李稷勋和非川籍的詹天佑都是在1919年不幸去世的,那一年爆发“五四运动”。2019年,我们将以何种方式纪念上述两位杰出人士和百年前学生的爱国之举?《校长之忧——兼听“五四”杂音》一文想回到当年更复杂的现场,一个处于大国博弈和国内矛盾背景下的现场。我对德先生和赛先生深深敬佩,但是又隐隐觉得激进学生暴力行为所反映的习性未必有利于民主和科学的精神在中国的发荣。这篇文章还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那时在上海会出现不利于北京中国政府的谣言?我在去年出版的《海潮大声起木铎》一书中一再强调,近代史研究必须关注外部势力的干预。
北京外国语大学意大利语专业的文铮教授为本书须签,在此谨表谢忱。
今年春天,我有幸参加《新京报》的好书评选活动,在庆贺仪式上还为《游隼》一书的出版社、译者颁奖。为了应景,我自称喜爱观鸟,手机里存有七八种鸟类的照片。想不到这段短短的致辞见报时,七八种变成了“七八十种”,也许是我不够标准的普通话引起误会。同事朋友中不少人订阅《新京报》,他们会不会真以为我摇身变为颇有成绩的爱鸟人?其实我只是在去年秋冬之交才对住处附近的鸟类有所关注,用手机拍下蓝天里飞翔的鸽群和树上栖息的斑鸠、喜鹊、灰喜鹊、乌鸫、极北柳莺和白头翁,有一次甚至拍到一只正在啄食过冬柿子的灰喜鹊。近一两个月,我看着小小的灰喜鹊一点点长大,无所顾忌地游戏,俨然是小区的主人。它们没有婉转的歌喉,叽叽呱呱地叫着,偶尔甚至会从窗外的玉兰树枝上好奇地打量着我,也许是把我当成乏味的房客了。这些被英国诗人济慈称作“轻盈的长着羽翼的精灵”[ 济慈《夜莺颂》里的原文是“light winged Dryad of the trees”,“Dryad”系希腊神话中的树精。]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