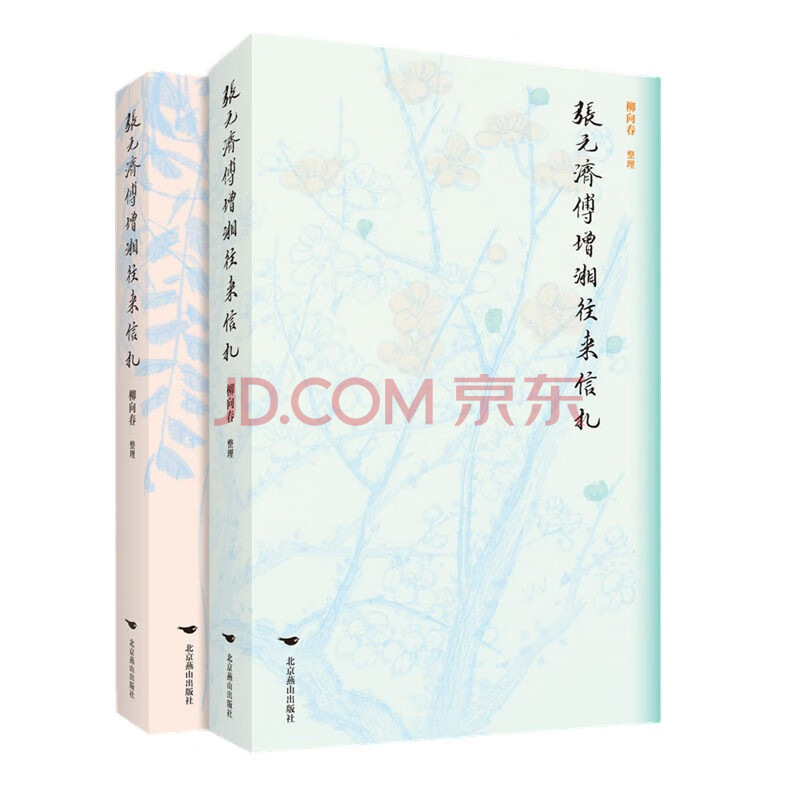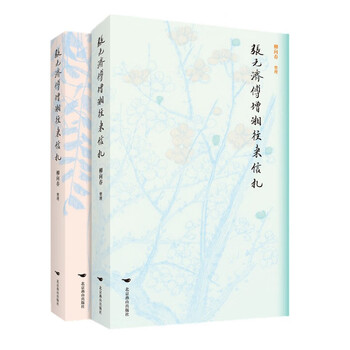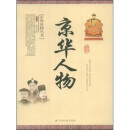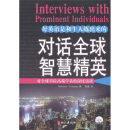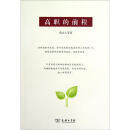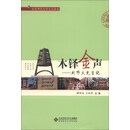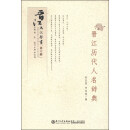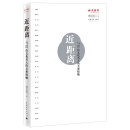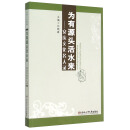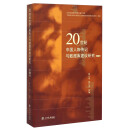内容简介
《张元济傅增湘往来信札》一书全面整理收录了现已刊布的所有张元济、傅增湘往来信札资料。全书以时间为序进行编排,张元济致傅增湘信件起于1912年,终于1947年;傅增湘致张元济信件起于1912年,终于1945年,两位先生信件各自成册,便于对照阅读。
本书对二人往来书信中的私事内容,未进行任何删减,对于研究二人的家庭、友情等方面有极大价值。信札中涉及了清末民初藏书家藏书流散资料、民国出版史资料、近代教育史料等诸多内容,不仅有助于拓展、深化张元济傅增湘相关问题研究的内涵,也可为全面、立体地彰显他们的学术贡献以及对保护、传承中华典籍的文化影响提供线索。
目录
前言
张元济致傅增湘(1912—1947)
傅增湘致张元济(1912—1945)
试读
“《南齐书》恐是元印(九行十八字),但厚白麻纸,不知元时有否?决非明印。或补板是晚宋,未可知。补板不避讳,原板大字古朴深厚,略如蜀本《史记》,请向子培一询之。”
“间有歧异,亦有宋本似误,而此本已经改正者”
“此版至元时尚存,不欲留前朝之讳,故灭其迹耶?”
前言/序言
《张元济傅增湘往来信札》前言
张元济、傅增湘都是二十世纪前半叶著名的文献大家。二人的往来书札向来号称文献渊薮,所谈多及传统文献的流布、整理、出版与研究,故在《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商务印书馆,1983,下简称商务本)问世以来,即为广大学人所珍视,以此为基础所做研究,不计其数。但正如该书整理前言所云,当时整理底本本系抄件,虽经顾廷龙先生亲自校对(据1961年4月《顾廷龙日记》,自1日起,连续三日有校傅沅叔致菊老信之记录),但仍落叶杂陈,每存讹误,如:1.张致傅函敬语、称呼署名被删除;2.擅改原文文句;3.对于傅函上所存张批,随意取舍;4.年份考订存在问题等。(具体见张人凤《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校读记》,《国学季刊》第十四期)因此之故,亟需重新整理一个更加可靠的文本,以供学界研究之需。2017年,时值张元济先生诞辰150周年之际,上海图书馆出版了《上海图书馆藏张元济往来信札》,其中张、傅二人往来书札尽在其中,共收双方信札627通,其中张致傅261通,傅致张366通,大都可以考知其所作年份,且多可对勘。这批书札始于1912年4月27日,止于1947年12月2日,时间跨度达35年。内容所及,除清末民初藏书流散,如京沪地区散出的《永乐大典》流转之外,还存有大量关于《四部丛刊》《百衲本廿四史》《道藏》等大部丛书的编印信息,尤其是对于古籍的版本鉴定及流转,多有讨论。鉴于此前整理本所存问题大都因未见原件而生,故以此原本影印本为底本重新整理,当更能符合现今深入研究之需求。更何况此次影印本中,尚存若干书札不见于前书。因此之故,此次整理,即以上海图书馆2017年影印本为底本,重新整理两位前贤往来尺牍,以为文献学进一步发展之基础。
此次整理,较前商务本而言,大致有几个进步或不同:1.补足了当时整理者所删除的信札中涉及的张元济、傅增湘二人的私事等内容。私人生活固然属于隐私,但时隔多年,其私密性已大为降低,甚至消除。还原这部分内容,对于研究二人之家庭、情感、友谊等方面至关重要。且信中出现这类文字,正可代表二人感情之深厚,交谊之纯挚。2.校正了商务本中出现的一些讹误。二人在步入晚年之后,以力弱手颤,字形颇为难辨。尤其是张元济致傅增湘函,大多皆为随手所记之信稿,不仅字迹模糊,且多修正涂画之处。原整理者精研张元济文献,辨识正确率极高,筚路蓝缕,难能可贵。然校书如扫落叶,商务本中仍存若干错讹,亟需修正。3.商务本中,除了张、傅二人往来书札外,又附录了一些相关信札,对于帮助理解二人信中所言及某事之来龙去脉甚为重要。今细绎《上海图书馆藏张元济往来信札》,进一步增补了这部分内容,以加深对于二人信中所及之理解。4.张、傅二人往来书札,大都注明了日期,但偶有未标注者,则需要就内容所述予以系年。商务本大致考证精准,但也偶有误系者,今则予以调整。5.张、傅往来尺牍,商务本整理者所见最全,《张元济全集》所收次之。时移世易,今上海图书馆所藏较诸前两书整理时已有流散,较前所遗漏者,当系捐赠上图之前,便已佚失。这部分未收于《上海图书馆藏张元济往来信札》之信札则依据前二书予以补足。与此同时,此次整理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过去遗漏、未曾整理的书信,可以补充前述二书。6.为了便于核对,将所有见收于商务本及《张元济全集》中者,均标注页码,方便读者互相比勘。7.商务本以时间顺序将二人往来函件混排,但因信件虽有先后,收信却未必仍此顺序,故去函覆信多有错落参差者,常令读者产生困惑。今改作二人各自分排,这样一来,就可严格按照时序进行排列,庶几眉目可以分明。
光绪十四年(1888)戊子,傅增湘中式顺天乡试,成举人。次年(1889)己丑恩科,张元济亦于杭州乡试中式第十名。二人往来函札中,均以“同年”互称,盖以正科、恩科可互称同年之故。光绪十八年(1892)壬辰,张元济以二甲二十四名入翰林院,为庶吉士。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傅增湘以二甲第六名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有“戊戌翰林”印。以翰林论,二人前后相差四科。惯例,清朝翰林对比自己早五科入翰林院者,尊称为老前辈。但也有为表示特别尊重,虽未达五科,也称老前辈者,如曾国藩之于胡林翼、张百熙之于瞿鸿機等,皆晚一科而呼对方为老前辈。傅增湘称张元济为老前辈,亦可类比。另外,据王世贞《觚不觚录》所载,明时翰林旧规,入馆后七科者称晚生,后三科者称侍生。这一习惯一直沿用至清,故傅增湘在信中多有落款为侍生者。张、傅二人现存通信虽始于1912年,但两人相识相知当远早于此,盖二人早年均曾从事教育,又皆喜好文献,交集必多。再据今存张元济致傅增湘第一函云:“昨午肃上弟八号信。上灯后得四月十九日第七号书”,可知在此之前,双方至少已互通书札七八次。再,1942年5月15日张元济致函傅增湘,并请代售弘治本《梅宛陵集》。从情理上言,无论是否能够找到愿购之人,傅增湘当有覆函报告。又现存最晚之函为1947年12月2日张元济致傅增湘者,信末,张元济特意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