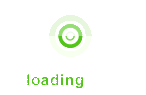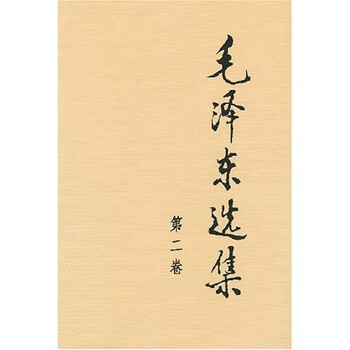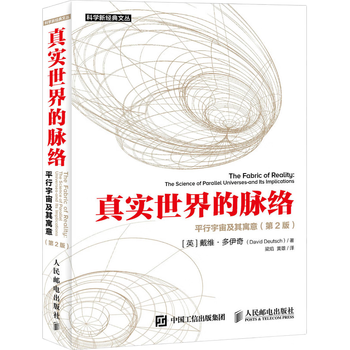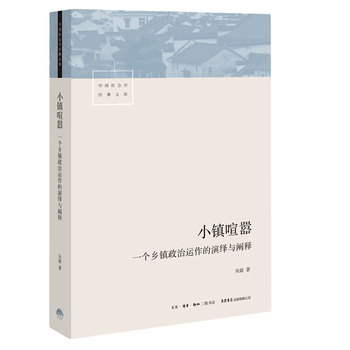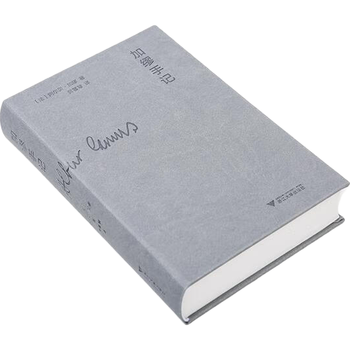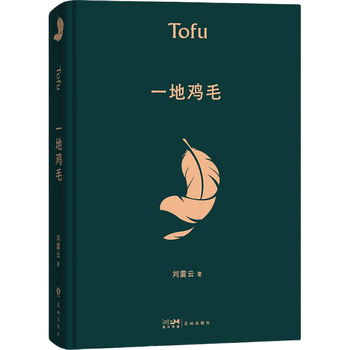内容简介
本书是国际知名建筑设计大师本杰明·伍德先生的亲笔自传,记录了作者从美国南方腹地来到中国长江三角洲的漫长旅程,回忆了他传奇的人生经历和难以复制的精彩轶事。本书分为31章,并非严格按照时间顺序排列,而是让话题和故事相互交织,每个章节相对独立。尽管本杰明·伍德先生以建筑设计领域的造诣闻名遐迩,但鲜为人知的是,他数十年跨越时空经历的一系列传奇故事,是他在专业领域之外同样难以复刻的宝藏和珍品。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本书不是一本关于建筑的书,而是一本回忆录。”本杰明先生有着高超的语言表达技巧,阅读此书,令人仿佛与之面对面,听他以诙谐乐观、智慧练达的口吻,将诸多鲜活的故事娓娓道来。作为一本传记,该书既有智慧和思想的凝结,又兼具生动的文笔,可读性强。
试读
第一章 在黄色巴士上等待
我老家的房子是一座由父亲翻修过的美国大萧条时期的农舍。母亲总在白色搪瓷炉灶上用铸铁深煎锅煎鸡肉和秋葵,这是父亲最喜欢的搭配。除了意大利面和肉丸,母亲不会做什么异国情调的菜。她的橱柜里没有任何进口产品,奶酪是经过加工的卡夫切达干酪或正宗的威斯康星干酪。也没有初榨橄榄油,她通常用动物脂肪油给煎锅上油。我也从来没有在家里的“西屋”冰箱里见过一块真正的黄油。但我们有真正的奶油,它就浮在那些未经巴氏消毒的当地酪乳上面。我们会把亮黄色的人造黄油涂在白吐司或自制酪乳饼干上。小时候,我和弟弟常常花好几个小时在沙坑里玩耍。母亲从厨房水槽上方的窗户看到我们,总会笑容满面地出来跟我们说,如果我们挖的洞够深,最后可以挖到中国去。她说对了。
我们的农舍建在一个平缓的山坡顶上,天气晴朗的时候,可以望见南面19英里处的亚特兰大市中心。内战前种植园文化和战后独立耕作社会留下的东西,散布在我们26 英亩宅地周围的数千英亩土地上。再生树种、休耕土地、耕地、荆棘丛、沟渠、腐烂的锯末和松树皮堆,以及丢弃的垃圾包围着我们。这一切都在等着一个瘦削的、皮肤黝黑的、金发碧眼的赤脚男孩和他的姐姐、弟弟前去探索。一片似乎无边无际的田野、森林,为我们的户外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我们从那些废弃坍塌、周围荆棘丛生的旧谷仓中弄出木板来搭建树屋,赤身骑着无鞍的昔德兰小马去老旧的蓄水池玩耍。我们在红色沙土上发现了切罗基族石英石箭头,精致小巧、棱角分明,上面还留有被暴雨冲刷的痕迹。我们踩着光滑的石头,打着滑,一路沿着溪流而上,寻找泉水的源头。我们小心地绕过被有毒藤蔓和荆棘掩盖的废弃手挖水井。我最好的小伙伴,一只猎犬,就在一个这样的陷阱中不幸丧生了。在被烧毁的柏油纸板小屋废墟旁,我们掀翻了那里的露天厕所。我们惊叹于种植园那座废弃的两层楼,虽然它没有地板也没有屋顶,但用了古希腊式的多立克柱,依旧气派非凡。小说《飘》里描述的时代已经过去,但依旧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在美国深南部,可怕的三K 党取代了四处劫掠的北军,成为最令人害怕的组织。
五岁时的某一天,我和母亲在一条碎石路旁等待黄色校车接我去罗斯维尔小学,那是我上小学的第一天。记得当时母亲弯下腰对我说,并不是所有和我玩耍的小朋友都会坐上这辆校车,有些已经被另一辆校车接走了。因为黑人小学在另一个县,非常远,只有白人孩子才能上罗斯维尔小学。母亲对我说:“有一天你会懂的。”
在进入种族隔离的公立小学之前,我和姐姐、弟弟上的都是私立幼儿园。与公立学校的制度一样,我们上的私立幼儿园也只接收白人孩子。这倒并不是院方想要实行种族隔离,而是因为害怕受到来自种族隔离支持者的暴力威胁。这个幼儿园有两个老板,一位是我母亲,另一位跟我们家关系很好,叫凯瑟琳·辛格尔特里。这两位女性都意志坚定,受过良好教育,而且非常注重儿童的早期发展。
最初,这所幼儿园开在希思·罗宋家里,她和我家是朋友。希思和她的丈夫有一处叫大橡树的庄园,位于历史悠久的罗斯维尔玉兰街,是一座建于19 世纪晚期的气派的红砖豪宅,周围视野非常开阔。幼儿园租用了这座宅子里装饰有橡木壁板的图书室。作为罗斯维尔最富有的家庭,他们还拥有镇上第一台电视机:一台六英寸的黑白电视机。这台RCA电视机有两个旋钮——开关和音量。电视机装在一个定制的柜子里,柜子里隐藏着各种不同形状的真空管和高压变压器。电视信号是通过屋顶那巨大的、用拉线固定的天线来接收的。
电视柜位于图书室光线最暗的角落。希思的丈夫每晚都会坐在一张大大的黑色真皮扶手椅上,要么看电视,要么看书。他还用烟斗抽烟。我记得他总是给幼儿园送一些盒装的金属线烟斗清洁器,我们会用来制作小人和其他小玩意儿。有时候我们会把这些作品跟一些五颜六色的彩纸一起留在他书桌上。
前言/序言
前言
我姓伍德,也就是“木头”,而我的父亲有个昵称叫“木片儿”。很多方面我都像从那老木头上掉下来的木屑,跟父亲一个样。我常花很多时间透过树顶仰望天空、畅想未来。而我的生活经历也充分证明:一颗灵感的树种,终将孕育出一片充满思想的森林。
这本书记录了一趟漫长的旅程,记录了我如何从美国深南部辗转来到中国长江三角洲这个伟大的世界舞台。书里写的都是真人真事,更是我的真情实感。作为一个美国人,我参与了上海这座非凡的国际化大都市的建设,帮助它展现了新风貌。1998年,我认识了一位香港人,他极富远见卓识,邀请我这个前超声速“鬼怪”战斗机飞行员加入他的“战队”,共同创造了历史,打造了中国首个世界级城市娱乐文化地标——上海新天地。在之后的20多年里,我又在中国做了许多其他建筑项目,改变了数以亿计的普通中产阶级的生活。
我原想请一位作家代我写这本书,但后来我想起了莱昂纳德·科恩唱的一句歌词:“像一个午夜合唱团的醉汉,尝试以我自己的方式获得自由。”那么,无论是好是坏,还是由我自己来完成这首独唱。这本书不是按照时间顺序写的,而是纵横交错,会在适当的时候时空穿插。我不喜欢被死板的架构约束,而更愿意让故事和话题之间有相互碰撞和交织。为了读者不被绕晕,我先简要梳理一下我不平凡的人生经历。
1947年,我出生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北部一个叫罗斯维尔的小镇,家里有三个孩子,我是长子,但排行老二,上面还有个姐姐。小时候,我们上的是种族隔离的公立学校。1961 年,那年我14岁,因为我父亲罗伊·伍德被肯尼迪总统任命为内政部部长特别顾问,我们全家搬到了弗吉尼亚州的亚历山德里亚市。1968年,我就读于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土木工程专业,次年进入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法学院。第二学期上到一半,离美军抽签征兵还有六个月的时候,学校批准了我的休学申请。于是我与我两位高中好友去了科罗拉多州杜兰戈,度过了一个漫长的夏天。我们借了些钱,买下并翻新了一栋废弃的维多利亚式房屋,使其成为我们临时的家。到了9月,我不得不做了一个决定:与其被陆军征召去越南,不如自愿加入美国空军。1971年,我从美国空军军官学校毕业,成为当时驾驶RF-4“鬼怪”战斗机最年轻的飞行员之一。在前往驻德国的美国空军基地之前,我和我的高中恋人莎拉结婚了。
越战结束后,我自愿参加了针对美国飞行员的“提前退役”计划,于1976年正式退役。但我们在欧洲又多待了九个月,并在希特勒“鹰巢”为年轻飞行员建了所户外探险学校。回美国之后,我们搬回杜兰戈的房子里,又在附近曾经的淘金小镇西尔弗顿买下并翻修了一座历史悠久的维多利亚式建筑。它曾是一家法式面包店,我们把它改造成餐厅和登山用品店。1978年,我回东部探亲,途中去了贝聿铭设计的华盛顿国家美术馆东馆,深受触动,从而决心成为一名建筑师。
1980年,在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后不久,我们卖掉了锡尔弗顿的房子,搬到了马萨诸塞州的剑桥,这样我就可以去麻省理工学院的建筑学院攻读研究生。1984年毕业后,本杰明·汤普森成为我的第一个老板,也是唯一一个。本于1994年退休,之后我与他妻子简合伙成立了一家新公司,又在1998年结束合伙关系,并与卡洛斯·萨帕塔成立了新公司。那一年,我们拿下了两个重要项目:翻新芝加哥熊队主场——新士兵球场以及规划上海新天地文化娱乐街区。次年,新天地项目正式动工,我也正式搬到了上海。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在上海工作和生活,这是一段多么精彩的人生旅程啊!
这里我有必要提醒读者,尤其是除家人和朋友之外的读者: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恶棍”,一个不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老怪物,犯下了所有的罪行。本书里有一些对政治家、其他建筑师,以及对各种各样鼓吹泯灭人性、制造疯狂活动的带头人不太礼貌的粗俗指责。必要的地方,我会使用直白、粗俗的语言。我童年时期的朋友们会用“N 字”“脚指头”来描述巴西果仁。而当时的煎饼粉盒子上还会印着一个身材丰满、穿着围裙的杰迈玛阿姨,头上还系着蓝色头巾。
我承认写这本回忆录的时候堆砌了太多的辞藻。我写作的方式就像我做设计一样:跌跌撞撞地穿过记忆的原木,又撞上人生体验之树,在灵感的森林中摸索前行。为了既不偏题也不枯燥,我引用了包括文学、电影、美术、音乐和管理在内的各种素材。这不是一本关于建筑的书,而是一本回忆录。命运的机缘巧合将我带到了上海,一待就是24年。或许某一天,我也会因为那些缘分而离开,去往另一个地方。
我去过古巴,走遍了哈瓦那老城每一家自称为海明威最爱的酒吧。这些酒吧有个共同点,就是里面总是充满了有精彩故事的人,会跟你分享他们喜爱的各种人和地方。我也有许多人生故事,本书只包含了其中的一部分。如果你有兴趣,那么欢迎来到我在上海的马提尼小酒吧,我会和你分享更多的故事。不过前提是你也要分享一些自己的故事。没有你们,我就不会有新的灵感。所以,孩子们,享受当下,让美好的时光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