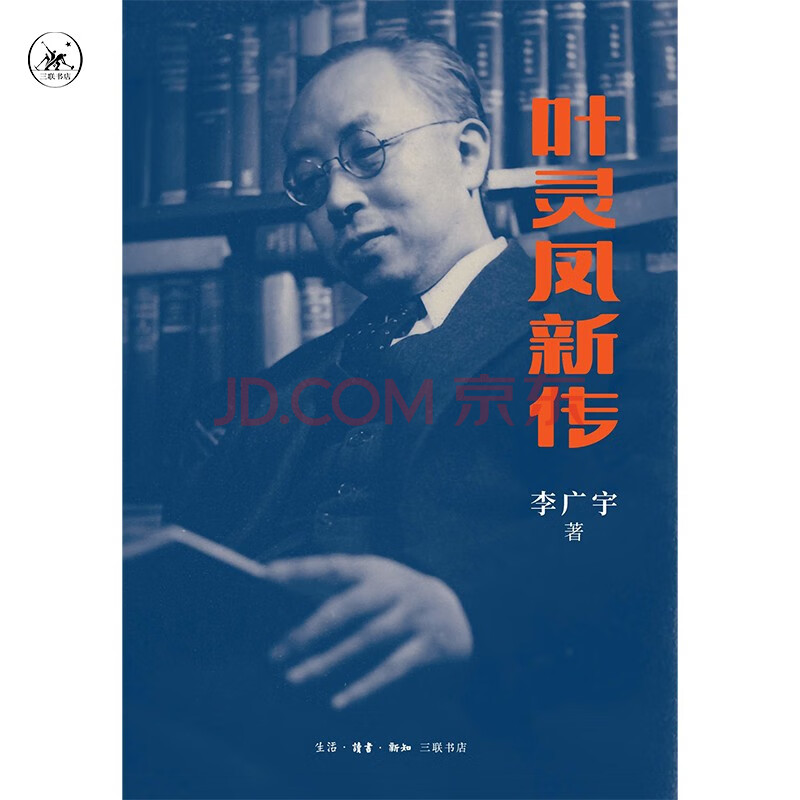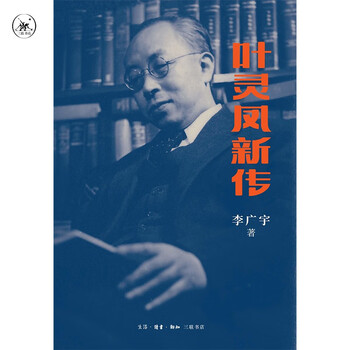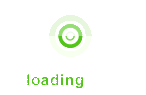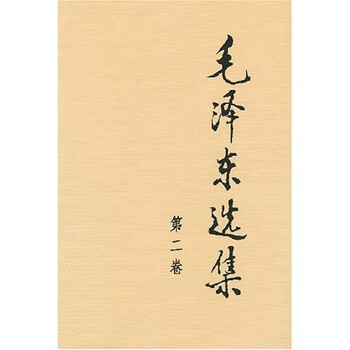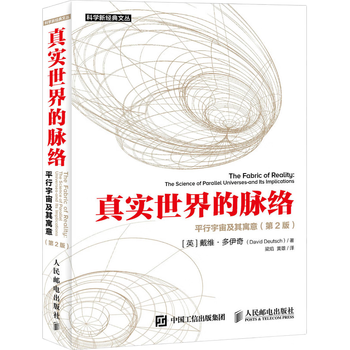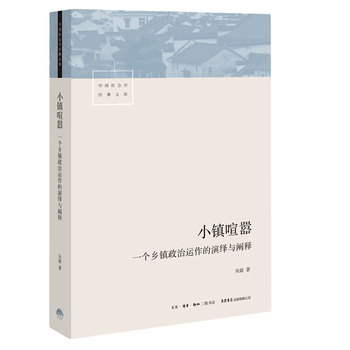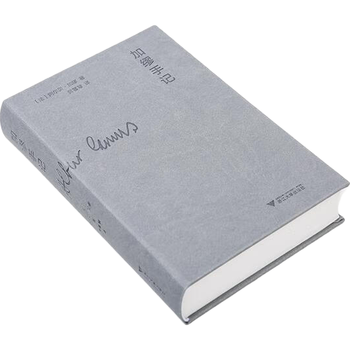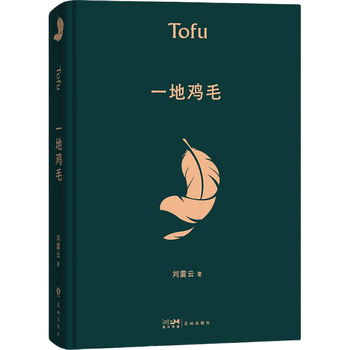精彩书评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与沪港两地关系最久最紧密的作家,当为叶灵凤莫属。这部《叶灵凤新传》是作者多年查考的结晶,生动描述了叶灵凤跌宕起伏的一生、多方面的文学成就,尤其是叶灵凤与香港文坛的密切关系,披露了不少新的史料,令人耳目一新。
——陈子善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十多年前,看到李广宇著《叶灵凤传》,心想作者何许人也? 材料何来?今天,广宇已成了我们叶家的好朋友和一份子,我们兄弟姐妹和侄子都说:“李官比我们还了解爸爸和爷爷。”他的《叶灵凤新传》,不是写事,是写情。他说过,爱书的人都该爱叶灵凤,希望爱书爱叶灵凤的人都爱广宇这本《叶灵凤新传》。
——叶中敏
(叶灵凤女儿,《大公报》前副总编辑、主笔)
目录
上篇
释名 _ 003
家乡南京 _ 007
童年和少年 _ 013
美专学生 _ 019
创造社的几位前辈 _ 025
追随在先生左右 _ 032
《洪水》时期 _ 041
出版部小伙计 _ 049
入狱与整顿出版部 _ 058
“最风行的是《幻洲》” _ 072
听车楼主 _ 080
双凤奇缘 _ 087
林风· 林凤· 灵凤 _ 101
《现代小说》与《现代文艺》 _ 111
左联的加入与开除 _ 121
《现代》同人 _ 126
比亚兹莱与叶、鲁恩怨 _ 139
“我也在‘热中木刻’” _ 169
中国的斋藤昌三 _ 197
在张光宇身边 _ 207
灵凤抚云舞 _ 221
新感觉派的一群 _ 230
文艺而称画报 _ 237
《六艺》:最后的安魂曲 _ 247
中篇
在救亡的洪流中 _ 261
岛上烽火 _ 278
叶灵凤是汉奸? _ 289
沦陷时期的写作 _ 303
“书淫”并非“淫书”之谓 _ 316
陈君葆日记中的叶灵凤 _ 325
沦陷时期的书事 _ 340
战后的“再就业” _ 349
下篇
“我同永玉很要好” _ 365
“我和鲁迅的那桩‘公案’” _ 371
《香港方物志》 _ 384
张保仔不只是个传说 _ 394
为什么要讲《香江旧事》? _ 400
书话大家 _ 412
书写中国,寻古中华 _ 419
“故事大王”生涯 _ 427
办刊高手壮志未酬 _ 433
“米当夜会”在香江 _ 439
西洋美术之旅 _ 452
叶灵凤在一九七三 _ 461
叶灵凤的身后 _ 467
参考书目 _ 475
叶灵凤年谱简编 _ 483
后记 _ 487
试读
创造社的几位前辈
人生之事有时非常吊诡,一个偶然的安排,很可能就改变了一生的走向。设想,假如叶灵凤当年不是住在民厚南里的叔叔家,便不可能遇上恰在那里安营扎寨的创造社诸君子。这样一来,他很可能会继续沿着自己既定的当一名画家的路子发展,但那画家,绝不可能是“中国的比亚兹莱”这样一种形象;也有可能不会发生与鲁迅的交恶,兴许还会成为鲁迅的一个得意门生,捏刀向木, 镌刻时代与人生。他也不会碰上创造社小伙计潘汉年,甚而不会加盟《救亡日报》、南迁广州、滞留香港……但人生没有假设,命运已经安排这位尚稚嫩懵懂的美专学生,对未来毫无预料地走进了民厚南里。
成仿吾是他见到的第一个创造社前辈。在《仿吾先生》一文中,他说:
在创造社的几位前辈之中,我见面最迟的是张资平先生,最早的就是仿吾先生。那还是一九二四年前后的事情,我在上海美术专门学校学画,住在哈同路民厚南里的叔父家里。那时除了学画以外,自己已经在学习写作,而且正像当时无数爱好文艺的青年一样,是《创造周报》的爱读者。当我知道《创造周报》的编辑部也设在民厚南里以后,有一天,我便将刚写好的几篇散文,附了一封写给仿吾先生的信,亲自送了去。当时仿吾先生一连发表了许多篇文艺批评文字,在我们文艺青年的眼中,他正是一位泰山北斗一样的人物,我当时不过二十岁,自然没有勇气,也没有这奢望,敢去拜见当时叱咤文坛的这位人物,因此只将那封信放在他们后门的信箱里,就急急的走了。哪知过了两三天,忽然有人叩门送来一张字条,上面大意说来信和稿件都收到了,请你有空到我们这里来谈谈,下面署名赫然就是“仿吾”。
……不用说,我当时收到了那张字条,就怀着一颗突突跳着的年轻的心,急急的去拜访他。当我踏上《创造周报》编辑部那一座微暗的木楼梯时,我的心里的兴奋是无可形容的,因为我知道这时不仅已经踏上了“文坛”,而且已经踏进创造社的门了。
叶灵凤似乎并未从成仿吾的作品中获得什么影响,但后者将叶灵凤迎进门来的意义非常重大。叶灵凤说:“这张字条给我的印象真是太深,三十多年来,我只要一闭起眼睛,它就清晰的出现在我的眼中。许多年以来,我一直将它什袭而藏,有时自己拿出来看看,后来偶尔也拿出来给其他爱好文艺的青年朋友们看,使大家知道前一辈的文艺工作者是怎样的热心提携奖掖后进,而一封信一句话往往怎样会决定了一个人一生要走的道路。”
成仿吾年纪比叶灵凤他们大了许多,这位“木讷寡言”的前辈,没少带叶灵凤他们一班少年,领略“吃小馆子的乐趣”。“在从前上海的石路上,在三马路与四马路之间的一个弄堂里面,有一家非常简陋的小馆子,称为复盛居。这是一家小小的天津馆子,卖的只是一般的北方面食和几种简单的炒菜。”叶灵凤说:“复盛居的价钱,虽然那么便宜,但是当时还在学生时代的我,自己仍不是随便可以吃得起的,因此多数总是跟了别人一起去的。这里面,东道做得最多的是仿吾先生。”在《吃小馆子的乐趣》中,叶灵凤这样描述当时的场面:
仿吾先生是喜欢喝一两杯的。复盛居供应的酒,自然是白干,因此壶和杯都很小。我是自少就不会喝酒的,可是全平却有很好的酒量。因此,能够陪仿吾先生喝一杯的,只有他了。敬隐渔和倪贻德虽然比我能喝,但他们有时过于相信酒能够浇愁那一类的话,于是半杯下肚,就已经醉态可掬,对于人生、爱情和社会,发出许多感慨了。
这时只有仿吾先生仍是像平时一样,不大开口,默默的喝着小杯里的白干,偶然说一句什么,那湖南乡音也仿佛更重了。
成仿吾虽然酒桌上不大开口,写起文章来却极其猛辣,人称“黑旋风”。一九二八年五月一日,他以“石厚生”为笔名,发表《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以一连三个“闲暇”向鲁迅发起挑战。成仿吾敢于挑战鲁迅的精神,是否对叶灵凤有些潜移默化的影响,很值得注意。因为叶灵凤向鲁迅放出“酒缸”和“露台”两支冷箭时,“我们的批评家成仿吾先生正在创造社门口的‘灵魂的冒险’的旗子底下抡板斧。他以‘庸俗’的罪名,几乎砍杀了《呐喊》”(鲁迅:《故事新编· 序言》)。无论如何,在挑战鲁迅这一点上,有人会同时提到他们两人。
至于郑伯奇,他也是经成仿吾介绍认识了郭沫若,进而加入创造社的。叶灵凤第一次有机会见到他,已经是创造社出版部成立以后的事。结识虽晚,但他对叶灵凤的影响却是决定性的,尽管对他来说纯属“无心插柳”之举。叶灵凤是这样回忆的:
好像是一个夏天,他从东京回到了上海,高高的身材,戴着金丝眼镜,似乎对我当时所画的比亚兹莱风的装饰画很感到了兴趣。我清晰的记得,他带我走去逛内山书店,知道我是学画的,而且喜欢装饰画,便用身边剩余的日本钱在内山书店买了两册日本画家蕗谷虹儿的画集送给我。这全是童话插画似的装饰画,使我当时见了如获至宝,朝夕把玩,模仿他的风格也画了几幅装饰画。后来被鲁迅先生大为讥笑,说我“生吞比亚兹莱,活剥蕗谷虹儿”,他自己特地选印了一册蕗谷虹儿的画选,作为艺苑朝花之一,大约是想向读者说明并不曾冤枉我的。
当时内山书店所售的蕗谷虹儿画集并没有几套,所以,是郑伯奇给了叶灵凤机会,让他和鲁迅同时拥有了一套,进而也使“生吞比亚兹莱,活剥蕗谷虹儿”这一名联得以完璧。从另一个意义上说,中国读者能有机会读到中文版的《蕗谷虹儿画选》,也要感谢叶灵凤,因为据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中所云,当初他和柔石等组织朝花社,“目的是在介绍东欧和北欧的文学,输入外国的版画,
因为我们都以为应该来扶植一点刚健质朴的文艺。接着就印《朝花旬刊》,印《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印《艺苑朝华》,算是都在循着这条线,只有其中的一本《蕗谷虹儿画选》,是为了扫荡上海滩上的‘艺术家’,即戳穿叶灵凤这纸老虎而印的。”
一九三五年,郑伯奇为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选入了叶灵凤的小说《女娲氏之遗孽》,在导言中,郑伯奇这样评价叶灵凤的小说:
一样是欢喜写性的变态心理,叶灵凤便和白采大不相同。白采所刻画的是主人公的性格,那种变态性格的描写是有迫人的力量;叶灵凤所注意的是故事的经过,那些特殊事实的叙述颇有诱惑的效果。所以白采的作品比灵凤的深刻,而灵凤的小说比白采来得有趣。《女娲氏之遗孽》是写一个既婚的中年妇人对于青年男子的爱欲生活。他把妇人诱惑男子的步骤和周围对于他们的侧目都一步一步地精细地描写出来。这和白采的《微青》相比,就可以看出两人创作态度不同。灵凤写小说是在《洪水》发刊以后,这《女娲氏之遗孽》更后,大约是在《幻洲》上发表的。
说过了郑伯奇带叶灵凤认识蕗谷虹儿,再回到比亚兹莱。这就要归功于创造社的另一位元老——田汉。叶灵凤在《比亚斯莱的画》一文中说:
中国最早介绍比亚斯莱作品的人,该是田汉先生。他编辑《南国周刊》时,版头和里面的插画,用的都是比亚斯莱的作品,而且他所采用的译名很富于诗意,译成“琵亚词侣”。后来他又翻译了王尔德的《莎乐美》,里面采用了比亚斯莱那一辑著名的插画,连封面画和目录的饰画都是根据原书的。
叶灵凤与田汉接触较多,他把田汉称作“老大”。他说:“大约在一九三二年前后,有一时期,我在上海差不多每天同田汉先生在一起。老大的身边照例总是有一大堆朋友跟着的,因为他实在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老大为了写剧本,在法租界边上那些较清静的旅馆里开了一个房间,大家闻风而至,聚在一起高谈阔论,或是浩浩荡荡的到大世界附近的小馆子里去吃晚饭。”那个时候,叶灵凤供职于现代书局,田汉主编的《南国》杂志和多卷本的《田汉的戏曲集》,都是由他付排。他在《作家们的原稿和字迹》一文中说:“经他校对过的校样,就像是巴尔扎克传记上所说的巴尔扎克校稿那样,那简直不是校对,而是修改原稿,有时甚至是改作或重写。”“田汉戏剧集里那些长长的序文和后记,都是这样产生出来的,而且都是当时在反动势力压迫下躲在旅馆里漏夜干出来的。你去读一下,你就知道他有些地方写得多么悲愤抑郁,有些地方又多么慷慨淋漓。”
为叶灵凤引介比亚兹莱的功臣,还有郁达夫。叶灵凤在《比亚斯莱的画》中接着写道:
同时,郁达夫先生也在《创造周报》上写了《黄面志及其作家》,介绍了比亚斯莱的画和道生等人的诗文,于是比亚斯莱的名字和作品,在当时中国文坛上就渐渐的为人所熟知和爱好,而我这个“中国比亚斯莱”,也就在这时应运而生了。我当时给《洪水半月刊》和《创造月刊》所画的封面和版头装饰画,便全部是比亚斯莱风格的。
郁达夫给叶灵凤打开的窗子,不只有比亚兹莱,更扩展到了“先后以《黄面志》为发表作品中心的那一批画家、诗人和散文家”,“除了比亚斯莱之外,画家方面还有惠斯勒、麦克斯· 比尔波姆,诗人有道生、史文朋、西蒙斯,散文小说家有王尔德、乔治· 摩亚等等”,叶灵凤对这个年代保持了极大兴趣和持续关注,他认为:“十九世纪的‘世纪末’,在英国文学史上虽不是一个怎样伟大的时代,但是却是一个才华横溢,百家争鸣,充满了艺术生气的特殊时代。一面是旧时代的结束,同时也是新时代的开始。”
郁达夫对于叶灵凤,是介乎师友之间的。在创作方面,叶灵凤从前辈作家中获得教益最多的,恐怕就是郁达夫了。他把平生所作第一本小品集《白叶杂记》称作“郁达夫式的笔调”。早期的性爱小说,有不少篇,从内容到细节,更可寻到郁达夫的影响。但他们也有弄翻的时候,一度有几年不曾来往,这些留待后面再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