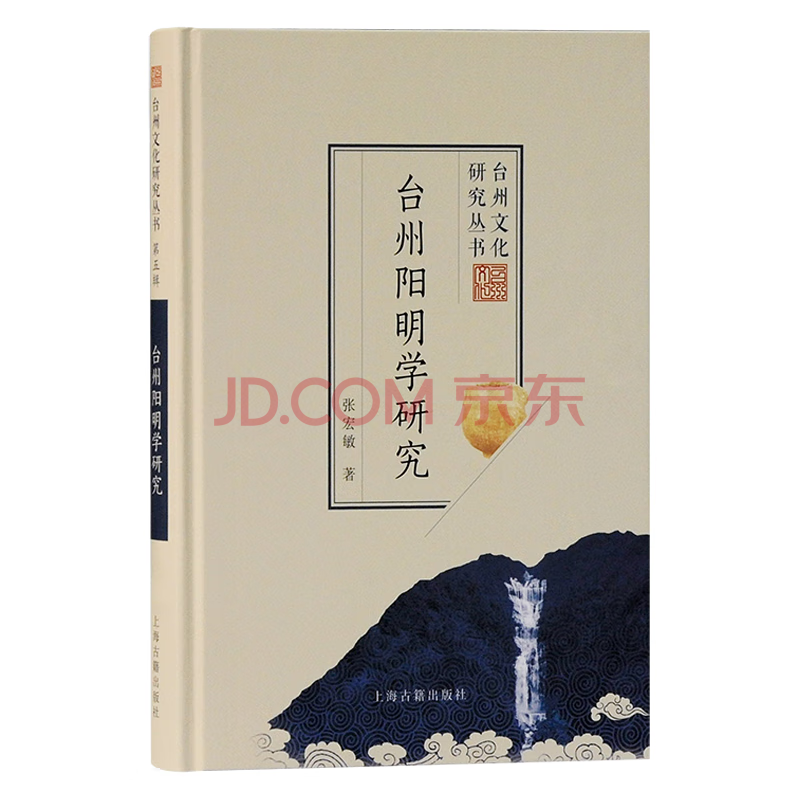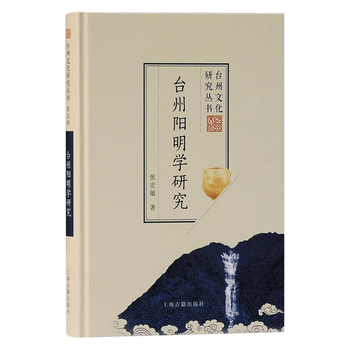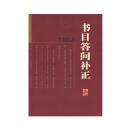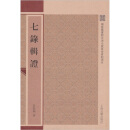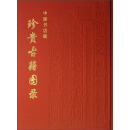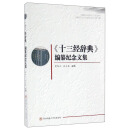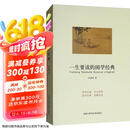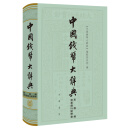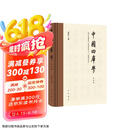内容简介
本书主要围绕台州阳明学者的交游与文献而展开。“交游”是指王阳明与台州籍阳明弟子(黄绾、应良、林元叙、林元伦、赵渊等)之间结识交往,王阳明针对台州籍诸弟子(如黄绾、应良、金克厚等)各人不同的学术根基与禀赋志趣而进行的传道、授业、解惑的具体过程,也包括以黄绾为中心的台州籍阳明门人群体之间的相互交往与学术切磋。“文献”是对台州籍阳明弟子门人的文献史料的盘点与梳理,主要包括黄绾、叶良佩、王宗沐的著作文献的编撰缘由、传世版本、文献价值等,还包括围绕江右王门学者邹守益佚文《应方伯良墓志》而对应良的生命历程与学术交游的梳理,浙中王门学者王畿佚文《明故南京通政司经历石洞黄公墓志铭》而对黄承文的生平学行的论述。该书对台州阳明学思想内涵、特质进行了深度的学术发掘与学理阐释,使得台州阳明学的学术内涵与独特价值比较丰满地显现出来;对明代中后期台州学者各种著作之创作背景、思想主旨、版本存世、学术价值等情况的系统梳理,尤其具有参考价值。
目录
序
阳明学的兴起无疑是自晚明以来中国思想界的一个重要事件,并深刻影响着中国(乃至于东亚)的思想史进程。台州天台山与甬上四明山在历史上有着深刻的联系,在文化上也有着亲缘性,但是,在长期以来,尤其是关于阳明学的研究中,天台山是被忽视的。台州,应该来说,是阳明学发展的一个特殊区域。但是,可能是与天台山文化作为佛道标志性文化的基本定位有关,对于天台山(台州)儒学的忽视,可能也是情理之中的。然而,情理之中并不代表历史事实即是如此。比如在《明儒学案》《台学统》《续台学统源流》等等作品中,我们都可以发现一大批台州儒家学者的身影。台州儒学的研究,从总体上来说,是一个长期被忽视或者说被掩盖的事实。从这个角度来说,无论是对于朱子学,还是阳明学,在台州的发展都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张兄宏敏博士的新著《台州阳明学研究》,从这个角度来说,是一部具有开拓性意义的力作,该书以“交游”和“文献”为关键词,对台州籍阳明弟子以及阳明学者群体进行了深入的考辩,由此呈现出了台州阳明学的一个基本发展脉络。将“台州阳明学”作为一个学术命题重新确立起来,这是该书最大的一个贡献。而全书的脉络则是围绕“交游”与“文献”来展开的。按照作者的区分,“交游”指得是王阳明与台州籍阳明弟子(如黄绾、应良、林元叙、林元伦、赵渊等)之间交往结识,王阳明针对台州籍诸弟子各人不同的学术根基与禀赋志趣而进行传“道”(圣人之道)、授“业”(良知之教)、解“惑”(致良知之法)的具体过程,也包括以黄绾为中心的台州籍阳明门人群体之间的相互交往与学术切磋;“文献”是对台州籍阳明弟子门人的文献史料的盘点与梳理,主要包括黄绾、叶良佩、王宗沐的著作文献的编撰缘由、传世版本、文献价值等,还包括围绕江右王门学者邹守益的佚文《应方伯良墓志》而对应良的生命历程与学术交游的梳理,浙中王门学者王畿佚文《明故南京通政司经历石洞黄公墓志铭》而对黄承文的生平学行的论述。这两个角度的选择,应该来说也是非常准确的,对于台州阳明学的群体以及相关的著述都作了非常清楚的梳理。尤其是作者不仅以文献的考辩为基础,同时对于相关历史遗迹都作了深入的田野调研,从而掌握了关于台州阳明学的大量第一手资料,这对于准确揭示台州阳明学这一议题来说,是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的。具体而言,这种意义可以表现为:
首先,将“台州阳明学”作为一个议题提出来,这就是一个值得认可的举措。虽然天台山和四明山在地理上是有密切关联,阳明学以及阳明后学在区域传播上也是各有特点。但是如前所言,正是因为天台山和四明山的这种特殊关系,似乎在提示我们应当更加重视在台州区域阳明学传播的具体表达,台州学者对于阳明学究竟有怎样的意义呢?《四库全目总目提要》对于明代台州临海籍儒学家金贲亨《台学源流》的介绍称:“是书叙述台州先儒,自宋徐中行迄明方孝孺、陈选,凡三十八人,各为之《传》。其疑而莫考者又有十五人,各以时代类附姓名于《传》末。其《传》虽多采《晦庵文集》《伊洛渊源录》诸书。然(金)贲亨当明中叶,正心学盛行之时,故其说调停于朱、陆之间。谓‘朱子后来颇悔向来太涉支离’,又谓‘朱子与象山先异后同’云云,皆姚江《晚年定论》之说也。”这里就很明显地呈现出了金贲亨理学所具有的“调和”程朱陆王之学的学术特质。再如黄绾,山东大学陈坚教授有一篇文章,题为《黄绾心学与天台宗佛学》(见《天台山文化当代价值理论研讨会论文集》,2015年未刊稿),就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探索,天台的宗教传统,天台宗的义理和道教的义理会不会影响台州学者对于阳明学的接纳呢?由此,作为一个独特区域概念的“台州阳明学”,自有其存在的意义,而宏敏兄的提法,有开研究风气之先的意义。
其次,“交游”与“文献”这两个点是本书侧重的重点,也是本书所花精力的重点所在,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这也是非常扎实的一种工作。因为经由这两个方面的梳理,我们可以对阳明学在台州的具体发展有一个非常直观的理解。虽然,由于时间和精力的关系。从本书对于这两个主题的处理效果来说,前者要优于后者。即作者对于阳明台州籍弟子之间的交游关系作了全面的考察,呈现出一种非常充分的、丰富的互动活动,这是阳明学在台州传播的鲜活例子。而在文献的部分,作者对于著述本身都作了比较深入的梳理,也基本上可以看得出台州籍阳明弟子(及再传弟子)的著作情况。但是,作品乃是思想的载体,也就是说,台州阳明学的独特意义恰恰是呈现在作品的具体描述之中,本书对于作品的思想内涵讨论方面,则稍显不足。但是,从总体上来说,瑕不掩瑜,本书已经从“交游”和“文献”的角度,较为丰富地呈现出了台州阳明学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尤其是对于目前学界尚未集中关注的台州阳明学来说,有一定的指示性。
最后,对台州
前言/序言
序
阳明学的兴起无疑是自晚明以来中国思想界的一个重要事件,并深刻影响着中国(乃至于东亚)的思想史进程。台州天台山与甬上四明山在历史上有着深刻的联系,在文化上也有着亲缘性,但是,在长期以来,尤其是关于阳明学的研究中,天台山是被忽视的。台州,应该来说,是阳明学发展的一个特殊区域。但是,可能是与天台山文化作为佛道标志性文化的基本定位有关,对于天台山(台州)儒学的忽视,可能也是情理之中的。然而,情理之中并不代表历史事实即是如此。比如在《明儒学案》《台学统》《续台学统源流》等等作品中,我们都可以发现一大批台州儒家学者的身影。台州儒学的研究,从总体上来说,是一个长期被忽视或者说被掩盖的事实。从这个角度来说,无论是对于朱子学,还是阳明学,在台州的发展都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张兄宏敏博士的新著《台州阳明学研究》,从这个角度来说,是一部具有开拓性意义的力作,该书以“交游”和“文献”为关键词,对台州籍阳明弟子以及阳明学者群体进行了深入的考辩,由此呈现出了台州阳明学的一个基本发展脉络。将“台州阳明学”作为一个学术命题重新确立起来,这是该书最大的一个贡献。而全书的脉络则是围绕“交游”与“文献”来展开的。按照作者的区分,“交游”指得是王阳明与台州籍阳明弟子(如黄绾、应良、林元叙、林元伦、赵渊等)之间交往结识,王阳明针对台州籍诸弟子各人不同的学术根基与禀赋志趣而进行传“道”(圣人之道)、授“业”(良知之教)、解“惑”(致良知之法)的具体过程,也包括以黄绾为中心的台州籍阳明门人群体之间的相互交往与学术切磋;“文献”是对台州籍阳明弟子门人的文献史料的盘点与梳理,主要包括黄绾、叶良佩、王宗沐的著作文献的编撰缘由、传世版本、文献价值等,还包括围绕江右王门学者邹守益的佚文《应方伯良墓志》而对应良的生命历程与学术交游的梳理,浙中王门学者王畿佚文《明故南京通政司经历石洞黄公墓志铭》而对黄承文的生平学行的论述。这两个角度的选择,应该来说也是非常准确的,对于台州阳明学的群体以及相关的著述都作了非常清楚的梳理。尤其是作者不仅以文献的考辩为基础,同时对于相关历史遗迹都作了深入的田野调研,从而掌握了关于台州阳明学的大量第一手资料,这对于准确揭示台州阳明学这一议题来说,是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的。具体而言,这种意义可以表现为:
首先,将“台州阳明学”作为一个议题提出来,这就是一个值得认可的举措。虽然天台山和四明山在地理上是有密切关联,阳明学以及阳明后学在区域传播上也是各有特点。但是如前所言,正是因为天台山和四明山的这种特殊关系,似乎在提示我们应当更加重视在台州区域阳明学传播的具体表达,台州学者对于阳明学究竟有怎样的意义呢?《四库全目总目提要》对于明代台州临海籍儒学家金贲亨《台学源流》的介绍称:“是书叙述台州先儒,自宋徐中行迄明方孝孺、陈选,凡三十八人,各为之《传》。其疑而莫考者又有十五人,各以时代类附姓名于《传》末。其《传》虽多采《晦庵文集》《伊洛渊源录》诸书。然(金)贲亨当明中叶,正心学盛行之时,故其说调停于朱、陆之间。谓‘朱子后来颇悔向来太涉支离’,又谓‘朱子与象山先异后同’云云,皆姚江《晚年定论》之说也。”这里就很明显地呈现出了金贲亨理学所具有的“调和”程朱陆王之学的学术特质。再如黄绾,山东大学陈坚教授有一篇文章,题为《黄绾心学与天台宗佛学》(见《天台山文化当代价值理论研讨会论文集》,2015年未刊稿),就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探索,天台的宗教传统,天台宗的义理和道教的义理会不会影响台州学者对于阳明学的接纳呢?由此,作为一个独特区域概念的“台州阳明学”,自有其存在的意义,而宏敏兄的提法,有开研究风气之先的意义。
其次,“交游”与“文献”这两个点是本书侧重的重点,也是本书所花精力的重点所在,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这也是非常扎实的一种工作。因为经由这两个方面的梳理,我们可以对阳明学在台州的具体发展有一个非常直观的理解。虽然,由于时间和精力的关系。从本书对于这两个主题的处理效果来说,前者要优于后者。即作者对于阳明台州籍弟子之间的交游关系作了全面的考察,呈现出一种非常充分的、丰富的互动活动,这是阳明学在台州传播的鲜活例子。而在文献的部分,作者对于著述本身都作了比较深入的梳理,也基本上可以看得出台州籍阳明弟子(及再传弟子)的著作情况。但是,作品乃是思想的载体,也就是说,台州阳明学的独特意义恰恰是呈现在作品的具体描述之中,本书对于作品的思想内涵讨论方面,则稍显不足。但是,从总体上来说,瑕不掩瑜,本书已经从“交游”和“文献”的角度,较为丰富地呈现出了台州阳明学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尤其是对于目前学界尚未集中关注的台州阳明学来说,有一定的指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