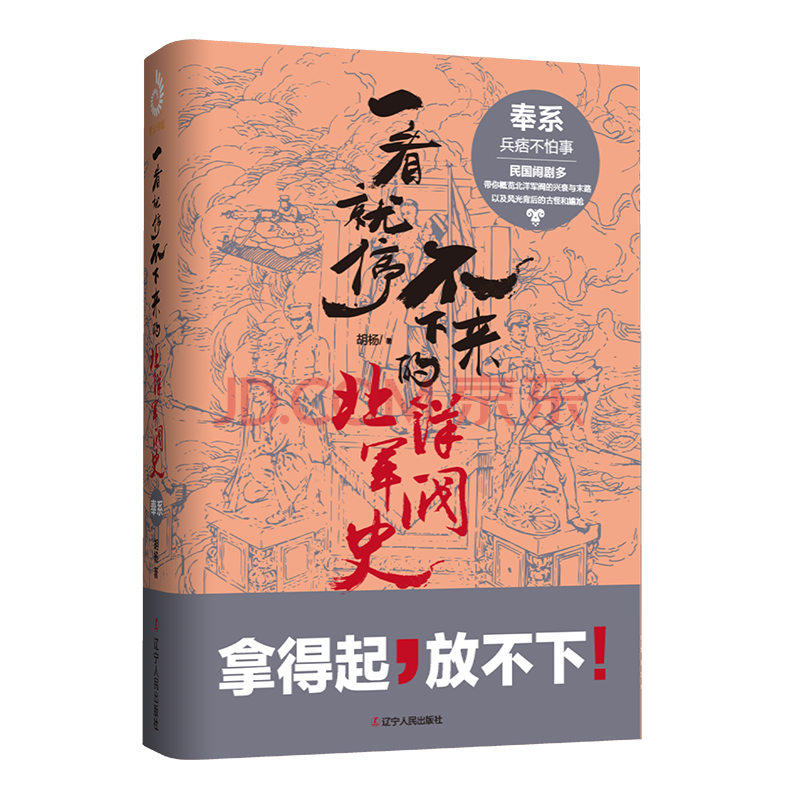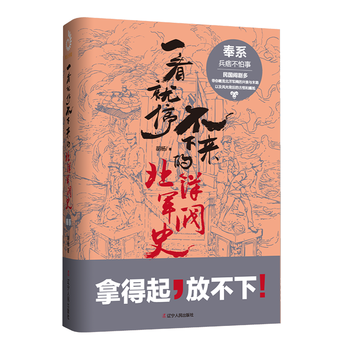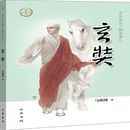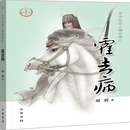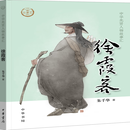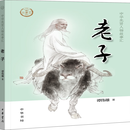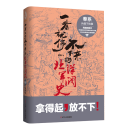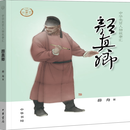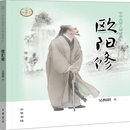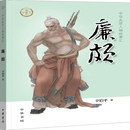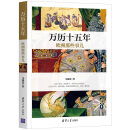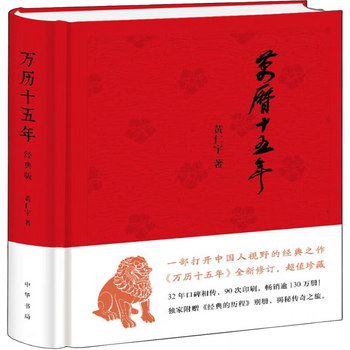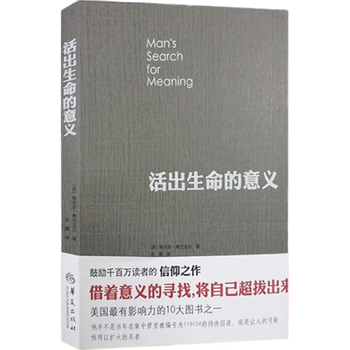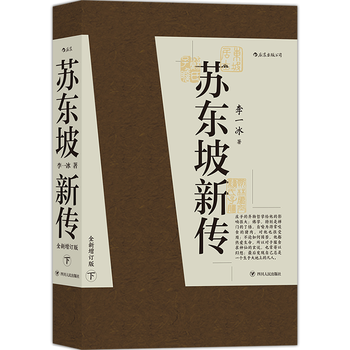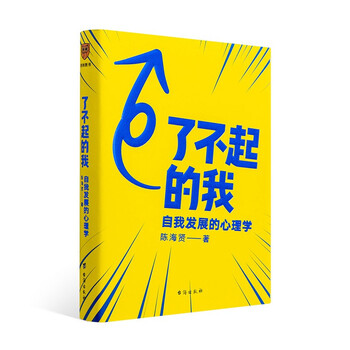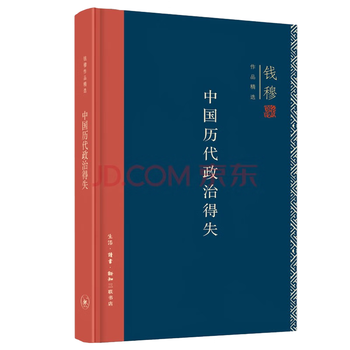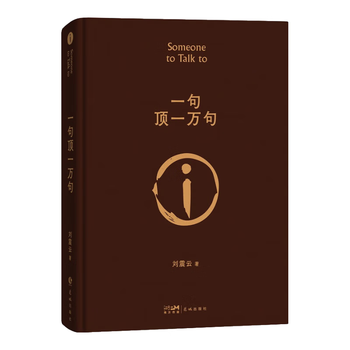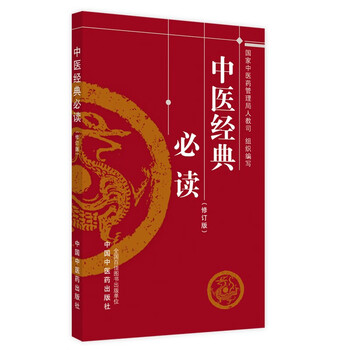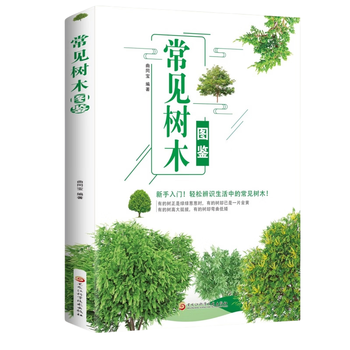内容简介
奉系军阀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部分:DI YI部分是DI YI直奉战争之前,这时的奉系军阀江湖气更浓,按照绿林的方式管理队伍,打仗的时候往往一哄而上、一哄而下,纯粹是打群架的套路;第二部分是DI YI次直奉战争以后,张作霖在东北卧薪尝胆,部队也逐渐走向正规化,到第二次直奉战争的时候,入关的奉军已经是一支铁打的部队;第三部分是皇姑屯以后,少帅张学良掌管东北军,此时的东北军就不再是军阀部队,而是国民革命军。
如果打个比方,皖系军阀是一帮政客,直系军阀是一帮秀才,那奉系军阀就是一帮混不吝。皖系军阀要打仗,必然是先找人借钱,有了钱有了枪有了优势才敢开打;直系军阀是先开会,怎么打都商量好,然后点兵派将出去开仗;奉系军阀则不然,张作霖只要拔出枪来跳到桌子上,奉军摔了酒碗抄起家伙就能出去干。直皖军阀是“说完了再打”,而张作霖则是“打完了再说”,所以北洋军阀中真正靠枪杆子说话的,其实只有奉系这独一份。
试读
一、独霸奉天:谁人不识张大帅
奉天在清末民初一直都是极为敏感的地方,奉天府也就是现在的辽宁省沈阳市,清朝皇帝皇太极改称沈阳为盛京,汉文意为“天眷盛京”。清军入关之后,遂迁都北京,以盛京作为陪都。1657年,顺治帝以“奉天承运”之意在盛京设立奉天府,所以盛京又被称为奉天,待清朝覆灭,民国建立,人们已经称沈阳为奉天,而不再称其为盛京。奉天既是清朝的“龙兴之地”,亦是东北重镇,北可退守蒙境,南可叩关入京,一心称帝的袁世凯自然比谁都看重这块地方。
(一)
1915年7月25日,驻防奉天第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抵达北京,随后即由军警处处长雷震春陪同到居仁堂觐见袁世凯。对于土匪出身的张作霖来说,这是他头一次进皇宫,在以前,这是他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只觉得什么东西都惊奇,尤其是陈列在清宫中的古瓷与字画,看得张作霖啧啧称奇、惊叹不已。待见到袁世凯,张作霖依然按照清朝的规矩行跪拜大礼,这一下算是正中袁世凯下怀。此时袁世凯正好掏出怀表看时间,张作霖看到袁世凯的怀表,却不知道是什么珍奇玩意儿,袁世凯随即把怀表送给了张作霖,张作霖忙不迭地连声道谢。
接着便渐入正题,诉及东北局势,袁世凯对张作霖说,“东三省形势危险,全仗军威镇慑,赖以有今日之安宁。嗣后仍当振刷精神,为东三省人民谋幸福。本总统有厚望焉。”这段话的意思再明白不过,袁世凯就是告诉张作霖:跟着我,有肉吃。只要张作霖跟着袁世凯,高官厚禄、荣华富贵必然是享用不尽,而张作霖也坚决表示,只要袁世凯吩咐的事情,他肯定毫无条件地照办。
袁世凯对看起来颇憨的张作霖印象极好,而张作霖也在袁世凯面前尽显其憨傻之气,双方你一言我一语,聊了很久,一团和气。整个谈话的过程中,袁世凯都不时开怀大笑,据说张作霖对袁氏的印象亦颇为深刻。待到会面结束,张作霖自居仁堂回到自己的行馆,看到之前在清宫内看到的那些古瓷和字画都已经由专人送来,来人告诉他,是大总统看到他很喜欢这些东西,所以特地送来。袁世凯做的这些事,让张作霖非常感动,也实实在在地给初出茅庐的张作霖上了一课,后来张作霖驾驭部下时,亦多使用袁氏的手法笼络人心。
有了袁世凯的这次接见,等于给张作霖的政治资本加上了重重的一笔。待张作霖拿着袁氏亲赐的古瓷和字画回到奉天,各界人士更是对张作霖另眼相待。据说,张作霖自北京回到奉天以后,他的宅邸“成为全省政治中心,每日宾客如云,文武官员都有。无论与张有无关系的事情,都与他相商或征求他的意见,事先必使他与闻”,曾在东三省任总督的赵尔巽想给亲信王永江谋个奉天民政司的差事,都要派人去询问张作霖,结果张作霖听罢即流露出“不悦之色”,赵尔巽就不敢再提了。
曾经提拔过张作霖的赵尔巽尚且遭受冷遇,就更不要说身在其位的张锡銮。但张锡銮虽然贵为奉天都督,但手里并没有实权,张作霖尽管不过是一个师长,但奉天内外的部队几乎都听凭他的调遣,张锡銮空有都督之职,却连一兵一卒都调动不得。而张作霖除了调动部队,也开始插手奉天地方官员的任免,政府的官员虽然都是张锡銮的下属,但却不得不听从张作霖的命令,连张锡銮尚且不能指示张作霖,更何况是下面的官员?但成为了奉天“太上皇”的张作霖并不满足,他并不想一直在张锡銮的后面,而是想成为真正的奉天都督,掌握奉天的军政大权。
初次入京的张作霖,多少还有些摸不着门路,凡事都需要雷震春指点。雷震春早年曾在奉天任职,管辖张作霖的部队,张作霖入京后多有赖于他的帮助,但雷震春也不欲张作霖在北京接触的关系过多,所以初次入京的张作霖只是走马观花。张作霖毕竟是精明的人,看起来傻,并不代表真的傻,跟在雷震春的身后早就瞧明白了门道,所以第二次张作霖再入京,便已经轻车熟路。
据当时奉天发行的《盛京时报》报道,张作霖二次入京其实是“秘密接纳政府要人,试图运动继任奉天将军的职务”,可见这件事情已经不是什么秘密,而这种事情居然可以见诸报上,显见张作霖并未阻止,甚至还可能通过某些关系悄悄授意。张作霖之所以胆敢这么公然地想要奉天都督一职,就是要给张锡銮压力,逼迫他主动让出都督的位子,张作霖其时大权在握,出任奉天都督只是一个形式上的差别。
在民初的官场上,这种事情其实很多,一方逼迫另一方下台,却又摆出一副事不关己的态度,逼得对方走投无路,自己才好趁机上位。段祺瑞对付黎元洪、冯国璋,用的就是这个办法,张作霖对付张锡銮用的也是这个办法,张锡銮本来就年迈体衰,加上处在如此尴尬的境地,于是就向袁世凯提出辞呈。8月,张锡銮终于离开了奉天这个是非之地,张作霖排挤走了张锡銮,便觉得奉天都督的位置必然非自己莫属了,但偏偏就是在这个时候,袁世凯硬是摆了张作霖一道。
(二)
段芝
前言/序言
前 言
从大帅府到紫禁城
关于奉系军阀,我最早的知识来源于单田芳先生的长篇评书《乱世枭雄》。还是在读初中的时候,自祖母那台老旧的收音机里,每天都听单田芳先生绘声绘色地讲着那个光头小个子张作霖的风云际会、纵横捭阖。在彼时的脑海里,来自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的张作霖,是民国时代的梁山好汉,大碗吃酒、大块吃肉,喝大了便嚷嚷要杀上金銮殿“夺了那厮的鸟位”。于是,脑海里便有了两个张作霖:一个是课本上的军阀,一个是评书里的好汉。
再后来便是工作了,无意间看到张学良先生口述的回忆录,看罢之后,脑子里又有了两个张学良:一个是历史书上描述的那个正义凛然的民族英雄,一个是口述史里那个甩不掉公子气的迟暮老人。我们这代人自小从父母和师长那里,学到的都是脸谱化地看待历史人物,这个人要么是高大全,要么就是三花脸,以至于后来再面对史料,疑心病比谁都重。
民初的三大军阀里,皖系和直系属于正统的北洋系,开创者段祺瑞和冯国璋都是袁世凯的左膀右臂,而奉系则属于北洋系的边缘派,如果不是张作霖靠着枪杆子直起了腰杆子,北洋军阀原本是不把这个胡子出身的小个子当回事的。说起奉系军阀,就不能不提到张作霖那个流传很广的段子,说是日本人找老张要幅字,老张挥手写就,但落款的时候却写成了“手黑”。身边的赶紧提醒张大帅,说应该是“手墨”,少了一个土字底,哪知道张大帅双眉一竖,妈拉个巴子,老子写的就是“手黑”,日本人想要中国的土地,老子连一寸也不给!
这就是崛起于黑土地上的奉系军阀,虽然只是小小的一件事情,却将这个绿林起家的军阀勾勒得惟妙惟肖。奉系军阀有气节,而且强势,正统的北洋系因为政治地位看不起奉系军阀,而奉系军阀也看不起那些只会玩政治博弈,不敢在战场上真刀真枪招呼的老军阀;奉系军阀也有江湖气的一面,张作霖做上了大元帅以后,依然改不了满口“妈拉个巴子”的口头禅,像杨宇霆这样徒有其名却连战连败的将领,张作霖照样留在身边,这个“义气”老张看得最重。
奉系军阀的历史,大概可以分为三部分: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前是第一部分,这时的奉系军阀江湖气更浓,按照绿林的方式管理队伍,打仗的时候往往是一哄而上、一哄而下,纯粹是打群架的套路;第二部分是第一次直奉战争以后,张作霖在东北卧薪尝胆,部队也逐渐走向正规化,到第二次直奉战争的时候,入关的奉军已经是一支铁打的部队;第三部分是皇姑屯事件以后,少帅张学良掌管东北军,此时的东北军就不再是军阀部队,而是国民革命军。
奉系军阀的顶峰时期,便是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到郭松龄倒戈之前,这一阶段的奉军睥睨北洋系无人可敌。当然,杨宇霆、姜登选在东南吃了孙传芳的败仗,但他们带过去的并非奉军的精锐之师,当时奉军的王牌部队,掌握在“郭鬼子”郭松龄的手里,到郭松龄起兵倒戈,奉军的精锐在奉系内战中死伤殆尽,加上郭松龄这位奉军中首屈一指的战将被杀,奉军中其实也不剩什么实力派了。郭松龄倒戈,其中包括在奉军中不被重用的关系,张作霖信赖亲近的幕僚杨宇霆、姜登选、李景林等,造成了郭松龄的倒戈,这也是奉军在北伐战争中不堪一击的原因之一。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入关的奉军,和之前北洋系的军队完全不同,当然这也和奉系将领的性格有点儿相同。奉军很少打政治战,虽然也有参与组织过三角同盟,但更多的是真刀真枪地开打,而且懂得利用先进的武器进攻,既敢于拼命也懂得怎么拼命。只要大话喊出去,那打掉了门牙也得硬着头皮往前冲,于是张作霖硬是敢带着几万奉军入关,和虎踞中原号称统率数十万大军的吴佩孚开战。光是这股子拼命劲,就足以让北洋系的老军阀们吓破了胆,第二次直奉战争还没有开打,准备倒戈的直系将领就已经够组团了。
如果打个比方,皖系军阀是一帮政客,直系军阀是一帮秀才,那奉系军阀就是一帮混不吝。段祺瑞要打仗必然是先找人借钱,有了钱有了枪有了优势才敢开打;直系军阀是先开会,怎么打都商量好了,然后点兵派将出去开仗;奉系军阀则不然,张作霖只要拔出枪来跳到桌子上,嚷嚷两句“妈拉个巴子谁谁谁欺负咱们,弟兄们说咋办”,奉军摔了酒碗抄起家伙就能出去干。直皖军阀是“说完了再打”,而张作霖则是“打完了再说”,所以北洋军阀中真正靠枪杆子说话的,其实只有奉系这独一份儿。